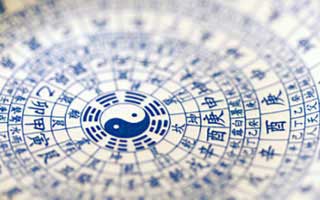屬羊十四日出生命運好嗎
這是一個 流浪與回家的故事。
過去十幾年,攝影師陳亮輾轉湛江、西安、廣州、無錫等地,拍攝了許多照片。回顧過去,他發現自己一直在尋找棲息地,一個是真正的、居住的家,一個是內心的家、精神的歸宿。
2003年,陳亮之一次離開家去流浪,20歲的他離開故鄉東海島,遠赴西安求學。抵達西安那天,下著小雨,他挺失望的,學校怎麼這麼小,西北菜怎麼這麼重口,三個月沒怎麼吃下飯。故鄉東海島不同,它有延綿的海岸線,的植被,的海鮮和柔軟的沙灘,他是在廣闊的天與海之間瘋跑著長大的。當時,海島的孩子只想著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大三那年,他放棄專修,開始攝影,跑到廣州當了一名實習攝影記者。他穿梭在廣州大大小小的街道,觀察那些與他相同的異鄉客,記錄了一些住在大橋下的流浪者。大學畢業,他到了江南,住在無錫清名橋邊的弄堂,記錄下弄堂作為老無錫人家的最后樣子。流浪至第六年,生活并不順遂,他感到痛苦又無力。此時,太湖拯救了他,他開始環著太湖攝影,看到了一些和他一樣將自己交付于太湖的漂泊者。2022年,當得知東海島即將面臨工業化改造,填海造廠,他決定結束流浪的日子,回到故鄉。
徹底回家之前,他又在廣州、上海等地拍攝了一組名叫《流浪人間》的作品,記錄了流浪在城市之間的人們。那年夏天的一個晚上,他正在掃街,突然聽到一個男聲唱著,流浪的腳步走遍天涯,沒有一個家。
這也是一代人的命運。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歷歷史上更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人們在城市和鄉村之間變換,卻總有一種漂浮在空中的掙扎與慌張。
現在,陳亮在湛江一所民辦高校擔任攝影專業老師,與00后的孩子們在一起,有課時開車跨海過去,沒課就待在島上,拍攝或者挑選舊照片,有時候搗鼓自家種滿龍眼、黃皮、木瓜、香蕉和菠蘿蜜的院子。晚上睡覺時,偶爾會聞到附近工廠散發的刺鼻味道。媽媽仍然不理解他為什麼回家,在故鄉,有時他被人覺得像個怪物,但這又是他現在所能想到的最妥帖的生活。
流浪,回家。陳亮始終在探討這些問題:人為什麼流浪?人又為什麼回家?人流浪的時候會找到家嗎?人回家的時候是不是也可能在流浪?
以下是陳亮的講述——
文|賴祐萱
編輯|槐楊
圖片|陳亮
1
2006年的一天,我在珠江邊上閑逛,走到橋。橋是廣州一座跨越珠江兩岸的橋,也是重要的主干道,、 街女、擺攤小販,很奇怪,各種各樣的人都往那里跑。很偶然地,我看見橋底下掛著很多衣服,感覺是有人住在那里。
那時橋上全是機動車道,電動車摩托車都不允許上橋,行人更不可能,我只能沿著橋墩爬下去。橋挺高的,我膽兒大,掛著焊的桿桿溜下去。你知道我看到什麼了嗎?一個躺在橋底下,翹著腿看報紙。
橋上汽車轟鳴,嗡嗡作響,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在橋底看報紙。我震撼了。他看到我,特別緊張,直接舉起一把刀,你出去。我知道我他的領地了,那是他的家,我是個外來者。
2006年7月29日,廣州橋底,橋上不停轟轟響,橋下一位男子安靜地看報
那段時間也是我流浪的開始。我出生在湛江一個名叫東海的島嶼,從小喜歡在海灘邊踢,想成為運動員,高考報了西安體育學院,覺得西安古城很有文化,特別想去。上了大學,才發現我這種不是從小接受專業訓練的人,畢業最多當個教練,可是那時我年輕,覺得人活一輩子,總要在地球上留點痕跡。
在西安的一個4月,我拍了一張人們排隊坐公交看桃花的照片,那時只有一趟車到西門城墻,大家自覺地排長長的隊伍,來一輛上一輛。我覺得,西安人怎麼這麼文明?現在看這張照片,會想起那個時代人們的服裝,人們的狀態,人們的熱情和笑容,還有四四方方的綠皮公交車。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審美,過去了就是過去了,但照片可以記錄下一切。
我開始學攝影,其實就是沒事出去掃街。花兩塊錢,坐公交到處游蕩。有時候背著包從西安出發,走到邊遠的鄉鎮,路上看見車就招手攔,晚上睡窯洞,餓了走到村民家給人10塊錢,他們會給你下碗面。
大三暑假,我到廣州找實習,很幸運,我成為《羊城晚報》的攝影實習生。之一個月,我獨立署名發表了17篇報道,稿費夠養活自己,我時常睡在報社,隨時待命跑突發,半夜我要麼在突發現場,要麼在醫院,要麼在。那是一段自由又美妙的日子。明明廣州不是我的家,但感覺到精神上特別滿足,特別充實,真正在活著。
也是在那段時間,我遇到橋下的。我趕緊跟他解釋,我是大學生,來做攝影實踐,他才放下刀,慢慢和我聊起來。后來那半年,我經常去找他,背著雙肩包,從橋墩滑下去,動作越發嫻熟,我們關系也變得緊密。一起去吃飯,一起在橋下、珠江邊逛逛。后來,我知道了他的故事。
大叔姓毛,家境挺好的,是,媽媽是老師,有個女兒在上大學,跟我差不多大。這樣的人怎麼會流浪呢?他說,他不是廣州人,后都聽說廣東有錢,想來發財,但來了之后,他發現別說發財,不如意一件接一件,日子越過越糟,婚也離了,和父母鬧得也很僵,漸漸也不跟家里 了。他在廣州流浪,發現了橋底,對他和其他流浪者來說,這是個好地方。不像馬路上人來人往,會有趕他們走,橋墩只是有些吵鬧,但很私密,很安全,很獨立,不會有人來偷東西,是一個完全屬于他們的場所,是最像家的空間。
他有了自己的家,還有了幾個家人,都是因為各種各樣原因流浪至此的人,他們相識十幾年了。毛大叔的朋友王先生 山西,42歲,自稱在初二時寫過一本短篇《冷暖人間》,當地出版社發行了5000冊。24歲離家后,他再也沒有回去過。
毛大叔的生活很規律:每天早上四五點,拿個小電筒到珠江邊上撿,字畫、鐘表、夾克、椅子、玉佩,什麼都能撿到。天蒙蒙亮,他拿著東西到珠江邊市擺攤,賺點錢,然后回到他的橋底,他的家。
他睡在橋墩下鐵架上,長10米,寬0.6米的鐵架可以睡好幾個人。因為清晨撿,他們起得都很晚,我一般在中午或下午去見他們,偶爾帶點零食去。白天他們也沒什麼事,就是在廣州晃蕩。我們在路邊吃5塊錢的盒飯,挺難吃的,感覺有時候飯菜都是餿的。洗澡也需要時機,江水漲高了,才能用塑料桶打一桶水上來。但他們并不在意。他們都很高興找到了這里,既省錢又暖和,還沒有人打擾。
我記不清毛大叔為什麼不工作了,也許是習慣了流浪,習慣了自由的、散漫的生活吧。他偶爾還跟女兒打,其他家人不 了。我鼓勵他,應該回家去看看。他說,年輕的時候出來,飄蕩了幾十年,現在老了,挺自卑的,覺得沒臉回去見家人。
因為他,后來我又認識了其他流浪者,拍下了他們的故事。他們都挺善良的。一般人不會給你拍的,也不愿意把心思告訴你,可他什麼都跟我說了,還讓我進入了當時的他的家。畢業后有段時間,我住在廣州城中村,每天坐地鐵擠不上,我就在 臺上聽歌,等三四趟車,等所有人走了我再上去。我經常深更半夜睡不著覺,和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那時候我特別能夠理解那種流浪感。
最后一次見面,我們分別的時候,他送給我兩個木屑化石玉佩,都是撿來的,很漂亮,一小塊木屑裹在琥珀色之中,陽光照著會閃閃發光。那段時間,這個玉佩我一直都戴在身上,踢球也戴著,看見就會想起他。遇見他,讓我覺得,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值得尊重,無論對方貧富與否,都應該善良、質樸、平等地看待他們。大叔也讓我看到,流浪盡管有些孤獨,但不一定痛苦和不堪,它仍然可以是一件很自由、很浪漫的事。
2006年12月19日,廣州橋底,王先生在家里看《珠寶玉器大觀》
2
后來,我也像大叔一樣,開始了我的流浪人間。
大學畢業后,我陰差陽錯沒能留在廣東工作,去了無錫《江南晚報》當攝影記者。在無錫,我就是一個異鄉者,租的之一個房子在清名橋旁邊的弄堂里。對,就是現在那個很有名的旅游景點。
我趕上了它從弄堂到景點的轉折點。那時,我租在二樓,小小的臥室,邊上緊貼著廚房和衛生間,一個月只要500塊。我每天騎著小車瞎逛,跑遍了無錫城的角落,那時有個很強烈的感受,整個無錫城到處都在,尤其是我生活的弄堂。
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舊城危房改造,一種是新城來了,拆舊建新。有多沖擊呢?每天醒來,我就能看見出租屋門口的弄堂在敲敲打打。而這些一百多年兩百年的老房子被拆完后,工人們模仿老屋,建一個新的,再把它做舊了。非常荒誕:你眼見著這條古街拆完了,再重建,搞上油漆,就叫清名橋古運河歷史文化街區。
歷史的江南正在消失。我想,這個東西太重要了,怎麼沒有人記錄一下呢?2007年開始,我帶著相機,開始拍弄堂,當時的設備很差,對焦慢得很,淺景深會跑焦,只能用深景深,不是刻意,但我被逼得拍成這樣,去 每一個細節。
后來發現,那些細節已是江南最后的生活日常。
江南弄堂的清晨從刷馬桶開始。屋里沒有廁所,居民們都去公廁倒馬桶,刷干凈拎回來,整整齊齊晾在巷子里。還有專門幫人刷馬桶的人。吃完早飯,老人們忙著鍛煉身體,舞刀弄劍,孩子們趕著上學。上午去露天菜市場買菜,中午做飯,洗衣,沒事喝點茶,睡個午覺,午后的弄堂最安靜。傍晚孩子們回來了,老人們在巷子里下棋聊天,孩子打鬧嬉戲,晚飯后三三兩兩走到清名橋散步,一天就過去了。那時清名橋少有游客,橋上聊天的、乘涼的都是居民,他們在弄堂里縫被子、補鞋子,在橋上晾曬洗干凈的被單。
大通弄有個大爺,用煤爐燒水總是冒濃煙,他就在煙霧繚繞中熏得睜不開眼。他孫女上學都得捂著嘴跑出來,好玩得要命。給他拍照后不久,大通弄就拆了。界涇橋弄里住著兩個年近百歲的老奶奶,她們喜歡坐在弄堂里說悄悄話,嘴貼著耳朵那麼說。那時候,看到我,總是招呼,小陳又來拍照啦,進屋吃飯呀。
弄堂里的大爺們。
現在,想要進入一個家變得特別困難,因為疫情,也因為人們對自己私密空間、對自己的保護意識變強了。但在弄堂生活的那幾年,認識一個人,進入一個家庭,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在桐鄉濮院遇過一個獨居老人,他的家掛滿了各種鍋具和老物件,桌上大大小小的熱水瓶。還有一個穿襯衫西褲皮鞋的大叔,當時我沒在意,這幾年才覺得他的照片怎麼這麼好,能看到一個江南人的文雅和傲氣,盆景的茶壺和花朵又是獨屬江南的精致。還有一戶在江陰的人家,世代學醫,三百年的老屋就要拆了,他們家的墻上掛滿了老祖宗的照片,大廳里還種著靈芝。
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這群人被迫離開弄堂、離開家的瞬間。2009年11月22日,那是一個周日,無錫天氣晴朗,清名橋沿河14號居民曹聽生一家搬家了。
橋頭的老屋,曹家已經住了一百多年。曹太太不愿意走,她小時候就在清名橋,嫁到曹家后也住在這里,她想一輩子住著,住到最后。但沒辦法,為了配合古運河歷史街區改造,他們不得不離開。60多歲的老夫婦,什麼都舍不得扔,衣柜、桌子、縫紉機都要搬走。這些家具也不知何時到這戶人家,現在樓梯太窄,門太小,都出不去了,他們從二樓窗戶把柜子托出來,下面有人接著。家當一件一件堆在橋邊,木圓桌、藤椅子、花棉被。屋檐已經掛上印著清名橋古運河的紅燈籠。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一種生活方式開始了。
2009年11月22日 無錫清名橋沿河14號居民曹聽生一家 為了配合清名橋古運河歷史街區的改造 開始率先搬出部分家具
那天,曹聽生把孩子們都叫回來,在老祖屋吃了一個團圓飯,他們喊我去吃,我不好意思,沒去。當時沒有想到應該給他們留一張家族合影,非常非常遺憾的。現在,我也不知道他們去了哪里,聽說搬到了挺遠的地方。曹家舊址現在是最著名的景區,對面開了家吧,小河、周云蓬都來過。再往前,商業味道更濃,很吵很鬧的酒吧、 紅餐廳,盡是一些所。
我挺不能理解。弄堂的靈就是生活,居民全部都趕走了,歷史在哪兒了?文化在哪兒了?生活又在哪兒了?有年過年我沒回家,拍攝返鄉的弄堂年輕人。我以為弄堂過年會特別熱鬧,結果那里冷冷清清,一片寂靜。很多子女都住在城里,過年回來看一眼,吃個飯就走了,或者把爸媽接到香滿樓擺一桌,連家都不回了。
我突然發現大家對家的理解不同了,可能年輕人覺得逃離這里是一件好的事情,流浪在城似乎比擠在小小的弄堂里更舒服。留在弄堂里的往往是一對一對夫妻,也有人老伴兒去世了就獨居,即使孩子們都走了,他也守著這個家。他們覺得這里才是家。
弄堂生活。
3
《江南弄堂》了很多榮譽,漸漸有人認識我,夸贊我。如果繼續拍弄堂,是保險的,可難道一直這樣拍下去嗎?不行。我寫了貼在床頭,你要否定自己,只有否定越徹底,才能改變越徹底。
那是我最頹廢的一段時間,我做攝影記者是比較理想的,我在敬老院做志愿者,發現陪伴老人最后一刻的大部分是護工,老人緊緊握著護工的手就閉眼了。有些老人去世了,孩子才來。有的只見錢,不見人。我調查了無錫十幾家敬老院,拍攝了一組照片,希望通過攝影發聲改善他們的環境,但是報社沒讓我發。我還拍過一個癱瘓的廚師,媽每天用繩子牽著他走在弄堂里,想讓他重新學會走路,報社也不讓發,說這樣的事情太多了。我覺得理想有點破滅,又處理不好報社復雜的人際關系,流浪感特別強烈,特別難受。
當時,我需要一個,一個自我救贖的途徑,一個把自己代入其中的地方。
2013年春節,我沒有回家,用年終獎買了一臺膠片相機,開始拍攝太湖。到四月,我辭職了。之問我,你跟爸媽說了嗎?他們很驚訝,怎麼會有人辭去這麼穩定的工作?他理解不了我有多高興。
拍太湖,是一個很純粹、很自我的選擇。我沒有多少錢,公積金也就5萬,加上卡里余額大概6萬塊錢,全部取出來,開著車上路了。沒有工作,沒有任務,什麼都沒有,只想著這棵樹好玩,那棟廢棄房子有趣,可以到湖邊小鎮吃碗面,也可以在小樹林掛張吊床,吃著西瓜,聽著歌睡午覺。或者什麼都不做,只是在湖邊發呆。有時錯覺遙遠的地方就是故鄉,我還像小時候那樣坐在海邊。它特別像我的故鄉,它很大, 在湖邊一望無際,家鄉的海也是一望無際。
太湖周邊能抵達的地方,我幾乎都去了。有一些城市有環湖路,有一些地方只能走小路,很像探險,不知道什麼時候沿著細路就會闖進一個村落。你會看到很多有意思的東西,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
我遇過在湖邊的人。兩個中年人坐在隱聊天,雙腳翹著的姿勢、雙手擺放的樣子都一樣,一雙白色高跟鞋還放在橋頭。那種狀態一看就知道不是夫妻,老夫老妻不會這麼甜蜜、這麼膩。他們之間的磁場有一種特別的浪漫。他們完全沒有想到我會出現,看見我拍照就走了。
橋墩上的人 2013 蘇州太湖
還有躺在太湖草叢睡著的女人、獨自 在假山上的男子、居住在帆船上的老人、戴著架的漁民、摘蘆葦葉的阿姨、月亮下深思的大叔……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叫陳燕(音)的女孩。
無錫太湖邊,一道湖邊堤壩是我的秘密,要走過一段狹長的水泥道,湖有個廢棄的臺,挺危險的,不小心就會跌落湖中。夏天我去游過泳,很舒服,到了冬天,我又想去看看。
天氣很冷,湖邊沒有人,但剛下車我就聽到了她的聲音, 某某某,我已經不再愛你了!我恨死你!歇斯底里的聲音,一會兒哭,又一會兒笑。我很慌張,趕緊跑過去,害怕她喊完就要跳湖了。她好像也發現我了,往回走,我們走得都很小心翼翼,然后在堤壩中間相遇了。我不好意思主動說話,反倒是她看見我笑了,你是不是怕我跳下去啊?我說,是啊,你要跳下去,我不得不下去救你,我最怕冷了。她又哭又笑,你放心吧,為這種人不值得。
她情愿把自己的心思交付給太湖。我沒有問她的愛情故事,也不知道她后來有沒有再來過這里。我只記得她說她叫陳燕,從外地來這里打工,現在,她要回去了。然后,她沿著湖走出去,不見了。
失戀女孩 2013 無錫太湖
除了這些人,一路上,也可以看到人類是如何太湖,如何消耗它又舍棄它的。
我曾路過一個荒廢的主題公園,聽說當年建造花了不少錢,但那時,水中長廊已經長滿了和苔蘚,頂棚漏了,柱子變得斑駁。我爬到景區更高處,俯瞰公園全景,結果發現對面山上有很多紅色屋頂,仔細一看,居然是個別墅群。
走進別墅群更令人,十幾棟三四層的別墅在山頂上荒廢,雜草和樹叢覆蓋了它,樓里更是布滿藤蔓和蜘蛛 。每棟房子里都有闖入者留下的痕跡:有的樓里有像,另一棟樓里有鳳凰圖騰,有女子肖像,有一句我愛你,有的,還有一條長布懸掛在房梁上,像極了現場。甚至還有一盆浸泡著沒有洗完的衣服,旁邊擺著一雙鞋,似乎放了很久很久。
一棟荒廢別墅的房間 2013 無錫太湖邊
有時我覺得太湖已經不堪重負,人們假裝看不見它的污染,看不見過度,照樣去湖邊搭帳篷,去湖邊踏青。無錫每年都有櫻花節,人山人海,大家會到黿頭渚看櫻花吃湖蟹,而不知道黿頭渚旁邊曾經的藍藻有多麼嚴重,湖水有多臭。前幾年太湖禁捕了,不允許扔了,人們也不能再靠近湖邊了。這也許是一種進步。
但是,太湖最美的地方就是它的原始和自然。森林,,湖水,沒有改造過的東西才是最美的。我記錄了那個時代的太湖——在附近打工的異鄉人們,結束一天辛勞后,可以和家人們騎車到湖邊看風景。他們還可以在湖里游泳,在湖邊燒烤、摘果、捕魚,做著和故鄉一樣的事情。
過去拍江南弄堂是追著拍,生怕錯過了瞬間,一天可以拍幾百張。拍太湖時,換了中畫幅膠片相機,膠片太貴了,手動對焦又慢,所以每一張照片都是我對瞬間謹慎的審視。不得不凝視它,不得不看著對方的眼睛,不得不打量它,再決定要不要與拍攝之物真正交往。
所以,太湖那組照片給人很寬廣的感覺,那也是太湖的迷人之處,自由和天地。我在太湖邊遇過一群羊,它們很悠閑地躺在那里,一直看著湖面,很安靜。它們有自己的世界。我在那兒看了很久,此刻的我跟它們差不多,我們都是來看湖的,我們沒有什麼不同。
太湖是博愛的,不管人類怎麼拆它,怎麼建它,怎麼摧毀它,它還是它。它包容我們,包容萬物,你們人類想在這里哭就哭吧,想挖就挖吧,想在這里看風景就看風景,想在這里就,想在這里睡覺就睡覺,你可以與它對話,也可以什麼都不說發呆,你可以跳進它游泳,你可以捕魚,也可以躺在礁石上。
異鄉漂泊多年,時常感覺真實的家離我越來越遠了。內心沒有安放之處,不管在哪兒,靈也是在流浪。不愿意觀察一塊石頭的美,不愿意看到一個水浪的美麗,甚至不愿意觀察一個黃昏。拍太湖其實是找回野性,找回自己,找回我與世界的關系。我跳進太湖,浮在水面上,眼睛和鼻子來,只能看到天和云,我在太湖之中。是太湖了我,拯救了我。在這里我找到了精神之地,我不再為流浪感到沮喪和懊惱。它讓我懂得寬容,懂得原諒。
2022年,宜興太湖邊休息的羊群2022年,宜興太湖邊休息的羊群
4
現在想來,如果我當時留在廣州,不繼續流浪,肯定買房了,娶妻生子了,最多換個報社,還是當攝影記者,生活不會有什麼改變。但我來到無錫,各種事情逼著你改變,沒有那段流浪,我不會決定拍太湖,不會找到自己的精神領地,也不會知道攝影的天地如此廣闊。
2013年10月,環太湖走了七八圈后,只剩下幾千塊錢,我覺得是時候回家了。一百多本攝影書送朋友,裝了些衣物和行李,開著我的小奧拓回到了湛江,然后又離開。2022 年,我又一次回到湛江,直到現在。
湛江仍然市井,還有很多傳統的、樸素的經營方式,比如七八個人騎著三輪車拎著竹籠子在街邊賣雞,熱氣騰騰的早餐攤,提著豬肉的居民,街邊拉臉毛的小攤,專門修理雨傘的地方……還有街邊的迷你裁縫鋪子,當地婦女戴著大沿白帽,坐在路邊,面前擺一臺縫紉機,街邊就可以改衣服做衣服。小店老板要外出,不會打印一張白紙黑字公告敷衍你,他們覺得不夠莊重,不夠嚴謹,非得找寫書法的鄭重其事用紅紙寫道,有事外出,休息5天,寫完還要放在太陽下晾干,特別生動。
很多熟人、很多鄰居、很多朋友在市井中相逢。它是一個充滿人情世故的地方。市井應該像賈樟柯一樣,吵吵鬧鬧,雜雜亂亂,有一種自由,野長,鮮活,無序中又有自己的道理。但是,這種市井正在非常快速地消失,服裝批發市場人變少了,有陣子村里都不讓養雞了,說是太臟了,要搞新農村。東海島也面目全非了,兒時的海灘、山林和村莊都不在了,說是要建設工業新城。一系列、填海、造廠,有時有些工廠還在偷偷排放,天空密密麻麻全是煙,我覺得,再這麼建下去,東海島就不是東海島了。
2022 年春節,農歷正月十六,游神隊伍經過東山老街,當天湛江東海島東山圩年例,隆重的民俗文化巡游活動
我開始拍攝《故園》,其實是故園最后的影像。我拍外婆家,外婆家拆掉了;我拍小時候摘野果的地方,也沒有了;我拍妹妹的傳統婚禮,她的家也消失了。
在很多城里人看來,東海島是個荒蕪之地,流放之地。這里仍然崇拜各路,有神,還保留著許多風俗。每次一艘新船入海都要進行祭海儀式,逢年過節還有很粗獷的人龍舞,一只蛇不小心被車碾死了,人們會把它掛在路邊,告慰它的離去。島民們表面彪悍,其實很良善,又特別崇尚自由,不喜歡那些規矩。我骨子里可能也是這樣的人。可是,隨著一切朝著城市化、工業化高歌猛進,過去的東海島也會成為一個過去。
每天我都在島上走來走去,有一天,走進同學的老屋,我發現他把很多照片都扔了。都是我們小時候的照片,畢業照,以前的學校,小時候的我們。它們泡在老屋的泥里,有些都被污水弄臟了,我撿起來,帶回家。后來我又去了大伯的老宅,走進去更驚訝了,兩相框老照片竟然都掛在墻上。我看到大伯年輕的樣子,看到堂哥堂姐年輕的樣子,還看到了堂弟年輕的樣子,看到了那個充滿了浪漫與理想的年代。老屋都是瓦房,時間長了沒人打理,屋頂都塌了。一個荒廢屋子的墻上掛滿了一個家族的回憶,卻沒人在乎。
我問堂弟,照片怎麼都沒人拿呢?他說,管這個干嘛呢?他們不是不在乎照片,而是不在乎以前的情感了。我覺得不可思議,人怎麼可以丟掉自己的記憶呢?我把那兩個相框都拿回家了。
大伯搬離村莊后老屋里遺留的相框 2022 湛江東海島
那時我才發現,東海島已經變了。大家都想著怎麼進城,怎麼發財,怎麼賺更多的錢。老房子還要它干嘛呢,趕緊到城里買房,在村里建新的樓房。我從無錫回來,搬到島上住,大家都覺得我是怪物。我媽覺得特別丟人,她認為一個人應該很有錢才會回家。
那感覺奇怪極了。在東海島的我,很像我曾經拍攝的城市流浪者,他們在某處,可又不在某處,割裂和懸浮感總是存在。我回家了,可是感覺還在流浪。
5
回顧十幾年的拍攝歷程,忽然發現我一直在尋找人的棲息地,一個是真正的、居住的家,一個是內心的家,精神的歸宿。所有的作品,一切的一切,落到最后就是兩個詞——流浪與回家。我始終在探討這些問題:人為什麼流浪?人又為什麼回家?人流浪的時候會找到家嗎?人回家的時候是不是也可能在流浪?
我拍下了自己所有居住過的地方,所有的我的家。之一張照片是在江南弄堂,那個住了將近五年的房間。離開的時候,我回頭,看到墻上貼滿了我的東西,被膠條貼住的棕紅色窗簾,掛在墻上的瓶起子,床頭放著的《攝影的智慧》,還有貼在床頭激勵自己的大大小小12張便簽,我依依不舍,給它摁了一張。
還有一張,拍的是另一個租來的房子,是房東夫妻當年的婚房。我去參加朋友婚禮,朋友把捧花送給我,希望我沾沾喜氣,我把它放在出租屋的桌上,一直放到我要走了。它自然枯萎了,我才發現,桌子左邊是男主人的照片,右邊是女主人的。
同事結婚當天送的花。出租屋桌子上還留著房東朱明囡夫婦的照片,據說這房子是他們當年的婚房 2022 無錫
后來,我又經過了很多出租屋,不斷地租房子,同時,因為我不在家,我爸把我的那一層樓全部租給別人。特別有意思,我們不斷在漂泊,別不斷在漂泊,我們不斷在換家,別在換家。
這可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從一個故鄉到另一個故鄉,永遠在搬家,換房子,我們的家成為別人的家,別人家又成為我們的家。我們的故鄉成為別人的故鄉,別人的故鄉也可能成為我們的故鄉。
一個年輕人在大城市生活,回到出租屋,并沒有回家的感覺,因為心在流浪。你知道自己不 于它,但也好像不 于故鄉。即使回到故鄉,你的生活方式已經跟故鄉不一樣,別人不接納你,你也沒法讓別人接納自己。你是很慌的,你不知道落在哪里才好。
我意識到,人總是需要一點什麼 我救贖。
是個船長,跑廣州到的貨船。從我有記憶起,他每次都是穿著西裝,拎一個皮箱,就離開家去廣州了。一去就是一年半載,有時候兩年才回來一次。我印象特別深,他每次回來和媽媽聊天,能聊幾天幾夜,好像他們的話說不完。我似乎從沒問過過得如何,我對他漂泊的人生一無所知。后來他退休了,回到故鄉,剛開始幾個月很好,半年就不行了。他適應了海上的生活,不知道怎麼跟別人去溝通,他和我媽剛開始還挺膩,后常吵架,最后都不住在一起了。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習慣,他所有的一切都跟我媽完全不一樣。
我特別能夠理解他,是這樣的,我也不過重復了他的路。
徹底搬回湛江前,我拍了一組照片,取名流浪人間,記錄那些在城市游蕩的人們:在飯店門口抽煙的幫廚阿姨,穿著不合身西裝行走在街上的白領們,坐在母親運貨車上的娃娃們,在大橋上鋪著涼席睡著的流浪者,酒場里彈吉他的女孩,在廣州 幫人運行李的工人,在高樓大廈前一片荒地上搭了簡易居所的人……
拍攝他們的時候,我一直在想,什麼是家呢?人類用金錢建造、堆砌了一個個小小的方格,并把這樣的與他人隔離的小方格稱為家。我們從出生起就住在這樣的小方格里,直到死去那天,又住進另一個小方格。
我想用照片記錄下有關我對流浪的感受,你會發現,不管走到哪里,或者不管在哪里,總有人想出去流浪,也總有人想要回家。人的一生注定漂泊,這是宿命,而回家也并不是流浪的終點。
「流浪人間」中的部分照片。
最近,我在拍個新的作品。我穿著當年的西裝,拿著他的皮箱,在整個東海島上行走,回到老屋。我 在被推倒的房屋廢墟上, 在村莊的溪流邊, 在巨大的香蕉林里,想象當年離家的心情。我以父輩的身份來告別吧,代表我,我以后也會成為。望著這一切,我在心里,再見了,故鄉,再見了,我的海島,再見了,我的過去。
那些還在異鄉流浪或者精神流浪的年輕人該怎麼找到自己的家呢?在這點上,我跟以前的態度有點不一樣了,不必回到故鄉吧。故鄉回不去,就真的回不去了。最重要的是,找到家人,找到愛人,找到同行者,還有自己的熱愛和追求。
有了愛就能建立一個家,建立一個家之后就可以落地生根,時間長了就是故鄉。我想過,如果遇到一個很愛我的姑娘,我也愛她,我可以跟著她,去哪兒都無所謂,有她的地方,就是家。
對了,我還想說的是,那個睡在廣州橋底下的大叔,后來也結束了幾十年流浪生活,他說,要回北方尋找他的家人了。不知道他現在過得怎麼樣,是不是真的回家了。
2022 年11月14日,湛江東海島,海邊一棵木麻黃樹。
以上就是與屬羊十四日出生命運好嗎相關內容,是關于東海島的分享。看完屬羊的哪天生日好后,希望這對大家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