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也有說“蚤子”)。”
這句話很多人都很熟悉,百度上隨便一搜“張愛玲經典語錄”,它肯定在其中。
但大家所不知的是,這是張愛玲18歲就寫出來的。它是散文《我的天才夢》中的最后一句話。
至今還有很多人在試圖解析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仿佛看到一個捂嘴偷笑,眼神犀利的少女:你們去猜吧。
18歲,在這樣一個大家都還懵懂青澀的年紀,張愛玲就已洞穿蒼涼世事,并用老辣的文字表達了出來。
這除了弟弟張子靜口中的“早慧”外,還有那種對文字特有的天才感悟力與掌控力,那是我們羨慕不來的。

詭異的是,張愛玲晚年真的受到了“蚤子”的困擾,讓她“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嚙性的小煩惱”。
這麼看來,《天才夢》的結語,還預兆了作者自己的晚年,難道天才的作家真的通“靈”嗎?
1985年, 身在美國加州圣迭戈的臺灣作家水晶,突然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張愛玲病了!》文中有這樣的描述:
“她自去年(1984年)起搬家,即染上了跳蚤。為了省錢,買了一只二手貨冰箱,跳蚤即從箱底繁殖,弄得她走投無路,連頭發也剃了,每日要洗頭,后來只得穿plastic(塑膠)衣服,再脫扔掉……。三天換一個motel(汽車旅館)。去看醫生,說她是心理作怪,然而每天晚上兩足會咬得紅腫。”

這是怎麼回事呢?她才剛過上不錯的生活沒幾年呢!
要知道,自從她1955年離港赴美后,日子過得一直不輕松。而且她還嫁給了又老又病又窮的左翼作家賴雅,這更是噩夢的開始。
雖然賴雅婚后對張愛玲很好,兩人也是個伴。但張愛玲得到的要比付出的多得多——她不但要經常照顧中風發作的賴雅,還要賺錢養活兩個人(賴雅當時基本只有每個月52美元的社會福利金)。
何況她的事業也并不順利。比起年少時在國內的一夜成名,美國的幸運之神并沒有垂青她——她的英文作品一直得不到美國文壇的認可。
她只有靠香港的宋淇鄺文美夫婦幫忙牽線,寫一些劇本賺錢。

張愛玲與丈夫賴雅
然而現實的無情還是一度擊垮了她。她付出全部心力,累到眼睛出血而寫作的小說《粉淚》遭到美國出版公司退稿,而且退稿信中的言辭讓人難以接受:
他們說小說“所有人物都令人反感”,且“squalid(骯臟)”。收到信的張愛玲一下子病倒了,打了好幾針維他命才算緩過來。
她后來在1958年打算寫長篇小說《少帥》,以張學良為主人公,甚至還跑到臺灣去想采訪張學良,并搜集素材,結果自然是碰了釘子。
回美國后,不幸的消息再次傳來:宋淇所在的公司倒閉,他不得不另謀出路。因此張愛玲的編劇生涯也隨之終結。
她收入銳減,又要給賴雅治病,后來只有搬到了黑人社區的廉價住房……

后期賴雅大小便失禁癱瘓在床,張愛玲只能一邊在學校打工,一邊寫稿,一邊還要照顧賴雅。她在那段時間,心中的小說夢和紐約夢都漸漸褪去鮮艷的色彩,變得模糊不清了。
1967年10月,賴雅病逝。張愛玲雖然有所失去,但同時也得到了解脫。
1970年代,也就是賴雅死后的幾年,“張愛玲熱”逐漸在臺灣升溫,之后香港、大陸也受到影響。張愛玲的版稅日益豐厚,生活也隨之有了極大保障,她終于不用再接那些她不喜歡的活干了。
也許張愛玲命里真的與愛情八字不合,從開始的胡蘭成,到后來的賴雅,但凡是攤上男人,她都被折磨得千瘡百孔;離開男人,她自己一個人時,反而好運就會降臨。

張愛玲與第一任丈夫胡蘭成
看來她來這個世界的使命,就是寫作,而且必須心無旁騖。誠如她自己所言“我現在寫東西,完全是還債——還我自己欠下的債,因為從前自己曾經許下心愿”。
沒想到她剛在美國站穩腳跟沒幾年,蚤子這個不速之客又闖入了她的生命,簡直猝不及防。
1980年代,“張愛玲熱”在整個華語世界成蔓延之勢,然而大洋彼端的張愛玲本尊卻無暇顧及這些,因為她正在進行著一場漫長的“人蚤大戰”。
這場“戰爭”耗時長久,令我們的才女精疲力盡。但在旁人看來,這更像一出無厘頭的鬧劇。
1983年10月26日,她在寫給臺灣友人莊信正的信中,首次提到了跳蚤和搬家的問題。且在此后的四、五年里,這兩件事竟成了她生活的主題。

張愛玲的臺灣友人莊信正
因為在家中發現了跳蚤,她不得不搬離居住了11年的那間公寓。然而第二年的1月,莊信正又收到她的信,她說:
遷到新居所后,沒想到冰箱底部的保溫層里帶來一種特別厲害的跳蚤,用昂貴的特效殺蟲劑連續噴殺了兩天,“都毫無效力”。
從那時起,張愛玲就開始了頻繁搬家的漂泊之旅:幾乎每天換一個汽車旅館,一路都在扔衣服、鞋、襪和箱子,之后又采購便宜的補上……
人在紐約的莊信正見朋友陷入如此境地也是愛莫能助,因此拜托了與張愛玲同在洛杉磯的,從事建筑生意行業的朋友林式同幫忙照顧張。
于是林式同從那時起,就承擔起了往后10多年照顧張愛玲的責任。而令人吃驚的是,在這10多年中,林式同只見過張愛玲兩面。

張愛玲晚年最信任的人——林式同
因為張很怕與人面對面接觸,她更愿意通過電話或寄送信件等方式。林式同一開始并不知道張愛玲是誰,因為他不太關注文學領域,他只是照莊信正所拜托的去做罷了。
他幫張愛玲找地方住,但是她總稱有跳蚤,而又重新踏上住旅館的逃亡之路。期間她也去看醫生,醫生給開的藥膏總是過一陣就失效,她的雙腿還是不斷變得紅腫。
在不斷搬遷的過程中,張愛玲的寫作事業被迫荒廢,此外她還丟失了《海上花》的英譯手稿和身份證件等重要物品,而朋友寄去給她的信件也經常是有去無回。
大家都很擔憂,紛紛猜測她口中所謂的“蟲害”是否是她得了癔癥,還是長期飲食不良引起的幻覺,亦或是精神出了問題?

1986年,經過宋淇、夏志清等友人的共同努力,多方聯系,終于在洛杉磯找到了一位名醫。他們急忙寫信推薦給張愛玲,讓她去看病。
兩年后,張愛玲來信,她的病終于查出原因了!
原來她腿紅腫的毛病最初確實是跳蚤引起的,但是它們早在兩三年前就沒有了,后來是她的皮膚敏感在作祟,涂了那位名醫給開的藥膏后,癥狀很快就基本消失了。現在她已經搬到了新的房子定居。
這就蹊蹺了,跳蚤兩三年前就消失了,張愛玲怎麼還一直覺得它們在騷擾她呢?
有人說是和她的心理有關,但她本人一再否認。不過詭異的是,在她生命的最后7年中,她仍然不時受到跳蚤的困擾。

林式同作為與她晚年接觸最多的人,在《有緣識得張愛玲》一文中,說張怕蚤子,“完全是心理作用”,是她“疑心生暗蟲”。
此外,林在文中還寫了這麼一句:
“不可思議的事是:在她十年前第一次給我的電話里,說要搬家的原因,和去世前給我的最后一通電話里,說她舊病復發,都提到蚤子,都和蚤子扯上了關系。”
1995年,也就是張愛玲去世那年,她的皮膚病再次發作,且侵入了耳朵,連衣服也不能穿,每天要照13小時的日光燈……她在7月25日寫給宋淇夫婦的信中這麼說:
“頭發長了更成了窠巢,直下額、鼻,一個毛孔里一個膿包,外加長條血痕。照射了才好些。當然烤干了皮膚也只有更壞,不過是救急”。

為何張愛玲會在生命的最后十幾年中總是跟“蚤子”過不去呢?
也許她確實被蚤子叮咬過,之后只是后遺癥引起的皮膚過敏罷了。但她總不時地說有蚤子,問題連醫生都說蚤子早就沒有了呢。
我想其中更深層次的原因,應如林式同所說,是心理問題。她早在《天才夢》中就說了,“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嚙性的小煩惱”。
她將與人交往,看成是被蚤子叮咬的煩惱。這應是源于其原生家庭的不幸福——她將父親與后媽的家比作“墳墓”;她在《小團圓》中,以母親為原型的角色是一個有眾多男友的輕佻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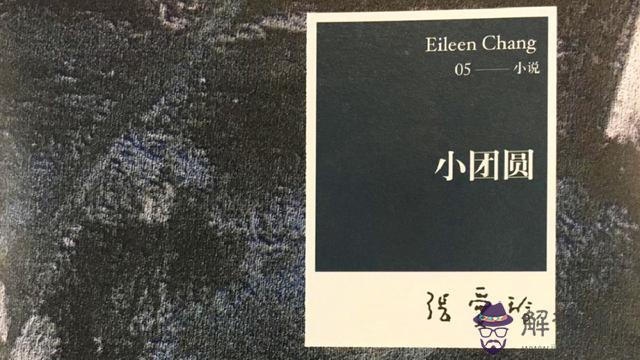
原生家庭對她造成的傷害,導致其在人際交往中感到不適應,不舒服。她把自己與世界隔開了,活在屬于自己的真空中,任思維去天馬行空。
她視與人打交道為麻煩,潛意識中將它與咬人的蚤子劃等號。但因為生活中總是避免不了和人打交道,所以她覺得蚤子無處不在,總是騷擾她。
1994年秋,臺灣《中國時報》授予張愛玲“特別成就獎”。作為回應,張愛玲拍了生前最后一張照片,寄給《中國時報》發表。
照片中她頭戴假發,面容蒼老且清瘦,手持一份報紙。

張愛玲生前最后一張照片
此外,她還要求發表她最后一部作品《對照記》的皇冠出版社將這張照片放到再版《對照記》的最后一頁,并附上了一段說明,這是她留給世間的最后一點文字。其中包含一首詩,曰:
“人老了大都
是時間的俘虜,
被圈禁禁足。
它待我還好——
當然隨時可以撕票。
一笑。”
次年9月,張愛玲被發現獨自在家中平靜離世。她躺在行軍床上,臉朝外,頭發很短,手和腿自然平放。遺容安詳,只是出奇地瘦。保暖的日光燈在被房東發現時還亮著。
9月30日,林式同及友人乘船,將張愛玲的骨灰撒向了浩瀚的大海。因她生前所立遺囑中提到“骨灰應撒在任何無人居住的地方”。

海葬任務完成后,林式同(左三)和其余出席人員在船塢合影
總的看來,命運待張愛玲如她自己所言,“還好”。她雖一世漂泊,孤獨終老,但這是她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她未必覺得不好。而職業呢,她也從事了自己所愛的。
在那個年代,做一個自己養活自己的獨立女性是非常不易的,張愛玲年少時就不喜歡跟別人要錢的感覺,她想要自己掙錢自己花,像姑姑那樣,清爽、利落地生活。這一點她也做到了。
所以,一切“還好”。

(全文終)
您的點贊、關注、轉發是對我最大的鼓勵!雪梨期待與您一起交流探討,非常感謝!
備注:圖片來自網絡,侵權必刪。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46173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