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
現在我們知道,中國八大菜系中最流行的非川菜莫屬,即便在海外,晚清民國時期一枝獨秀的粵菜,現在也應該已退居次席讓位于川菜了吧。其實,在民國時期,川菜也有風頭直逼粵菜之勢,而且出圈(川)也比粵菜更早,故曾作《民國川菜出川記》刊于2018年7月14日的《上海書評》。近三年來,繼續發掘一手文獻,積累漸多,也更了解晚清民國川菜在全國的發展流行情況,及其贏得“標準國菜”殊榮的故事,故值得再撰一文,談老上海的川菜館。以就教讀者方家,文獻方面,則力避重復引用,有興趣的讀者自可查閱前文。本文為下篇。
上海的閩川菜館與粵菜館的起家途徑迥異——粵菜館從物美價廉的宵夜館做起,川菜館則一開始就走昂貴的高端路線,但往往高處不勝寒,特別是在“更新迭代”,遭到蓄勢而來的粵菜的強勁挑戰之后,上海川菜館在三十年代后漸趨低落。但是,關上一扇窗,打開一扇門,在粵菜漸趨發達高端時,其據以立身起家的“物美價廉”的后院,卻遭到了川菜最強勁的挑戰。
上海作為遠東第一都市,雖然商業經濟發達,但富裕階層畢竟是少數,古往今來都是如此,而大多數中下階層也要解決飯館吃飯的需求問題,如何因應他們的需求,“食在廣州”就是很好的啟示:廣州固然有像大三元六十元一位的昂貴的魚翅,也更有無數的從二厘館到大茶樓的供給廣大市民階級的價廉物美的飲茶食飯之處。其實如果認真觀察,上海也不例外。比如上海數量最多生意也最好的,就是那種專為苦力黃包車工人而設的“六個銅板一碗飯,五個銅板一碗菜”的本地館子。聚集在在愛多亞路與北四川路武昌路一帶“兩角小洋一碗臘味飯,一角半錢一盤辣椒炒肉絲”的廣東館子則次之,那是瞄準中小資產階級的顧客,基本維持上午不營業而晚上通宵營業的宵夜館風格。但奇怪的是這兩種號稱價廉物美的小館子,卻也學了上海的壞脾氣,竟然還要學著大飯店收小費,“因此不能說是純粹的經濟飯館,而能稱為純粹的經濟飯館的,那就是四川館子了”。
那這種四川經濟飯館如何能別具一格?因為他是沖著學生來的,這簡直讓人“懷新”(懷念新時期我們的讀書時代),故愿多引一段時人的文字,定能引起廣大的讀者共鳴:
上海的大學都是由學生自備伙食的。因此,這一種飯館應著學生的需要而產生。他們不收小賬,飯菜的價錢在一起,多半是每元錢買七張飯票,一張飯票吃餐飯。一餐飯的菜是有規定的,大概是一菜一湯,菜有多種的樣式,由客人隨著自己喜歡的而點菜,他們常備的菜,如家常豆腐,回鍋肉,青燉肉絲之類,你喜歡吃那樣的菜,就點那樣的菜,吃完之后,給一張飯票,什麼事也就完了,是非常簡短爽快的。
在當時,特別是國都定鼎南京以及遷都重慶之后,上海的大學堪稱全國第一,市場既然廣大,以致本地幫、廣東幫都聞風擠入這一市場,不過為著招徠起見,自然仍稱四川飯館。更重要的是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即隨著這種四川飯館的發達,“有許多家庭為了省事起見,也在這一種飯館里包飯了”。(本節開頭各段所引,均見《上海的經濟飯館》,《大公報》上海版1936年8月8日,第13版)
其實,延至今日,川菜館競爭之道,仍然是以價廉物美取勝的。而隨著經濟稍一不景氣,“價廉物美”是連中高檔餐館也不敢或忘的,那就“和菜”的流行,但和菜也是粵菜特別是川菜館的天下:
“和菜”,等于北平山東館子的“自磨刀”,一元兩元以至四元五元,可以一聽客便。不過普通的和菜,尤其是“北京館子”,五元以下的粗的不能入口,其口味還及不上東安市場的潤明樓。但此間幾家川菜館粵菜館的出品則都能令人感到舒服,比起北平的大陸春、新廣東來新鮮而適口了。(陋公《上海的飯食店》,《大公報》上海版1936年5月26日第12 版)
同時人們發現,經濟不景氣所造就的這些川粵經濟飯館,才是真正的川粵菜館的全盛時代:
以前,吃便飯多往小飯館去,樓下講錢碼,一碗咸肉豆腐湯,一碟爛糊肉絲,白飯兩盅,所耗只不到半塊錢,在當時可算無上便宜了,但后來有幾家廣州菜社,就樓下辟經濟小吃部,每只菜只二角至三角,雞鴨魚蝦,應有盡有,對于三四人合共小酌,是最相宜的,所以一校經濟朋友,多舍小飯館而去光顧廣州菜,一時四馬路浙江路一帶,接連開著十多家,為粵式酒家的全盛時期。
后來三馬路上,又開了幾家川菜小吃店,本來川菜在上海是最高貴的,自幾家便飯館開幕后,漸由貴族化而轉變到通俗化,化一元左右即可一嘗蜀中異味,而三四角的一種客飯,更是無上經濟實惠的。(淑君《市面不景氣 經濟小酌風靡一時》,《大公報》上海版1936年7月26日)
我們再搜羅一下從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后期這十年間上海川菜館的歇業開業信息,大多因貴而歇而廉而興。
1928年,曾經有名于時的共樂春川菜館歇業改組了:“共樂春川菜館,前以主人勞介眉,虧款停辦。房東哈同,以生財抵房租,乃復由王翊宏等改組協記續辦……”(紅,《晶報》1928年11月9日3版)
像《成都大新樓川菜館開幕盛況》,一看標題,以為是什麼大酒樓,再一看內容,原來不過是“三馬路成都大新樓便飯處”,盡管聲稱“館中廚師系專聘川中名手,選菜出菜,純照成都辦法,而菜味尤屬川味中之杰出”,其實都是些普通的大路菜:“其中辣子雞丁、雞油絲瓜、醬燒茄子、衛生豆花,尤深得客人贊許。”(《新聞報》1929年8月13日2版本埠附刊)
從奢華向經濟型的大勢,早期豪華川菜館都益處老板廖海澄的際遇最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由于奢華路線難繼,他在1928年將菜館出讓給秦廣記:
據都益處廣記川菜館號東秦廣記聲稱:都益處川菜館開設上海愛多亞路,前號東廖海澄無意經營,憑中情讓盤與秦廣記名下,計大洋二萬一千五百元,自本年陰歷八月十六日起歸廣記繼續營業,所有從前都益處或廖海澄名義人欠人往來賬目及代人作保等事均歸廖海澄君負責理結,與都益處廣記無涉,合行代為登報通告,此啟。(《蔣士料律師代表都益處廣記川菜館啟事》,《申報》1928年9月29日第6版)
接著就在即將開業的大中華飯店的開辦川菜部:
大中華飯店開設上海四馬路跑馬廳,謹擇于夏歷十二月初六日先行交易……聞前都益處主人廖海澄君烹飪精美,海上馳名特聘其承辦本公司筵席菜點,以便旅客各界諸公盍興乎來。(《申報》1929年1月11日第1版)
聽起來好像格調不俗,但事實上旋即打價廉牌了——“每客僅取五角”,較之都益處時代每客動輒二三元以上,相去數倍:
大中華川菜部,系軒茀康律師分事務所主任程樹芝及前都益處主人廖海澄所組設,布置之美暨烹調之精,早為滬地人士所贊許。今春起內部復大加改良,添增客飯,每客僅取五角,藉次普及,故日來座客常滿 ,大有應接不暇之勢云。”(《大中華飯店川菜部擴張營業》,《新聞報》1929年2月16日第16版)
可是,愣是這樣還是開不下去,不久又轉到南京飯店去了:
本飯店在英租界山西路(即盆湯弄)特建七層大廈,辟二樓開設南京川菜社,由廖海澄君承辦……(《南京飯店啟事》,《申報》1932年7月10日第7版)
當然仍是主打經濟廉價牌:
……大宴則珍錯畢陳,小食則蒸炸都全,點心特制……定價格外克已,敢保來賓滿意而歸。現擇于今日與南京飯店同時開幕。(《南京川菜社澄記開幕露布》,《申報》1932年9月16日第1版)
盡管如此,也只開了三四年:
四川人廖海澄,前在本市開設都益處川菜館,因營業不振,出盤與人,后承包山西路二百號南京飯店內附屬之川菜部營業……亦因營業清淡,于上年底總結賬時停歇……(《前南京飯店川菜部賬房章遠帆遭暗殺》,《申報》1937年6月26日第1版)
看來,不能真正放下架子,做真正的經濟川菜,是做不下去的。因為走經濟路線,所以很多川菜館紛紛開了出來,單搜羅在報章打廣告或軟廣告的,已見不少。如1929年5月5日云南路云南樓川菜館開幕廣告說:“春樓家老四亦為一股東,四年前加入美麗川菜館,未能愜意,喪其資斧,今又再接再厲,達到目的,惠然軒之外,已無多讓,改良川菜,亦迎合時尚之一也。”(有鬼《廿五兩件事:魔術照相云南樓川菜同日開幕》,《瓊報》1929年5月5日3版)這里面點到了好幾家川菜館,所謂“已無多讓”“改良川菜”什麼意思,無非求其經濟適口耳。再如六合居川菜館說開設英法兩界二十余年,今夏由大世界移至廣西路民和里口,“因陋就簡,未便率爾正式開業,現因東川名司到齊,特訂于九月二十八日正式開張”。(《六合居京川菜館正式開張》,《新聞報》 1929 年 11 月 9 日,第16 版)所謂遷址重開,“因陋就簡”,也是要走經濟路線了。三馬路慕爾堂對面的玉壺春四川菜館更直接宣告“定價低廉,桌菜格外從豐,小吃尤為便利”,并稱這正是“是川菜館中之特色”。(《玉春壺川菜特色》,《時報》1930年12月8日6版)二馬路永安公司后面悅來川味小食館在“吹水”說是“四川廚司專聘到申,新增坐位門面刷新,應時小菜烹調鮮”,然后卻最直白地告訴你有多便宜多經濟:“特備餐券,每元三張,招待周到,歡迎來賓。”(申報1931年5月3日,第19版)也即說一元錢可供三人吃一頓,較之前述都益處原老板開設的大中華川菜社每客五角,又廉價了百分之十幾。還有無名小館,取值就更廉,味道也不真的必差:“川菜味美而直昂,小酌不便。有川味小吃處者,在寶善街怡園下層,緣石級上,別有洞天,烹調不下陶樂春、都益處等川菜館,而取值僅及其半。主人蔣鵬程司割烹,李樹青司招待,尤無川館隔閡之弊。”(吃, 《晶報》1929年4月24日第3版)三馬路廣西路口的峨眉川菜館,突出“菜點一律小洋”,也是一種經濟的表現。(《社會日報》1932年9月8日,第2版)
往川菜館靠攏的滇川菜館,走的也同樣是經濟路線:“呂班路麥賽而蒂羅路口、新開之潔而精之滇川菜館,其庖人為滇中某巨室家廚,所制各菜,鮮美精致,別有風味,其最著名之炸松針、翠湖魚、醍醐豆花等,即在滇中,亦甚名貴,且肴饌清潔,取價低廉,夏令小食尤極相宜也。”(《東方日報》1932年7月6日第1版)
因為價廉物美,食客自然趨眾,同時開設成本自然也低,遂有“小規模川菜館大盛”的報道出來:“近日,小規模之川菜館大盛,麥家圈雙鳳園內,有云記及滬海春,五馬路沿有川味香……”(《晶報》 1929年5月24日第3版)風氣之下,至有粵菜館改川菜館的現象,如珠江路中珍珠橋川菜館梅花酒館即為原來的粵菜館改成。(《梅花館改營川菜》,《中央日報》 1935 年 12 月 8 日第7版)
食客趨眾的另一體現,是很多高大上的宴集活動,都愿意“屈就”這些名不見經傳的經濟飯館了。比如四川旅滬記者協會的聚餐例會,就假座華格臬路成都川菜館。(《兩團體商救川災 籌組募振川災游藝會》,《大公報》上海版1937年5月1日第7版)上海五卅中學的教職員聚會,也選擇在大西洋川菜館舉行。(《校聞:教職員舉行聚餐會》,《五卅校刊》1936年第4卷第26期,第2頁)大世界西華格臬路的蜀蓉川菜社這種小菜館,敢“邀本埠新聞界往嘗試佳肴,到者二十余人,表示滿意而散”,真有小鬼當家的味道。(《蜀蓉川菜社昨招待新聞界》,《新聞報》1936年11月7日第15版)再則四馬路口的成渝川菜社上海分社(按該總社在南京)開幕典禮聲勢似頗盛大,請了“名票李元龍播送平劇”,因為活動在電臺搞,其實成本也高不到哪兒去,最關鍵的他們還是以價廉吸客:“其名產有特制之蜀中著名渾漿豆花,清涼可口,每份僅售一角……”(風流道人《名票李元龍播送平劇:成渝川菜社開幕,假座于華興電臺》,《游戲世界》1936年7月29日第3版)
經濟川菜的盛行,形成了川菜的代表菜“四川小炒”,并與“廣東燒烤”“北平清燉”并稱為“中國食譜上的‘三絕’,也可稱為‘國粹菜’”。還說特別適合年青小伙子偶約二三友人聚餐,“化錢不多,而且津津有味”。甚至說以前小炒不興的時候,偌大一個上海市,稍出名川菜館“只有聚豐園、榮記二三家,而且蜷伏在衖堂里不敢出世”,“這幾年來陸續添了陶樂春、錦江、小花園、經濟、重慶樓、蜀蓉、成會,總共不下二十余家。小花園附近,及華格臬路,差不多成了兩個川菜區呢”!(子明《四川的小炒》,《大公報》上海版1936年11月15日,第15版)
文章中提到的經濟川菜社曾經在《社會日報》連篇累牘地打廣告,似乎確實價廉而物美——“特設經濟菜,每客售洋四角,連飯在內。”(《經濟川菜社開業》,《社會日報》1935年3月22日第1版)“漢口路六九八號經濟川菜社,營業極為發達,擬于端節中擴充范圍……(《社會日報》1935年5月30日第1版)三馬路廣西路西的經濟川菜社,不知同名還是別一家,號稱”海上著名川菜館,素有標準川菜之名,該社主人,交游素廣,營業蒸蒸日上,現屆周年紀念,內部大加革新,并將門面擴大,菜肴佳妙,早已有口皆碑,現應社會需要,特備大盆小盆二種,價目奇廉,凡欲嘗物美價廉之菜肴者殊有一試價值”。(確,《晶報》1936年3月23日第4版)自詡如此有名,取價確又如此奇廉,大概只有川菜館才做得到吧。凡此種種,比較起1929年5月成立的上海三馬路大舞臺西首大新樓川閩菜館,還沿襲早期的套路,稱“何妨嘗川閩異味”(客,《大晶報》1929年6月9日第2版),實在已經是通過走經濟實惠路線而“換了人間”了。
從戰時孤宴到戰后繁華
1937年8月13日,日軍啟釁,上海漸漸淪陷,而租界尚存,繁榮不盡,出現所謂孤島時期,川菜館也因應變化,姑可名之為“孤宴時期”,因為似乎有超越經濟小炒,重回豪華貴氣的趨向,而且也似乎是成功的:
上海之有高尚川菜館,以前只有陶樂春、都益處、美麗等三數家,八九年前,三馬路一帶開了不少川幫飯館,規模并不大,可是他們以“家常便飯”為標榜,很合上海人的口胃,所以營業甚盛,陸續開出的,有數十家之多。
不過這種“便飯館”,風行了沒一兩年,風氣又變了!在三馬路和小花園一帶,接連出現六七家富麗堂皇的川菜館,其間以蜀腴、蜀蓉、成渝、小花園、聚豐園等幾家最出名,相隔不多時,大世界西首開了一爿“錦江”菜社,里面布置的精雅,設備的富麗,可稱獨具匠心……除錦江以外,蜀腴,小花園等幾家,設備布置,也相當講究,像現在夏天,多裝有冷氣,顧客都是上流人物,無論小酌或整席酒菜,并不算貴,宴請客氣的賓朋,最為相宜。
文章還進一步比較稱:“上海是五方雜處之所,所以各幫菜館酒店,也分成若干幫口。蘇幫、徽幫、本幫規模較小,京幫菜館派頭很大,只是時至今日,京菜館的地位已漸降落,被幾家川菜館取而代之了。”(紅絨《上海的川菜館》,《錫報》1938年7月28日第3版)據此,大體可以說這種轉型是成功的。 剛開業時聲明要走廉價路線的蜀腴,也迅速向高檔方向轉型,比如著名的狀元實業家張謇之孫張融武的大型豪華婚宴都設在那兒,就很可以說明問題:“是日來賓到者極多,梅蘭芳也趕來道賀……”著名戲劇史評家張古愚并作一趣文《聽了予倩一席話省落蜀腴三碗飯》(《十日戲劇》1938年第1卷第23期)以記之。而且其盛況一直延續到戰后。比如1946年4、5月間,遷回上海的新民報主持人陳銘德、張慧劍等,就是在蜀腴招待上海各報社巨子,其中也包括新聞界的老饕嚴獨鶴。(老莊《蜀腴伙計“久仰”嚴獨鶴》,《風光》1946年第9期第3頁)也可以說終民國之世,蜀腴都是滬上川菜名館:“地道川菜,馳名全國,價廉味美,譽滿滬濱。設備現代化,招待周到化,既聞名而來,必滿意而去。”(《蜀腴川菜館》,《大眾夜報》1948年5月3日第1版)川籍文化大家唐振常先生對蜀腴所葆持的川菜傳統,印象尤為深刻:“寫到川菜,蜀腴為正宗。一九四七年,劉文輝將軍駐京代表范樸齋宴上海新聞文化界諸人于此,難得的是,全桌沒有一樣辣的菜,保持了四川人正式宴客絕無辣菜的傳統。”(唐振常《鄉味何在》,載《雍飧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頁)顧頡剛先生的戰后上海之行,少記飲食之事,但就曾兩記蜀腴之行:
1946年9月17號:到蜀腴赴宴。
1946年10月16號:到蜀腴應宴。
另有兩次錦江之行:
1949年5月15日:到雁蕩路錦江菜館,晤振宇等,吃點。
1949年7月9日:到寧海路錦江川菜館赴宴。(《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五卷第719、727,第六卷457、484)
當然,川菜館取代京菜館不算啥,幾欲取代粵菜館,那才真算得上牛氣:
粵川兩幫——上海的菜館,當以廣東幫勢力最為雄厚,近年來四川菜館,因了菜肴的鮮美,恰合于上海居民口味,生涯大盛,大大小小的川館,開設了不少,與廣東館同為上海菜館兩大幫,雄視同行,到處可以見到……四川館以前,都益處曾震動了全上海的老饕,現在卻已普遍開設,如聚豐園、蜀腴、金剛等,都很著名,所有的菜肴,有特殊風味,滋味鮮美,勝于廣東菜,因能雄峙于上海的菜館業中。(南宮《上海菜館的陣容》,《總匯報》 1939年11月23日第3版)
在此期間成長的幾家川菜館,還發展成了后來的歷史名店,如:
潔而精川菜館:雁蕩路82號,1937年,供應獨具一格的上海美味川菜,發揚百菜百味特色,吸引了中外賓客。
綠野飯店(原名綠野新村):淮海中路689~695號,1937年,經營川揚幫菜肴,特色菜點有魚香肉絲、麻辣豆腐等深受消費者歡迎。
其中綠野飯店還培養出一位川菜大師:“林萬云,1922,綠楊村,特級川幫烹調師。”創辦于1938年3月的威海衛路梅龍鎮酒家(1942年遷南京西路1081弄22號),則更加故事豐富:菜館的得名既源于京劇《游龍戲鳳》中的一面旗幡,其與戲曲屆結緣也自在情理之中,比如“越劇十姐妹”曾在此舉行結拜儀式,上海的文人雅士也每每聚首于此,并一度成為中共地下組織和文化界進步人士進行秘密活動的場所。特別是,因其首創香嫩滑爽、清鮮醇濃的“海派川菜”,成為政府的重點接待點,周恩來總理也曾于1958年7月14日光臨做客。(《上海飲食服務業志》第一篇《飲食業》第七章《名店名師》,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版)
不過,盡管有高檔川菜的畸形回潮,但形勢比人強,總體經濟形勢是下降的,經濟川菜肯定會繼續“發揚光大”。所以,1938年1月13日開幕的浙江路小花園川菜社,標價更廉:“經濟小吃,每客三角一菜一湯,每客五角二菜一湯,連飯在內,奉送香茗。”(《小花園川菜杜》,《杜會日報》1938年1月14日)但這小花園可不是普通的經濟川菜館,而是號稱川菜大王的啊;能天天在報章打廣告,也是實力的體現:
本埠浙江路小花園二一一號小花園川菜社,為滬上最完美之川菜社,堪稱“川菜大王”,蓋以該社無論在烹調,設備,裝璜各方面,均別創一格……(《川菜大王小花園川菜社》,《力報)》 1938 年1月23日第4 版)

春節宴客請到浙江路二一一號小花園合記川菜社……(《川菜大王》,《東方日報》1938年2月19日第3版)
而且輿論也認為他們當得起“川菜大王”的稱號,并有名家共贈此牌匾的盛舉:
”八一三”戰事開始,滬上商業大受影響,就是菜館業當然也不能例外。
昨日我與知友數人,聚餐于小花園川菜,到了目的地卻出我預料之外,早已宣告客滿,經他們經理嚴逸星君特別設法,勉強得一立足地,其盛況真是空前了。
……
前日海上各彈詞名家共贈扁額一方,上書“川菜大王”四字,這說得一點也不夸大,至少在上海的川菜館中,川菜之王,受之無愧矣。(《請問川菜誰家好,上海有小花園》,《東方日報》1938年2月27日第4版)
當然這也可以并行不悖,就像股票可以百酒齊跌而茅臺獨漲,有高檔川菜館滿日偽上層之畸形需要,有經濟川菜館滿足廣大市民普通需求,反而能使川菜館更健康發展。同時,也不妨礙知名川菜館的豐儉兼顧,比如蜀蓉川菜館也開賣經濟早點一樣。(《蜀蓉川菜館經濟早點》,《時報》1938年4月12日第6版)
特別是到了戰爭后期,整個國家因為戰爭的耗竭,生活水準大大下降,辣椒咸菜,最是下飯“利器”,所以上海經濟川菜館大有因國難而再興的意味,看看后期層出不窮的川菜開業廣告即可見一斑。比如1944年4月蘿蔓飯店盛記開業自稱“名廚調制川菜”;西藏路金谷飯店西藏廳強調“正式川菜,硬派作風,沒有音樂舞池歌唱,完全在吃頭上講究”;五星小餐、大觀園相繼開業均宣稱主營川菜。(《社會日報》1944年4月30日、9月18日、12月23日、12月27日)就像時下因為經濟下行及電商和外賣等的沖擊,很多飯館轉手頻繁,當時也是,但轉來轉去,還是轉成川菜的多,比如蜀云就是:“一年以來新仙林之花園酒家,凡三易其名,去年下半年后稱寧波味圃,近數月來又改川菜,則招牌為蜀云小餐矣。”(唐大郎《蜀云小餐》,《繁華報》1945年6月11日,收入《唐大郎文集》第8卷《西風人語》,上海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44頁)
由于“各省人士在大后方住久,習慣麻辣,還有后方生的川娃兒,沒有辣椒不吃飯,形成川湘云貴各省的飯館到處風行,變成一枝獨秀了”。(唐魯孫《吃在上海》,載《中國吃》,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頁)等到戰勝來歸,上海的川菜館自然較前大興,并特別突出正宗四川特色。比如四川人王興,就跑上海來開一間川菜館“上海酒樓”,開設廳房二十余間,并效法廣東餐館設大禮堂和火車椅,自然也標榜“正宗川菜”。(《商業小志》,《大公報》上海版1946年7月28第5版)并在開幕廣告中稱自己正宗到“與重慶之九華源、成都之姑姑筵同稱三絕” ,因而“賓客盈門,盛極一時”。(《上海酒樓開幕》,《申報》1946年8月6日第4版)還敢夸口說上海酒樓“味勝重慶‘九華源’成都‘姑姑筵’”。(《正宗川菜松風夜宴風味獨特》,《申報》1946年8月7日第9版)上海警備司令曾假座宴客,可謂宣示上海酒樓地位的標志性事件:“宣司令指示剿匪七辦法,晚七時,宣司令并在江寧路凱歌歸上海酒樓歡宴出席各官長。”(《確保滬郊各縣治安 舉行十縣警備會議》,《申報》1947年5月11日第4版)只不知是上海樓何時又結緣著名的重慶川菜館凱哥歸了:“‘凱歌歸’以前在重慶便是頭等的酒菜館,勝利后到上海來,如今也打定基礎了。主人為黃埔軍人李岳陽,極好客。”(易秋《川菜和湖南菜》,《小日報》1947年12月2日第4版)
很有意思值得特別提出的是,除了沿自戰前的錦江飯店的女老板董竹君,新開的好幾家川菜館都是女子掌柜,依稀可見文君當爐的傳統:
近年來比較時髦的川菜館,都在靜安寺路,梅龍鎮開設已久,去年開了一家南海飯店,今年又開了一家上海酒樓,最近西藏路的金谷飯店,辟了一個四海廳,專售川菜。南海的主持人,不知是誰?梅龍鎮,上海樓以及四海廳,卻都由女人在經理著。梅龍鎮的吳湄,是戲劇家……四海廳是由新聞業前輩張竹坪的夫人做“擋手”,張太太從前在內地也開酒菜館,所以這位“擋手”原是老手。上海樓則是二位朱小姐,她們都是畫家,也都是唐云的學生。(陶甄《川菜館之“女掌柜”》,《誠報》1946年8月28日第3版)
稍后《申報》1947年1月16日第9版《“吃”在上海特輯:異軍突起的川菜》也特別提到了川菜館“文君當爐”的形象,只是記述略有出入:
川菜館里,女老板獨多,錦江經理董竹君,原籍江蘇,于歸四川,故以川菜聞名。梅龍鎮上座客,頗多藝術界中人物,這是因為女主人吳湄,有聲于話劇界的綠故。新仙林隔壁的上海酒樓,也是女主人,乃畫家朱爾貞朱蘊青所設立,藝術家和川菜有緣,她們都是有修養的人,經營方法,當然與眾不同。
后來聲稱經營“正宗川菜,標準西餐”的四姊妹飯店,老板也應該是女老板當家吧。(《四姊妹大飯店》,《力報》1947年4月21日)不過《“吃”在上海特輯:異軍突起的川菜》中提到川菜館“揚點川菜”的特色,更值得我們重視:
近來揚點和川菜,好似結了不解之緣,有幾家川菜館,像綠楊村等,大都兼賣揚州點心,“揚點川菜”,合為一詞,人人皆知。
川揚并舉,確乎一時所尚:“西藏路中爵士渝園餐廳改組就緒,延盧欣甫任總經理,并自成都聘來名廚司,昨日起重行開幕。川菜揚點之外,且售咖啡茶座。”(《申報》1947年2月11日5版)“四川菜肴,邇來為滬上最時髦之食品,紅玫瑰菜社,以新派作風,創設于亞爾培路回力球場對門,專制川菜冷飲,揚州點心……”(蕭蕭,《和平日報》1947年3月29日第5版)著名的梅龍鎮酒家,也標榜川揚菜,唐振常先生則認為“多少已上海化了”。(唐振常《鄉味何在》,載《雍飧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頁)綠野飯店(原名綠野新村,更是以“經營川揚幫菜肴”,后來成為歷史名店,并養出一位川菜大師:“林萬云,1922,綠楊村,特級川幫烹調師。”(《上海飲食服務業志》第一篇《飲食業》第七章《名店名師》,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版)
如果我們聯系到川菜館早期川閩并舉、中期師粵制粵,如今又“揚點川菜”的種種“創新”之舉,則可窺知其如何入鄉隨俗,兼收并蓄,坐穩做大之路徑,也可想象其后來走出國外,何以能“炮制”出“左宗棠雞”以適生存并求發展了。而滬上川菜館這種創新,還曾“倒灌”故鄉呢!比如重慶竟然也出現了一間與海上著名川菜館同名的“蜀腴”,并在上海的報章打廣告稱“特聘滬漢名廚,烹調新型川菜”。(《新聞集錦·渝蜀腴川菜館……》,《大公報》上海版1946年7月23日,第7版)
更能彰顯川菜的鼎盛及成功的,還不是川揚兼營,而是別人兼營或改營川菜,特別是向為上海灘龍頭老大的粵菜館,像著名的東亞又一樓,都改營川菜,可視為標志性事件:“東亞又一樓酒家,前為擴充內部暫停營業,現業已改造就緒,并加裝修工竣,于前日起復業。該樓改營正宗川菜及著名粵點,內部煥然一新當為滬上第一流酒菜館云。”(《東亞又一樓改營正宗川菜》,《中華時報》1947年9月8日第4版)在香港,這種情形更突出,此處不贅,可參見拙文《民國川菜出川記》(2018年7月14日《上海書評》)以至于有人說:“粵菜在上海已漸見沒落,A CLASS的酒菜館,如今大多賣川菜和湖南菜。”(易秋《川菜和湖南菜》,《小日報》1947年12月2日第4版)也有人說:
全中國人之言享受,上海人可謂得天獨厚,山珍海饈,佳肴名果,胥盡滬人大快朵頤以后,始及于內地。當寇氛江南之時,海上人仕,群喜粵菜,華字頭酒家,鱗次櫛比,即此故也。勝利以后,重慶人的大批復員,“要得”既尊為國語,川湘菜肴,乃奪粵菜之寵。是故向日顧客,如山陰道上之廣州酒菜館,今多門可羅雀,反之川湘菜館,戶限為穿。六十年風水輪流轉,開菜館亦須當令也。(聞天《川湘粵菜鏖戰紀》,《力報》1948年1月9日第2版)
這種種說法,雖不失夸張,尚不屬悠謬;回望歷史,還是應祝賀川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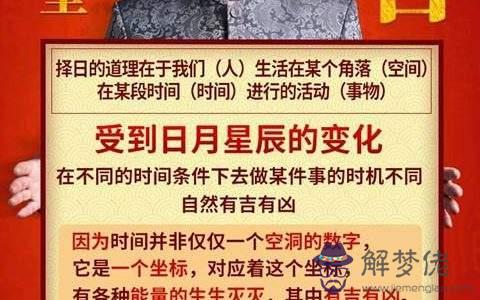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丁曉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44409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