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鄭子寧
摘編 | 徐悅東

《中國話》,鄭子寧著,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1月版
一種常見的說法是,全世界的語言中“媽媽”都是mama,因為這是人類嬰兒最初能發出的聲音。當一個牙牙學語的嬰兒發出ma的時候,他最親近的人,喜出望外的母親激動地把這個聲音當作嬰兒呼喚自己,久而久之,代代相傳,全世界的人類語言就把ma當成“媽媽”的稱呼了。這個說法聽上去很有道理,普通話中的“媽媽”自不必多說,英語雖然書面上寫mother,但口語也是mum。
可惜的是,這個說法至少在中國并不靈驗。
凡是看過清宮劇的人都會對皇子稱呼皇帝的叫法印象深刻——“皇阿瑪”,這是一個經典的編劇背離現實的案例。在清朝的滿文書面記載中,對父皇一律稱Han Ama,也就是“汗阿瑪”,如果寫漢文的話則是“皇父”或者“皇考”。“皇阿瑪”不說絕對沒有,至少也是難得一見的。Ama在這里指的是父親,顯然ma就不可能指媽了。在滿文中,媽有eniye、eme、aja三個說法,第一個最常見,也就是清宮戲中常見的“額娘”。今天在東北一些早就不說滿語的滿族家庭里,還把爸爸和媽媽稱作“瑪”和“訥”——和傳說中全世界都把媽叫ma可不一樣。
人從出生到死亡,互動最多的就是親人。因此,親屬稱呼往往是一種語言最穩定的詞匯,甚至在常用語言發生轉換后,家庭內部也經常使用原來的親屬詞匯,就像部分東北滿族家庭那樣。但與此同時,親屬稱呼又會因為各種原因被替換,如在不少地方,傳統上稱呼父親的“爹”就因為當代聽起來比較土,被“爸”迅速替換。
如果時光倒回1000多年前,情況或許正好相反,比較土氣的“爸”會逐漸被流行的“爹”所替換。
自遠古傳來的“爸媽”
自古以來,父親在漢語書面語中一直寫作“父”。今天在普通話乃至多數漢語方言中,“父”讀fu,不過在上古時期,“父”的讀音卻更近今天的“爸”。這是一個從原始漢藏語時代傳承下來的詞,藏文中“父親”稱ཨ་ཕ(apha),緬文是အဖ(apha)。雖然漢語歷史上語音發生了非常大的改變,原本的“父”(音近ba)已經讀成了fu,但是由于“父”使用頻率非常高,在口語中保留了歷史上的發音,因此才用另外一個漢字“爸”來表示這個古老的發音。與之相類似的則是“母”在口語中說“媽”。
這是個異常古老的稱呼,甚至在漢藏語中的用場也絕不僅僅限于指父母。藏文很多名詞帶有原來表示父母的后綴,如“太陽”叫ཉི་མ(nyi ma),“月亮”叫ཟླ་བ(zla ba),效果近似漢語“太陽婆婆”“月亮公公”。在麗江的納西語里,太陽則也是“女性的”/ȵi33 me33/。本就有自然性別的動物更是要帶詞綴,公豬要帶表示“男性的詞綴”稱為/ bu21 phv̩33/,麗江南邊不遠處的劍川的白族人則把公豬叫/te̱21 po55/。在詞語后綴中,劍川白語仍然保留了古老的“父”,盡管現今的劍川白語中稱呼父親已是/ɑ31 ti33/(阿爹)。
漢語中其實也有些類似的例子。普通話里有尾巴、啞巴、鄉巴佬、結巴,而在山東、東北等地的方言里,還有呆巴、瘸巴、瞎巴、癱巴、力巴(外行)、齁巴、摳巴、腳丫巴之類的詞。不過這些詞長久以來都是口語的說法,難登大雅之堂,在書面上出現得也晚,然而有理由相信,這樣的詞綴在口語里已有很長的歷史。
如果穿越回宋代的中國,當時的語言情況會和現代大不一樣。今天中國西南地區的漢語普遍比較好懂,但是宋朝的蜀地情況則大不相同。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當時的蜀語和蜀道相比也不遑多讓,素有極難解的聲名,與中原的開封、洛陽一帶的語音大不一樣,蜀人甚至把中原一帶的語音稱作“虜語”。
遺憾的是,這種蜀語已經隨著元朝四川人口的劇烈變動灰飛煙滅,今天的四川方言和宋朝的蜀語傳承關系很弱,而主要是明朝進入四川的漢語的后裔。
今天我們對宋朝蜀語的了解主要來自同時期的人。根據南宋蘇州人范成大的記錄,他當時路過了嘉州(今四川樂山)的一個渡口,渡口叫作“王波渡”。
范成大一定對“王波”是什麼意思困惑不解,他趕緊詢問了本地蜀人,當地人給他解釋后,他才恍然大悟,為此他特意詳細地寫下了“王波”的來歷:“蜀中稱尊老者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稱。”在當時的蜀語中,加“波”是常見現象,一如今天的納西語、白語、藏語。然而,從上古傳承到現在的“父”,也并非從來都是一帆風順。

范成大
“爺”是祖父還是父親?
《木蘭詩》在中國家喻戶曉,“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愿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被一代代中國人傳頌。毫無疑問,花木蘭稱呼自己的父親是“阿爺”。
今天在中國,除了“父”“爸”之外,用來表示父親的主要有“爺”和“爹”。然而這兩個稱呼到底指的是父親還是祖父,在各地差異很大。今天的普通話里“爺”表示祖父,“爹”表示父親,這在北方地區比較常見。而在南方很多地方,情況則各不相同,如合肥把祖父叫“爹爹”,父親叫“爺”;蘇州、常州把爺爺叫“阿爹”,父親叫“爹爹”。不過在宋朝以前,“爺”和“爹”只會指父親。這兩個字在中國古代的韻母并不是普通話的ie,而是ia,同一韻母的“斜”在“遠上青山石徑斜,白云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一詩中和“家”“花”押韻。今天不少方言,如閩南話、客家話甚至在陜西的許多縣里,“爹”“爺”的韻母仍然是ia。
《木蘭詩》本是一首北朝民歌,它差不多是最早使用“爺”的文學作品。“爺”幾乎是在魏晉南北朝時突然出現的,一開始甚至都無字可寫,借用了“耶”,后來才加上了偏旁變成“爺”。東晉時代的書圣王羲之在給女兒的書信“二十七日告姜,汝母子佳不?力不一一。耶告”中曾經署名“耶告”,即“父告”的意思。幾乎同一時代,“爹”“娘”也都同時出現。仿佛在幾十年間,華夏先民突然覺得用了幾千年的“父”“母”已經不敷使用,需要用別的詞來稱呼父母了。
王羲之是西晉北方高門瑯琊(今山東臨沂)王氏的一員,出生在北方,幼年時就隨家庭南遷會稽(今浙江紹興)。王家南遷并非是一般的遷徙,而是躲避戰亂,和他們一起南逃的北方人數不勝數,王羲之書信中的“耶”字可能來自這些迫使他們家族南遷的北方草原民族。

王羲之有“耶告”二字的書法
自東漢以來,朝廷不斷將北方草原民族內遷安置。進入三國時期后,曹魏繼續內遷北族。到了西晉時,關中、并州(山西)都已經有大量的北族定居。此時東亞氣候進入相對寒冷的時期,旱災等災害頻繁發生。內遷已久的北族和從草原新南下的北族紛紛起事,最終洛陽被攻破,晉懷帝被俘,西晉滅亡,史稱“永嘉之禍”。
此時來自中亞的粟特商人早已在中國經商多時。1907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玉門關外的一座瞭望塔遺址中發現了幾封粟特書信。其中一封是由當時居住在中國的粟特商人頭領娜娜槃陀發給在康國(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的老板的信息通報。
縱使娜娜槃陀是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大商人,他寫信時的極度恐懼在1000多年后仍然可以透過信札散發出來。
信的開頭是一番恭維對方的套話。隨后娜娜槃陀就以驚恐的語氣匯報了他聽到的信息:“……已經有三年沒有一個粟特人從中國出來了……最后一個皇帝因為饑荒從洛陽跑了,他的宮殿和城市被放了火,宮殿燒了,城市毀了。洛陽沒了,鄴城沒了。更糟的是……匈奴人控制了長安……他們昨天還是皇帝的臣民!剩下的中國人不知能不能把他們從長安、從中國趕走,或者他們會繼續打下整個國家……我們老了,快死了,如果不是這樣,我不會寫信告訴你我們怎麼樣。閣下,如果我告訴你所有關于中國現在怎樣的事——太慘了——你不會從那兒獲得任何利潤。還有,閣下,八年前我派了兩個人‘入關’,距我最后一次聽到他們的消息已經過去三年。他們之前還好,現在,自從厄運發生,我沒有從那兒收到任何關于他們現在的消息。更壞的是,四年前我派了另外一個人……當他們抵達洛陽時,那里的印度人和粟特人都餓死了。我還派了一個人去敦煌……他在未經我許可的情況下跑了,他遭到了報應,被殺死了……”
這封信并沒有抵達撒馬爾罕,從發現地點來看,應該是被玉門關外的軍士沒收了。我們不知道娜娜槃陀后來究竟是設法擺脫了厄運,還是和當時的許多人一樣死于戰亂。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年代,幾十年間,中國北方和巴蜀出現了十余個不同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權,進入了五胡十六國時代。
一般的說法是,五胡包括匈奴、鮮卑、羯、氐、羌。娜娜槃陀的信件中提到的洛陽的淪陷應該指的是后趙石勒、石虎攻陷洛陽的事,石勒家族屬于羯人。五胡都有著自己的語言,但是幾乎都沒有留下文字記錄。現今我們對這些語言的了解幾乎都只能通過漢文典籍中的只言片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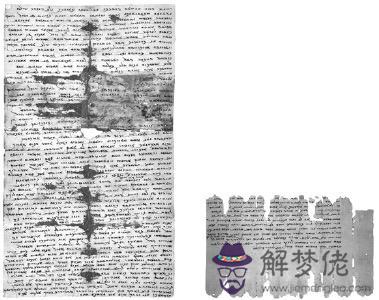
粟特文2號、3號古信札
以五胡在歷史上的影響力,今天留下的資料可以說令人驚異地少。五胡中氐人建立了仇池、成漢、前秦、后涼,羌人建立了后秦、宕昌、鄧至。氐、羌的族源和語言都相對明確,屬于漢藏語系,而匈奴、鮮卑、羯的語言就比較撲朔迷離。其中匈奴和羯的語言資料奇缺,雖然歷史上有用鮮卑語翻譯漢語典籍的記錄,但是后來全部散佚,至今也沒有出現過任何一本鮮卑語文書。
鮮卑語是南北朝到初唐時中國北方影響最大的北族語言。伴隨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統一北方,鮮卑語在北方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在軍旅之中。不但鮮卑人自己說鮮卑語,北方許多行伍出身的漢人也學會了鮮卑語。如北齊奠基者高歡就是鮮卑化的漢人,小字“賀六渾”,明顯是鮮卑語。因此在這些北族語言中,鮮卑語最有可能是“耶”的來源。
今天能確定意思的最大的一批鮮卑語詞匯來自《南齊書》中的《魏虜傳》,主要是一些北魏的官職名稱。《南齊書》的作者是梁朝人蕭子顯,出身齊梁兩代的皇族蘭陵蕭氏,是齊朝開國皇帝蕭道成的孫子。蕭子顯從小在江南長大,平常不使用鮮卑語,因此他所記錄的鮮卑語主要集中在敵國北魏的一些稱呼方面:“國中呼內左右為‘直真’,外左右為‘烏矮真’,曹局文書吏為‘比德真’,檐衣人為‘樸大真’,帶仗人為‘胡洛真’,通事人為‘乞萬真’,守門人為‘可薄真’,偽臺乘驛賤人為‘拂竹真’,諸州乘驛人為‘咸真’,殺人者為‘契害真’……”
稍整理一下蕭子顯所知的鮮卑語,就可以發現鮮卑語明顯把做某事的人稱呼為“某真”,“真”前則是所擔任的職務。這也為后人試圖揭秘鮮卑語提供了最初的線索。
我們先來看看守門人“可薄真”——不過在破解5世紀的鮮卑人的語言前,我們可以先穿越到1000年后的奧斯曼帝國宮廷去看看。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是奧斯曼帝國曾經的首都。幾乎每個去土耳其的游客都會慕名前去游覽奧斯曼的王宮托普卡帕宮。在奧斯曼帝國時期,蘇丹的女人們就居住在托普卡帕宮中,夢想著能在激烈的宮廷斗爭中翻身上位,斗爭的激烈程度不輸中國古代的宮禁。在土耳其語中,托普卡帕宮是Topkapı Sarayı。Saray就是宮,Topkapı則由top(炮)和kapı(門)組成。在托普卡帕宮外院和內廷的分隔處也有一道門,外院是蘇丹和朝臣議事的地方,而內廷除了太監之外只有蘇丹一個男人可以進入。這道門的控制權由一個特定的高級太監掌握,在土耳其語中稱作Kapı ağası,即“掌門太監”的意思。在今天的土耳其語里,看門人是kapıcı,其中-cı就是“做某事的人”的意思。
奧斯曼人的祖先是來自北方和中亞的草原游牧民族,他們在唐以后逐漸西遷,一路征服當地人,最終于1453年攻破東羅馬首都君士坦丁堡,kapı正是他們一路從草原西遷帶去的詞匯。
在《大唐西域記》中,玄奘和尚描述了他所經過的一處叫“鐵門關”的地方。他說:“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峻峭,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固,多有鐵鈴,懸諸戶扇,因其險固,遂以為名。”鐵門關位于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是古代烏茲別克斯坦進入阿富汗的交通要道。這道關口曾是兵家必爭之地,我們也因此能夠在蒙古草原上的毗伽可汗碑文中發現鐵門關的蹤影。毗伽可汗碑中提到突厥汗國拓境,東到卡德爾汗森林,西到鐵門關。在碑文中,鐵門關寫作Temir qapïγ,后者即“門”。Qapïγ差不多是“可薄”最可能、合理的來源。

玄奘
然而另一些證據則說明,鮮卑語不大可能是一種突厥語。漢語的“真”以-n結尾,但是突厥語“做某某事的人”的后綴通通沒有-n。譬如“老師”,在維吾爾語中是oqutquchi,在哈薩克語中則是oqïtwshï。要找到-n的線索,得在突厥語外尋找。
青海湖東岸的海東市民和縣是中國土族最主要的聚居地之一,土族居住的地區歷史上是吐谷渾活動的地方,吐谷渾為鮮卑慕容部的一支。
今天的民和土族說的語言非常有特色。一方面在基本的詞匯上較為接近蒙古語,而在語音上則和青海當地的漢語方言趨同,幾乎已可以用漢語拼音拼寫,同時又吸收了不少藏語的成分。在民和土族語中,表示“做某事的人”正是qin,譬如“要”是kerli,“乞丐”就是kerliqin。土族語的-n在諸種蒙古語系的語言中并非孤例,蒙古語系一貫有一些詞有時隱時現的-n,如在蒙古文里“舌頭/語言”拼寫為kele,但是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市南邊錫尼河的布里亞特蒙古族說的蒙古語中,這個詞發音為/xələ̆ŋ/。這也很可能是鮮卑語中表示“通事”(即“翻譯”)的“乞萬真”的詞源—蒙古文中,“通事”的拼寫為kelemürči,而在突厥語中,“乞萬真”則完全解釋不通。
另一批證據則由鮮卑人自己提供。
北魏孝文帝時,鮮卑人自上而下進行了漢化改革,孝文帝改革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拋棄鮮卑姓,改用漢姓,并且以身作則把皇族的姓氏“拓跋”改為“元”。
改姓浪潮中不少鮮卑姓是直接采取音譯方式選擇了讀音相近的漢姓,譬如“步六孤”改“陸”,“賀樓”改“樓”,“丘穆棱”改“穆”,但是很多鮮卑姓并無讀音相近的漢姓,更改也不遵循這個邏輯,如“宥連”改成了“云”,“叱奴”改成了“狼”,“若干”改成了“茍”。
“云”“狼”“茍”算不上當時漢族高門常用的姓氏,不存在為了融入漢族高門攀附大姓的問題,語音又和鮮卑老姓并不相近,那麼最可能的情況是,這幾家鮮卑人選用了和自己的鮮卑姓意思相近的漢姓。而這幾個姓都能在蒙古語里找到解釋,蒙古文“云”為egülen,“狼”為činu-a,“狗”為noqai,這三個詞都是他們的語言中非常基本的詞匯。而在突厥語系的語言中,這幾個詞則根本對不上,如維吾爾語中“云”為bulut,“狼”為böre,“狗”為it,同鮮卑語毫無關系。
不過,鮮卑人比蒙古人登上歷史舞臺要早千年,從時間先后順序上來說,鮮卑語顯然不可能是從蒙古語演變而來。而從鮮卑語留下的詞語來看,雖然和蒙古語有關,但是其語音甚至已經比元朝的蒙古文更加簡化,顯然也不具備演變成后來的蒙古語的可能性。只能說鮮卑語同蒙古語在更早的時候有同源關系。當鮮卑人南下中原時,蒙古人的祖先留在了草原,此后的千年時間,他們一直很不起眼,草原上突厥、回鶻、黠戛斯、奚、契丹、女真輪番登場,又逐個曲終人散,蒙古人的祖先一直在草原東部默默發展,直到成吉思汗時代統一蒙古諸部,成為新的草原和世界霸主。
成吉思汗
以鮮卑人在南北朝到初唐的巨大影響,如果中原漢人要從某種外語中引入親屬稱呼,鮮卑語自然是最可能的首選。鮮卑人不但深度參與中原王朝的政治生活,而且由于定居中原的鮮卑人大規模漢化,隋唐時代的不少貴族家庭都有鮮卑血統,這也使得鮮卑語的親屬稱呼可以通過這些家族的鮮卑親眷流入漢語,并因為是貴族家庭的用語而向全社會擴散。然而我們關于鮮卑到底如何稱呼自己親人的知識非常少,目前所知的關于鮮卑語的親屬稱呼包括鮮卑語把兄稱作“阿干”,母稱為“阿摩敦”,父稱為“莫賀”,除“阿干”可能和“哥”有關以外,其他和隋唐中原流行的稱呼并不一致。
事實上,就“爺”而論,鮮卑入主中原是4世紀末的事,可是4世紀初南遷的王羲之已經在使用“耶”了,因此要確定“耶”的來源還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爹”這個稱呼到底從何方來?
“爹”一詞最早出現于三國時期魏人編纂的《廣雅》。宋朝《廣韻》中,“爹”字收了兩個不同的讀音,一個解釋為“羌人呼父”,一個解釋為“北方人呼父”。中國古代的“羌”涵蓋了西部的眾多漢藏語民族。今天在四川涼山的彝語中,當面喊父親的一般稱呼是/a34 ta33/,而在提到父親時的尊稱則是/a21 bo33/,和漢語“阿爹”“父”的分野幾乎一樣。
而在北方,“爹”的來源可能確實和草原民族有關。
唐德宗年間,回鶻汗國出現內亂。此時率兵戰吐蕃不利的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引兵回國。新可汗在郊外邊哭泣邊拜大相說:“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于阿多,國政不敢豫也。” 頡干迦斯覺得可汗這麼卑微地哀求自己,非常難過,也抓著可汗一起哭。根據《資治通鑒》的說法,“阿多”是回鶻語父親的意思。可汗自稱自己是兒子,認頡干迦斯為父,可見他不管是發自內心尊崇,還是迫于形勢所逼,都完全不敢得罪這位大相。在維吾爾語里,父親是ata,就是所謂的“阿多”。這個詞在突厥碑文中的記載最早出現在8世紀早期的翁金碑上。當時并不是所有的突厥人都使用ata,在闕特勤碑中,父親就寫為qang。
相比父親在不同地方有“爸”“爹”“爺”等不同說法,漢語在叫“哥”的時候卻非常統一。例外情況大多和福建有關,閩南地區把哥哥稱作a-hian,這是“阿兄”在閩南地區的發音。
隨便翻開任何一本南北朝以前成書的古籍,你所能看到的“哥”都是“歌”的意思。從上古到中古早期,漢語中哥哥都說“兄”,幾無例外。然而今天在全國各地,除了福建和從閩南遷出的潮州、海南方言,幾乎沒有什麼地方會在口語中把哥哥叫成“兄”。似乎除了文化人在通信時互稱“兄”表示尊敬以外,口語中的“兄”基本只出現在“弟兄”“兄弟”兩個詞中。
“哥”取代“兄”的端倪出現在唐朝,一開始出現在皇室的語言里。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名曾經對讓他拜見尚宮的建議不屑一顧,直接說了句“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為?”,而當時“哥”除了表示“兄”,也可以表示“父”,唐太宗給兒子李治的信件落款就是“哥哥敕”。
“父”“兄”不分的亂輩分之舉并不符合漢語傳統的親屬稱謂系統。但是如果考慮唐朝皇室在南北朝時曾與鮮卑貴族大量通婚,這樣的叫法可能就并不意外了。
稱呼親戚背后的邏輯是什麼?
漢語的親屬詞匯分類相當細致,一個親屬該怎麼叫要根據這個親屬和自己的輩分關系,是父系還是母系,乃至這位親屬自己或者某位其他親屬的年齡關系。即便如此,漢語親屬關系中仍然存在明顯的不對稱現象,父系男性要比母系或者女性親屬分得細一些。譬如父親的兄弟要根據比父親大還是小分別稱作“叔”“伯”,但是如果是父親的姐妹則統一稱“姑”,而母親的兄弟則統一稱“舅”。而且輩分上,“姑”和“舅”也可以跨輩。
唐朝王建的《新嫁娘詞》中間一首是:“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這里的“姑”是丈夫的母親,“小姑”是丈夫的姐妹。孔子過泰山,碰上婦人哭訴“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這里的一家祖孫三代都死于老虎,“舅”在這里指的是丈夫的父親。
然而在不同的語言中,由于社會結構的不同,什麼親戚屬于一類,什麼親戚需要分開是很不一樣的。在泰國,對年紀比自己稍長的人均稱พี่(phi),這個詞在泰語中就是“兄”或“姊”的意思,這兩個在漢語中嚴格區分的親戚在泰語中用一個詞表示。相應的,“弟”和“妹”在泰語中均為น้อง(nong)。這在從中國南方延伸到泰國的壯侗語系語言中是個普遍現象,在云南西雙版納的傣語中,“兄”和“姊”為/pi33/,“弟”和“妹”為 /nɔŋ11/。
壯侗語在對“母姊”“母妹”“父姊”“父妹”四個親戚的區分上也和漢語邏輯截然不同。在漢語中,這四個親戚是按照父系、母系兩分,父系叫“姑”,母系叫“姨”。但是在德宏傣語中,“母姊”和“父姊”都稱/pa42/,“母妹”是/la54/,“父妹”則是/ʔa33/。漢語中優先區分這四位親戚屬于父系還是母系,但是在德宏傣語中,則要先分這四位親戚比自己父母年長還是年幼,年長的歸一類,年幼的再根據屬父系還是母系確定稱呼。在四川涼山的彝語中,一個人對兄弟姐妹的稱呼則和自己的性別有關。一個男性要區別稱呼自己的兄/vɿ55 vu33/、弟/i34 ʑi33/,姐妹則統稱/n̥i21 mo21/;女性則要區別稱呼自己的姐/vɿ55 mo21/、妹/ȵi33 ma55/,兄弟則統稱/m̥a21 ʦɿ55/。
中國古代的草原民族匈奴和鮮卑的親屬稱呼,除了零星見于漢語典籍的幾個外都已經無法還原。幸虧古代突厥人有在墳墓勒石以記錄墓主功績的習慣,我們今天才得以對古代突厥人的親屬稱呼有比較系統的了解。在古突厥語中,一個重要的特征是輩分的概念和漢語很不一樣。在古突厥語中“叔”和“兄”用一個稱呼eči,已經出現了把比自己年齡大的父系男性親屬統用一個稱呼的現象,這和“父”“兄”同稱僅有一步之遙。

鮮卑人
事實上,在新疆東部的綠洲里,我們已經可以找到“父”“兄”轉化的實例。今天的維吾爾語里aka是哥哥的意思,然而在吐魯番南部的魯克沁附近,aka指父親。一個更具有普遍性的例子出現在哈薩克語之中,哈薩克語里父親是äke,祖父是ata。和近親語言如新疆西部的柯爾克孜族的語言相比,哈薩克語的父親比較接近柯爾克孜語的哥哥(agha),祖父比較接近柯爾克孜語的父親(ata)。
這可能和游牧民族的“還子習俗”有關,即長子會把自己的第一個小孩交給自己的父母(小孩的爺爺奶奶)撫養。自此這個小孩會把爺爺奶奶稱作“父母”,而把親生父親稱作“哥哥”。如果其他孫輩跟從這個年齡最大的孫輩的叫法,久而久之,本來用來叫哥哥的詞就會轉而指“父親”,而本來指父親的詞就會改指“爺爺”。這樣的傳統可能在北方民族中由來已久。
北齊皇室受鮮卑影響很嚴重,根據《北齊書》記載:“(高)緯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南北朝后期,原籍山東瑯琊的南渡家族后裔顏之推被西魏俘虜,遷回北方。當踏足家族兩百余年前逃離的北方時,他發現北方人“……至有結父為兄,托子為弟者”,并對北方人輩分倫理的輕忽頗為吃驚。
作為南渡高門家族成員,早已南遷江南的顏氏家族和身邊的士族交際圈顯然都沒有這種輩分錯亂的跡象。當他們在4世紀從北方離開時,這種現象在北方并不普遍。在200多年間,中原地區受到了北族風俗的嚴重影響,以至于讓回到北方故土的顏之推大吃一驚。亂輩的風氣一直到唐朝都很盛行,唐朝皇室甚至身先士卒,不光“哥哥”兼表“父兄”,還多次出現收養孫子當作兒子的事。
“女郎”為娘
在“哥”“爺”“爹”紛紛登場的同時,母親的稱呼也發生了改變,一個新的詞“娘”開始用來指代母親,這個稱呼在初唐開始流行。
在繁體字里,“娘”有兩個對應字,一個是“娘”,一個是“孃”。嚴格來說,在唐朝時,前者一般指的是年輕女子,后者才指母親。
“娘”的出現要早一些,隋之前的碑刻中已經出現了“某某娘”的人名。此后“娘子”是對女性的稱呼。
莫高窟第98窟是五代時期敦煌的統治者曹氏家族修建的。洞窟墻壁上繪制了大量的壁畫,主要是一些佛經場景的再現。在墻壁比較貼近地面的部分則是洞窟出資人——曹氏家族成員的畫像,其中就有“故新婦娘子翟氏供養”、“故女第十四小娘子一心供養出適翟氏”和“新婦小娘子索氏供養”等數幅壁畫。年紀較小的女性稱為“小娘子”,年長的則叫“娘子”。
這種用法并不僅僅限于北方,唐朝樂府詩中有一類詩叫作《子夜歌》,據說是晉朝一位名叫“子夜”的吳地女子所作。傳說未必靠譜,但是《子夜歌》所用的語言有大量的吳地特征,就算那位名叫“子夜”的女子子虛烏有,《子夜歌》也可算是吳地女子創作的產物。如“芳是香所為,冶容不敢堂。天不奪人愿,故使儂見郎。”,作者自稱為“儂”,以“儂”為“我”至今仍然可以在浙江很多吳語中找到痕跡,甚至一直延伸到兩廣一帶,像廣西貴港的粵語仍稱“我”為“儂”。在另一首詩“見娘喜容媚,愿得結金蘭。空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中則出現了“娘”,在今天江浙地區的許多吳語方言里,年輕的少女仍然稱作“小娘”或“細娘”。
我們甚至可以在更南的地方找到“娘”的蹤跡。
位于中緬邊境的云南瑞麗是以前勐卯古國的都城。瑞麗的傣族女性一般稱“朗某某”,這個“朗”并不是姓氏,而是加在女性名字前,表示對女性的尊稱。“朗”實際上是德宏傣語(la: ŋ45)的音譯。這個稱呼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相當久遠的古代。傳說中勐卯國歷史上曾經有位繼承王位的公主“朗玉罕良”,她當時的都城位于“允朗玉”,即“二公主城”的意思。
和西南地區很多漢語類似,德宏傣語n/l不分,在德宏傣語的近親緬甸撣邦的撣語中,這個詞就是 (náang)。這是云南傣族、緬甸撣族、老撾老族和泰國泰族女性都非常常用的尊稱,大約相當于漢語“女士”。而貴族女性的稱號則往往還要在nang前后加一些其他成分,譬如緬甸第一位總統的夫人——木邦土司的女兒就叫“召婻哏罕”,“召婻”即“公主”的意思。
泰國王后的稱號中,冠于名字前面的部分為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นางเจ้า(Somdet Phra Nang Chao),其中也含有nang。泰國的泰族大約在晚唐到五代時從廣西、云南南部南下至中南半島。至遲這個時候,“娘”就已經進入了他們的語言中,因此在唐朝時,“娘”這個稱呼已經擴散得非常廣泛,從西北的敦煌到南方的廣西、云南皆有使用。“孃”則是個早就出現的字,然而漢魏時期,這個字的意思是“煩擾”,是“攘”的一種寫法。入唐以后用“孃”表示母親的規模漸漸擴大,晚唐開始,“孃”“娘”漸漸有混用情況出現。
然而關于“娘”“孃”是如何突然出現的有好幾種說法,一說“孃”來源于突厥語“你母親”。在突厥語系的語言中,表示“你的”時在詞語后面加上-ng,如維吾爾語母親是ana,你母親是anang。“娘”則是“女郎”或是“女兒”的合音。可是“孃”借自突厥語的說法卻存在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突厥汗國在6世紀中期脫離柔然汗國自立,在攻滅柔然汗國后成為新的草原霸主。中原王朝始通突厥是在西魏大統十一年(545年),突厥在不久之后就成為中原王朝北面的心腹大患。然而整個突厥汗國和后繼的東突厥、西突厥乃至后突厥都始終沒有能夠像鮮卑人那樣入主中原,雖然不少突厥家族后來先后內遷在唐朝為官,但是比起鮮卑在中原的影響仍然微不足道。而且突厥汗國碑刻中母親是ög,ana要到后來的回鶻時代才出現在文書里。
總而言之,中國人在從三國到唐朝的幾百年間完成了一次親屬稱呼的重新組合,舊的稱謂消失或者暫時隱匿了,新的稱謂出現。這次親屬稱謂的變動一直影響到今天中國人如何稱呼親戚。然而,除了“哥”較為明確是鮮卑或者其他北族的稱呼外,“爺”“爹”“娘”是如何在短時間內突然取代漢語固有的稱呼仍然存在諸多疑團。
原作者 | 鄭子寧
編輯 | 徐悅東
導語校對 | 王心
來源:新京報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44398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