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來源: 極晝工作室
在這個團隊里,最年輕的成員只有18歲,年長的也只有22歲,死亡這種終極問題對他們來說太過抽象。一名大一的隊員原先只在文學作品中接觸到自殺,詩人海子的死甚至帶給她浪漫主義的感受。
但接觸這些案例后,現實不再具有這種美感。
文 | 程靜之
編輯 | 王珊
一個身體開始墜落。
他穿著黑色的T恤衫,淺白色的牛仔褲包裹著單薄的雙腿,在空中轉了一個圈,然后重重砸在紅色救生氣墊的邊緣,一只鞋被甩出很遠。
人群里響起一片尖叫。在南昌“夢時代”廣場這個繁華的商貿圈,一個17歲少年的生命畫上句點。
天快黑了,又下了點小雨,廣場的霓虹燈亮了起來。一個多小時后,江西師范大學新聞系大二的學生鄭丹到了現場,清掃車正在工作,地上已經沒什麼血跡。她沿著少年王家新的足跡,一層一層往上爬,手心冒汗。
她覺得一個人的生命似乎太輕了。
2018年5月,21歲的鄭丹以校園記者的身份接觸這起少年自殺事件。她打聽到逝者王家新的住址,那是一棟灰色水泥外墻的老樓,大空調的箱子“呼呼”地吹著氣,樓道狹窄陰森,門縫里滲出一線燈光。是什麼導致王家新走上死亡之路?鄭丹渴望知道真相,猶豫了幾分鐘,她敲響了王家那道綠色的鐵門。
據《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過去16年的統計數據,自殺已成為中國青少年繼交通事故、溺水和白血病之外的第四大致死因素。
擺在鄭丹面前的是一些宏觀的數字,她想探究背后的密碼。在導師指導下,她和5名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學生,一年內走訪北京、河北、江西、江蘇等地,深度訪問7個家庭,大多是2018年被輿論關注的青少年自殺事件,試圖還原他們在選擇自殺前所經歷的不同階段,最終整理成論文《失控的想象——社交媒體時代青少年自殺現象研究》,包含親友采訪、專家錄音和采訪日記,達幾十萬字。
這六名學生和研究對象年齡相仿,有人也曾閃現過自殺的念頭。當他們觸碰這些逝去的年輕人,開始對生命有了一個模糊的新概念,也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了自己的生活。
另一扇門向他們打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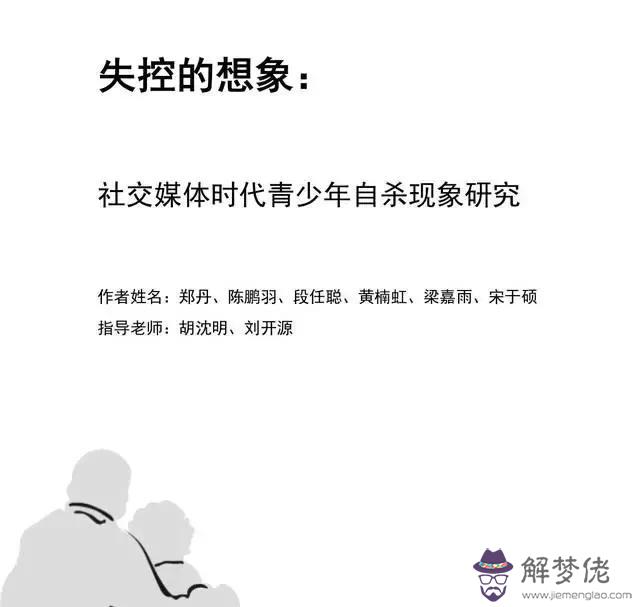
被戳破的想象
坐在河北固安縣的肯德基窗邊,胡軍建裹著黑色羽絨服,眼皮耷拉,他在這里接受過很多媒體的采訪,后來把所有記者的微信都刪了。“每次采訪完,我都發誓是最后一次,但是看你們來了,又不忍心了。”他看著三名與兒子年齡相仿的大學生,紅著眼眶,就要哭出來。
這些學生告訴他,正在做一個關于“青少年自殺”的社會調研,希望尋找問題和規律,聯合實際找專家提出可行的規避方案。
7個多月前,兒子胡政在自殺群里約了兩個年輕人,在一個出租屋里燒炭自殺,死后12天才被鄰居發現。警方到達現場后,發現門縫、窗戶縫,甚至窗簾都被膠帶貼了起來,屋內留有三盆未燃盡的木炭,還有一封兩行字的遺書:“我們是自愿的,與任何人無關。”
父親胡軍建記得,胡政離開家那天,沒有吃晚飯,洗了個澡,出門還噴了香水。“我問他搞這麼香干嘛,他一笑,很靦腆的孩子,說跟人家約好了。”胡軍建對鄭丹他們說,只看到兒子模糊的背影,背著一個時尚的小布包。
采訪胡軍建之前,大三的隊員段任聰認為他文化水平不高,可能是一名粗暴的父親,但面前的胡軍建時而哽咽,話語充滿溫度。
段任聰是個情感細膩的男生。來之前,他就在報道中捕捉到兩個細節:胡政曾有一段減肥的經歷,連續四個月去健身房,減了40多斤,又在淘寶上買了許多關于成功學的書籍。“我能看到他自律、想要成功、愛干凈的模樣,卻看不到死亡的氣息。”段任聰說。此前,他認為自殺者就是懦弱的和沖動的,無力面對生活現實,而胡政的性格和行為存在巨大的反差,“他究竟有多決絕,將自己生存的希望完全封閉?”
失去兒子后,胡軍建潛入自殺群,也曾試圖尋找兒子自殺的原因。在他的敘述中,段任聰逐漸拼湊起胡政短暫的生命軌跡:從小搬過兩次家,初中輟學,淘寶創業失敗,潛伏自殺群兩年,網戀女友提出分手。
“他肯定很孤獨。”胡軍建后來意識到,搬家切斷了兒子的朋友圈;兒子淘寶創業期間,一個人在外租小單間,每天耷耷地坐在床上,對著電腦,旁邊是一堆外賣盒子,“傻傻的,問了半天一句話沒回”;自殺群里,每天接觸的又是“找人一起去燒炭”“一起去華山蕩秋千(跳崖)”這類信息。
鄭丹和段任聰他們后來總結,胡政的自殺經歷了疏遠親人和尋伴的過程,多重創傷事件疊加,讓他早已形成固有觀念,“在他進入自殺群約死之前,甚至在結束那一段愛情之前,他就已經開始自殺了”。
這是團隊接觸的第三起自殺案例。他們將研究范圍限定于10-25歲的青少年,選取了在校學生、創業者、失業者、自謀職業者等不同的樣本類型。
“夢時代”廣場跳樓少年王家新是典型的自謀職業者。登陸他的QQ賬號,鄭丹發現他在網上認了很多妹妹,將兩個班群設置為“免打擾”,卻加入了各種踢球群、閑聊群、簽到群、互贊群。在僅自己可見的QQ空間里,寫著 “我很孤獨,有誰能陪我”。
鄭丹加了王家新同學的QQ,在同學的評價中,王家新學習成績不好,邋遢,喜歡吹噓玩游戲的水平。他試圖用笨拙的方式討別人喜歡,卻時常受人欺凌。母親回憶,兒時幫他洗澡,身上總是青一塊紫一塊。他中考都沒參加,就在修車廠和家附近的酒店打工。
自殺一個月前,王家新在網上交了一個女友,女孩提出分手后,他告訴一個“妹妹”:“我打算離開了。”“妹妹”沒太在意,猜想只是玩笑。

2018年母親節前一天,17歲少年王家新的生命在“夢時代”廣場畫上句點。受訪者供圖
隨著采訪的深入,鄭丹發現,有些事情越發與她設想的不一樣。原先,她認為社交媒體造成了胡政和王家新的死亡,但后來發現,他們在生活中找不到存在感,因此都在自殺前通過社交媒體自救。
“青少年自殺多源自社會承認的消失。他們曾經都試圖拓展新的支點,并且通過戀愛初步實現了他們的想象,一旦戀情受到破壞,生命最后的寄托點也就會坍塌。”論文最后這樣寫道。
在這個團隊里,最年輕的成員只有18歲,年長的也只有22歲,死亡這種終極問題對他們來說太過抽象。一名大一的隊員原先只在文學作品中接觸到自殺,詩人海子的死甚至帶給她浪漫主義的感受。
但接觸這些案例后,現實不再具有這種美感。
宋于碩是個喜歡弗洛伊德的理工男,大二時轉到新聞學院。在他看來,“自殺,這個詞匯和我之間的距離處于一種很奇怪的狀態。”他用一個物理實驗做類比:在一個盒子里,有一只貓和少量放射性物質,這些物質有可能衰變殺死貓,也有可能讓它活下來,盒子打開前,一切都是未知。“就像薛定諤的貓一樣,‘自殺’只要不出現在我的生活中,它的存在取決于我的認知。”
現在,盒子被打翻了,他隱隱體悟到自殺者無力反抗背后的無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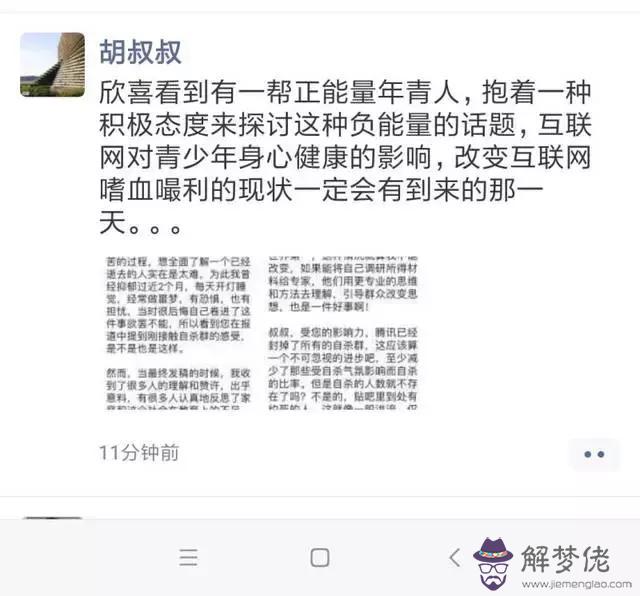
采訪結束后,胡建軍發了一條感謝朋友圈。受訪者供圖
影子
鄭丹接觸的第一個案例就是王家新,那段時間,王家新總是出現在她的夢里。她經常在半夜驚醒,脖子被汗水浸濕,有時感覺王家新就在身邊。她像被關進了一個小黑屋,不想和別人說話。
之前在媒體實習時,這個敏感的女孩就目睹過年輕生命的逝去,“就像大批的老鼠涌向海里”。她在南昌進賢看到死于煤氣中毒的五個女孩,躺在殯儀館的玻璃柜里,面色發黑,身體腫脹。一個母親靠在床頭,目光呆滯,被人從地上拉起又趴下。這一幕帶給她的沖擊太強烈了。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她去找學校的心理老師幫忙分析王家新。等她說完,老師并沒有給出更多的解釋,“相比王家新,我更想知道你的心理還好嗎?”兩人都沉默了,鄭丹的眼淚掉了下來。
調研的最初階段,導師胡沈明發現,鄭丹過于沉浸在案例里。“她對自殺理解的理論深度仍然不夠,交流時候情緒低落,更多希望她能從理論上超脫出來。”他希望研究能抵達更遠的地方,揭開青少年自殺的規律,“尋找生命的真諦”。
聽到這個形而上的概念,鄭丹懵了,“不知道從哪里下手。”她找到學院另外5名學生,展開深度調研,并以此作為挑戰杯全國大學生系列科技學術競賽的參賽課題。
學術界對自殺問題的討論從未停歇。《自殺論》作者迪爾凱姆從社會學角度,論述個人自殺與社會的關系。北大哲學系教授吳飛把自殺視為一種文化現象,試圖尋找中國式的理論解釋模式;致力于生命危機干預工作的謝麗華主要研究農村婦女自殺。而這些,對于青少年可借鑒的并不多。
查閱完論文,團隊把 “殺魚弟”作為下一個研究案例。
2018年7月31日,在與家人激烈爭執后,17歲的“殺魚弟”孟凡森搭配著水和冰紅茶,喝了30-40ml的百草枯原液,肺和腎都被灼傷,經治療后脫離生命危險。10歲時,他因在父母的魚攤上幫忙殺魚而走紅,伴隨著“輟學”、“家暴”等質疑。
鄭丹去蘇州尋找“殺魚弟”的第一天,下著小雨,郊區鬧市的盡頭,掛著“山東蘭陵大發水產”的招牌,疾馳而過的車輛濺起一溜泥水。她在店門口看見“殺魚弟”一只腳踏進魚池,赤手抓起一只魚扔在外面,稱一下再扔到案板上。收攤之后,家里六個孩子擠在客廳里看動畫片,房間里的被子雜亂地堆著。
“我當時的想法是什麼?就是死了就沒有那麼煩惱,腦子轉不過來,一直在一個死角上。”孟凡森對鄭丹說,他住院第二天就想通了,現在最煩惱的,是很多字不認識。
鄭丹想以教單反攝影為由,約孟凡森單獨談,父親卻始終不同意。
“我我憑什麼讓你帶走我兒子?”父親咆哮著。
“你總不可能叫他殺一輩子魚。”鄭丹說。
“就殺魚,殺一輩子魚!”他將池子里的水潑在外面,幾乎濺到鄭丹的衣服上。
孟凡森勸鄭丹趕緊離開。“說不通的,我們親戚帶我出去玩一天,根本不可能的,他這個人很難說話。”
“結構猶如一張大網,讓生于其中的人無處逃脫。”她在論文中總結,“青少年往往處在家庭和學校織就的封閉社會結構之中,一旦無法準確把握和理解結構的力量,悲劇便有可能發生。”
鄭丹也曾急于掙脫家庭結構的壓迫。上高中時,她和弟弟在縣城租房,每天買兩塊錢的面,向鄰居借火生爐子,煮好了姐弟倆一起吃。每次考差了,媽媽怪她不努力,她一個人躲著哭鼻子。奶奶又經常打電話抱怨,父母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打架。這一切都壓在她身上,讓她難以呼吸。
她甚至在“殺魚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深灰色的農藥片被含在嘴里,邊緣開始慢慢消解,一股刺激、帶點苦澀的味道竄進鼻腔。幾年過去,這種味道依然殘留在鄭丹的記憶中,爸爸拿了一個大馬勺,舀了一瓢水,讓她喝了吐,喝了吐,味道才被慢慢沖淡。
那是鄭丹距離死亡最近的一次。父母在地里干完農活回來,又打起來了,媽媽捏著拳頭捶打爸爸的臉,鄭丹過去阻攔,被扇了一個巴掌,“你不要管”,媽媽對她說,“今天不是我死,就是你爸死。”
“那就一起死啊。”鄭丹在幾個窯洞里挨個找農藥,取出一片含在嘴里。爸爸追過來,猛地敲打她的背,藥片還沒來得及吞下去,就被拍了出來。
“有時候覺得自己很倒霉,生在這樣一個家庭。”在她的成長中,爸爸媽媽一直打架,開始她會在旁邊大聲哭,后來習慣了,干脆走遠散散心,或者去另一個窯洞看書。
團隊里另一些成員也有過類似的記憶,一名男生至今無法原諒父親,小時候因一個誤會而責打他,高中篡改文理科志愿,帶給他的傷害是無法磨滅的。
這些經歷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殺魚弟”:從小在農村長大,看到就是方圓十里,陷入另一個世界后,就看不到更多之外的東西。“在這一過程中,他的思維由多元逐步發展到一元,甚至極端化,從而喪失理性,逐步失控,最終形成自殺意念。”

“殺魚弟”孟凡森脫離生命危險后,回到店鋪里繼續殺魚。 受訪者供圖
失控
鄭丹很少對朋友提起正在做的選題,一起調研的同學都覺得這個事情,太難,太難了,不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家人也不理解,“你怎麼去挖死人的事情,會把人逼瘋的。”姐姐在電話里訓斥,“你是一個無良記者,把這些東西曝出來,就是提供了一個(自殺)模版。”
一次放假回家,父親趴在床頭抽煙,“丹啊,你學這個專業我們都很后悔。”母親在一旁附和。
她對研究沒有把握,感覺像拿一個小錘頭在鑿洞,每走一步都是探險。
下一站目的地是濮陽,6天前,一個高三男生突然跳樓了。
這不是一場策劃已久的自殺。2018年,袁治垚和班主任約定,考進全校前30名就可以換宿舍,達到要求后卻仍被拒絕。課堂上,他在黑板上留下四句打油詩,“并非無寢室,僅為少拿錢,侵害我身體,與你何加焉?”之后在墻邊上搬了凳子,跑出教室,一躍而下。
在這之前,一切看起來都很尋常。翻看手機和日記本,大致是與學習相關的內容。剛過的18歲成人禮儀式上,爸爸抱著他在氣球上寫了自己的夢想——杭州師范大學。最后一天的監控顯示,他上午還在換著不同的資料書寫作業。
這起“非典型自殺”事件像一個特例闖進來,打破了這群年輕人所有的預設。沒有家庭不和、沒有遭遇過什麼打擊,“不存在一個謎,層層揭開,自殺現象的背后是單薄的,就想出個氣,就自殺了。”
大三的黃楠紅也無法理解這起自殺事件。在她看來,自殺是比較私密的行為,袁治垚不是選擇在房間,而是上課的時候,在萬眾矚目下,像是英勇就義,背后的邏輯關系是什麼?
他們聯想起兩個多月前,湖南衡陽成章實驗中學三名女生服藥自殺事件。唐予心因成績退步,被母親要求寫檢討書。當晚,她在班群里表達自殺的想法,之后與兩名同學一同服用了秋水仙堿片的處方藥,想嚇唬一下老師。她錯估了藥物的致死量,留給父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有信心,我一定會活過來。”
六個隊員開小組會議時,段任聰認為唐予心的行為是一種表演,不屬于“自殺”。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點。他們將調研的7起案例按社會、自身、隨機三個因素畫成思維樹狀圖,卻無法捕捉到其中的規律。“不知道自己在搞什麼。”一次,鄭丹改論文的時候突然崩潰。
鄭丹在調研中接觸過一個抑郁癥患者,給她發來自殘的照片,胳膊上布滿一道道刀痕。鄭丹不知道怎麼辦,只能讓她趕緊去包扎。
“我挺心疼她的,但我明確知道自己幫不了什麼,因為我還沒有完全理解她的世界。”鄭丹只能給她的朋友圈點贊,害怕某一天女孩就不再回信息了。那是一種強烈的無力感,“我很難幫到他們什麼”。
遠在馬來西亞的導師胡沈明在電話里提醒他們,“如果把人生當做走路,自殺者就是把路走成一條的人”,把青少年的認識和思維看作“想象”,一旦變得非理性,就容易失控。胡沈明幫他們總結出“渴望認同、積極爭取、遭遇排斥、拓展失敗、認知窄化、消極抵抗、偶爾頂撞、直接對抗、以命抗爭”幾個階段,認為大部分自殺者都會經歷其中的一個或幾個。
他們又找到“希望24小時”自殺熱線。這條中國最大的自殺干預危機熱線2012年成立于上海,江西中心的接線室隱匿在南昌市一棟普通的居民樓內,幾乎不被附近的人所知。
他們在那兒了解到更多超乎想象的案例。一個男孩自殺的念頭起源于童年和父親的一次爭吵,他最心愛的小提琴被砸壞了;一名北大女孩畢業后,搞砸了團隊項目,造成巨大損失,坐在賓館的窗臺邊打電話,“我不想活了”;一名男生不小心碰到了女同學的胳膊,被要求對她負責,什麼活都讓他干,他覺得只有死才能解決問題;一個初三學生,升學考試時,被監考老師沒收手機后,直接從五樓考場跳了下去。
“人在遭遇創傷事件后會產生創傷心理,做出偏差行為。”志愿者吳樹家解釋說,對于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來說,創傷事件不論大小,可能成人眼中的一件小事,就能把他們壓垮,“除了父母、老師,他們沒有更多的求助管道,拉力也少,很多東西壓在身上,就以為是天大的事情,內心容易崩潰。”
梁嘉雨在醫院調研時遇到一位阿姨,主動陪女兒的同學看心理醫生,她認為不能因為孩子不夠優秀,就放棄他們,“如果父母都不理解,孩子會覺得更痛苦”,她覺得父母都能像這位阿姨一樣,很多悲劇或許能避免。在門外等待醫生時,梁嘉雨無意中聽見咨詢室里傳出打給熱線的電話錄音。“有自殺傾向的人很大程度上不愿意、不放心與外界交流”,她認為如果隱私做得不好,有人會更加抵觸心理治療。

團隊成員在討論論文細節。受訪者供圖
脫節的一代
失去兒子的一年里,王家新母親的嗓音變得沙啞,胳膊軟塌塌的沒力氣,有時在路上看到與兒子身形類似的男孩,就忍不住落淚。父親總是發低燒,每天早晚喝中藥。
他對自殺的新聞變得敏感,去年年末,同濟大學一名研究生從醫學院輔樓五樓跳下,今年,上海盧浦大橋上,一個男孩從車里沖出來,從橋上一躍而下。
“家庭教育好的也跳,不好的也跳,你怎麼講得清?”他依然無法理解孩子的死亡。
夫妻倆試圖向神佛尋找答案。他們找到一個神婆算八字,又為大兒子請了一道平安符。他們在一些小事上變得敏感,不讓大兒子拉電閘,每天給他發微信,深夜守著他回家,甚至等到凌晨。他們期盼著大兒子能早點結婚,為家里再添一個人口。
采訪結束后,鄭丹和他們時有聯系,陪他們過了一次端午節。
她害怕弟弟成為下一個王家新,頻繁給他打電話,聽他說煩心事。她還記得小學時,一次弟弟回家晚了,在家門口被媽媽拿著電線抽。他哭紅了鼻子,在外面站了很久。長大后,弟弟不愛講衛生,也沒什麼朋友。
“我感覺你和王家新有點像。”鄭丹說。
“我不會像他那樣去跳樓。”弟弟在電話那頭笑了。
鄭丹一直覺得姐弟倆沒有感受過父母的關愛,但她也知道,母親每次打完孩子,都會讓另一個去看看怎麼樣了。第一次從家人那里感受到愛,是在大一患上肺結核的時候。父親把家里的羊都賣了,把一沓又一沓錢交給醫生。早晨醒來,母親把粥和小籠包買好了,放在炕頭。麥子成熟的時候,母親堅決不讓她下地,盡管家里人手不夠。
她突然意識到,之前調研時,更多是帶著對家庭教育的批判,但采訪胡爸爸的時候,她明顯感覺到了胡爸爸很無奈,覺得其實做父母也不容易,對于家長的角色,有了更深一點模糊認識。“他們也在慢慢學習怎麼做父母”。
現在,她對媽媽更加寬容了。因為沒有及時打電話回去,媽媽總是生氣,把她微信拉黑了好幾次,都要慢慢哄。她想起一次,媽媽和爸爸打完架,一個人在窯洞里喝醉了酒,鼻子紅彤彤的,躺在炕上哭,“你不知道姥姥把我打成什麼樣。”后來,小姨告訴她,媽媽小時候拉一頭驢到溝里去打水,回來路上灑了一桶,從早上被打到晚上。但這是媽媽心里的紅線,從來不允許鄭丹提。
隊員梁嘉雨也想起來,上初中的時候,好幾次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大哭,做警察的父親站在洗衣房的窗前,注視著窗臺的方向,以防她做傻事。
調研結束后,他們對父母的評價普遍提高了兩三分。“以前總覺得爸爸是需要改變的,現在明白他的性格是他的生活環境造成的,我會去接受他。”段任聰說,他們決定拍制一個視頻,把一些家庭和學校教育的問題反應出來。寫劇本的時候,段任聰還是無法站在父母和老師的角度看問題,不知道他們在不同的情景下會作出什麼反應,他意識到“我們這一代人不愿意和父母交流”,造成雙方不理解。
5月26日下午,論文答辯的日子到了,隊員穿著白色襯衫,黑色西褲,打了領結,走上講臺。
“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也很有創新性。”一名評委老師說。另一名老師則認為材料比較薄弱,數據分析不夠。他們最終獲得省二等獎。
鄭丹也意識到,已有的例子可以套在總結出的公式里,但范圍之內,可能也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在這些案例中,她看到了青少年自殺的各種因素,也感受到了自己這個年齡階段普遍的迷茫、孤獨和無助,生命的脆弱和復雜。“所以自殺之謎是什麼,我也說不清楚,糅雜起來好像又精簡,研究最終只能定在大部分青少年的心路歷程。”如果有機會,她想幫助更多家庭降低與孩子之間的壁壘。
她至今記得,坐在離開固安的長途車上,看到胡政爸爸胡軍建發的朋友圈和一條短信,“很高興看到你們這樣的年輕人也在關注‘死亡’的話題,讓我看到了跟我孩子同齡人心靈的純凈,從陰霾中尋找到了陽光。”
論文結果出來第二天晚上,鄭丹趕上最后一班地鐵,去了“夢時代”廣場。晚上九點多,賣小吃的店面依然亮著閃爍的霓虹燈,一些青年在廣場入口處彈著吉他,夾雜著小攤販喇叭的叫賣聲。那些來這兒尋找快樂的人,很少知道一年前,一個少年的生命在這兒終結。
站在地鐵口,鄭丹望向五層“空中花園”王家新跳下來的位置,那里已經被徹底封起來了,透明的玻璃圍欄又加高了一層。
那里是“夢”結束的地方,也是開始的地方。
搜狐極晝工作室出品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作者簡介

程靜之

一頂鴨舌帽,一雙采訪鞋。
作品包括《等待章瑩穎》
《木里的風,帶走了涼山消防四中隊三班》

為嚴肅閱讀提供選項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44382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