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胡簫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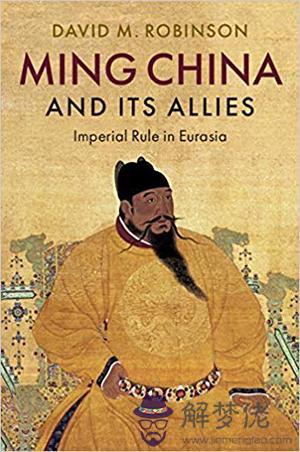
David M. Robinson, Ming China and its Allies: Imperial Rule in Eur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公元1367年秋,朱元璋在平滅張士誠、納降方國珍以后,逐步將經略重心北移,意圖恢復中原,并在大軍開拔之際發布了張夷夏大防的《奉天北伐討元檄文》。在申明自己天命所歸的同時,朱元璋提出了著名的八字口號,即“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后世史家常以此為立論基礎,將元明鼎革判為民族革命。及至清末民初,此一口號及其象征意涵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如孫中山便將其化為同盟會的政治綱領,宣揚排滿復漢,甚至在清帝退位伊始拜謁明孝陵時興奮地感嘆道:“嗚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靈,何以及此?”(《謁明太祖陵文》)
問題是,明朝在恢復中華的同時,真的驅逐胡虜了嗎?錢穆早就觀察到討元檄文內在邏輯間的張力,并點出其文字口吻“氣和辭婉,從來檄文,殆少其例”(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六冊,第99-100頁)。當代史家奇文瑛的研究也指出,明初因為現實需要,朝廷其實在用各種方式淡化與故元移民的對立,與之前諸朝相比,明朝漢人與北方民族“雜居狀況只有加深而沒有削弱”。(奇文瑛:《明代衛所歸附人研究——以遼東和京畿地區衛所達官為中心》,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頁)也就是說,政治口號并不能完全反映歷史現實,明朝中土與塞外之間也并不總是非此即彼的一刀兩斷,雙方具體的互動過程,當放置在動態的歷史語境中仔細檢審與考察。
魯大維(David Robinson)的新作(Ming China and its Allies: Imperial Rule in Eurasia,暫定中譯名《明代中國及其盟友:歐亞大陸的王權統治》,下文簡稱《盟友》)便是討論明朝與北方民族動態互動的全新力作。作為美國明史學界近年來產量頗豐的青壯年史家,魯大維循著“大元帝國的遺產如何影響明朝政權架構”的思路,已經完成了一系列的作品。其2013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檢審明代“尚武”活動的著作《神武軍容耀天威》已經譯介進入國內市場,并由陜西師范大學馮立君教授作了精彩述評。而在此書以后,魯大維于2019年末、2020年初在劍橋大學出版社連續出版兩部新作,可以視為作者對“尚武、外向、多變的另一種大明”(馮立君語)的最新思考。本文主要評介《盟友》,至于另一本新作In the Shadow of the Mongol Empire: Ming China and Eurasia(暫定中譯名《蒙古帝國的陰影:明代中國與歐亞大陸》),筆者當另文討論。
蒙古人與明代王權
在一種常見的歷史敘述當中,明朝與蒙古草原諸政權通常被描繪成對手,雙方互不相讓,多有沖突。有明一代,明朝皇帝始終將蒙古視作心腹大患,或以力、或以利,或以攻、或以守,雜合多種手段試圖穩定帝國的北部邊疆。即便是承平時代的朝貢互動,在草原領袖如俺答汗眼中,亦不過是漢地俯首稱臣、接受蒙古上國地位的象征,所謂“年年月月不斷供我所需,令人滿意稱心如意”(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頁)。在這樣的表述脈絡下,很少有人去探討蒙古政權對于明代王權的鞏固究竟有何積極意義。
魯大維新著便從這個維度展開論述。《盟友》聚焦太祖以后的數位帝王,他們在十五世紀前中期統治著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最多的商業中心、最龐大的常備軍和最磅礴的經濟體(第4頁)。而他們統治的權威與合法性,在魯大維看來,則與其時歐亞大陸最為耀眼的貴族集團——成吉思汗后裔及支持者——息息相關。《盟友》分析了十五世紀前六十年間明朝王權統治的構建及實踐,尤其關注那些“來朝遠人”(men from afar)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作者認為,與蒙古貴族的互動是明代皇帝形塑身份認同、確立統治風格、獲取支持并在東部歐亞大陸組織地緣政治聯盟的重要舉措。既往研究多從軍事、貿易、外交或文化互動角度探討明蒙關系,而本書則另辟蹊徑,圍繞著“王權”這一概念檢審明代帝王與君權的特質究竟如何呈現在與草原領袖互動的過程之間。以此,作者希冀糾正流布于既往研究中的三類失焦表述,即:(一)明代中國總體而言呈現一種內向生長的態勢,與外向發展的西方世界形成鮮明對比;(二)即便是有限的對外交往,學者亦多將目光集中于經濟、文化、技術交流與人口往來,而帝王與王權本身在這樣的敘述中不見蹤影;(三)與外向、多元、擴展式的清朝王權特質相比,明朝皇帝的統御之術顯得狹隘且僵硬(第5-6頁)。通過關注十五世紀前中期明廷與內亞地區之間的戰爭與和平、聯盟與背叛,又或是推心置腹與勾心斗角,魯大維對明代帝王為何、以及如何與廣闊的歐亞世界保持聯系發問,從而激發學者對明代王權更為細膩的體認。
不一樣的皇帝
與其父相比,明成祖朱棣在史學界受到的關注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說他是明代帝王中被研究得最為透徹的一位亦不為過。《盟友》能否讓讀者對朱棣產生不一樣的認知?如果說王鴻泰的研究展現了朱棣以儒學支撐政權正統性,并為自己塑造文治“圣王”形象的努力的話(王鴻泰:《圣王之道:明文皇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臺大歷史學報》第57期(2016年),第117-181頁),那麼魯大維筆下的朱棣,便是一個與蒙古下屬佐肉酣飲、跨馬馳騁、彎弓圍獵、并肩作戰的草原霸主。本書的第一、二章對大量詔書、外交文書及詩歌進行文本分析,考察朱棣如何建構并強調自身對蒙元政治遺產的承續,以合法化明朝對北方大地的權威、統御與征伐。作者認為朱棣在洪武時期便對包括地理、人事、習俗以及生活方式的蒙古事務頗為熟悉,這影響了他日后皇權統治的諸多面向。朱棣充滿“內亞因子”的統治特質亦為蒙古人所肯定,以至于燕王的稱呼長久存在于蒙古人的歷史記憶當中,蒙古史籍《黃金史綱》甚至將朱棣直接判為元順帝遺腹子。分析朱棣與北元大汗鬼力赤、本雅失里的通信,魯大維認為朱棣充分掌握了北元動蕩政局的相關訊息,在草原實權派激烈爭奪汗位的當口不斷介入紛爭,以便將自身塑造成更具合法性的北地領主。而在詔書中不斷重復諸如大元德運已失、大明代之而起的對正統性的強調,則充分體現出皇帝面對東部歐亞世界并未將順帝北歸視作蒙元政權合法性之斷裂的焦慮。換言之,朱棣在與北方世界互動的過程中,存在著持續不斷地向部屬及外鄰展演權威的迫切需求。在這個意義上,五次北征便成為了皇帝宣示正統性的最佳展示。在十數年的連續北征過程中,朱棣不僅運籌帷幄、親臨戰陣,更需要在軍事行動處于被動之時不斷籠絡朝鮮國君、女真豪酋、瓦剌首領甚至中亞汗王,強調戰爭的合法性及皇帝的必勝決心,以避免政治軍事聯盟關系的破裂。而在取得軍事勝利之時,朱棣則積極地將自己的帝王印記鐫刻于大漠草原,通過修改地名、勒石封功,以及品評甚至摧毀前元遺跡,嘗試將自身的武功植入北地的歷史記憶里。
在北征過程中,朱棣頻繁地與草原領袖宴飲、圍獵、閱兵甚或出生入死,表現出十足的尚武氣勢。面對此般情形,朝中的漢族文士作何反應?他們如何理解并敘述皇帝與他的“北虜”下屬們啖肉飲血展示勇武的場景?魯大維考察了諸如楊榮《次興和舊城宴別夷人》一類的詩歌,以示漢人士大夫如何以歌頌華夷一家的方式贊美皇帝的豐功偉績。與此同時,他也發現在盛譽皇帝武功之外,漢人士大夫亦通過其他方式表達出對皇帝與蒙古人過從甚密的不滿。如在分析胡廣詩歌時,作者便點出詩人在創作大量記功詩的同時,亦頗多借古諷今,一方面批評漢代冒進出擊匈奴的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則肯定韓安國勸誡漢武帝暫停戎事、與民休息的舉措。可以說,明初的文官群體為成祖親征大漠量身定做了一套論述以肯定其合法性,但也并不完全認同皇帝對蒙元遺產的接受和享受。如果說檀上寬在其《永樂帝——華夷秩序的完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31頁)中將永樂北征視作其“成為中華世界天子的近乎瘋狂的執念”還是傳統論述的延續的話,那麼魯大維則對永樂皇帝身上潛藏的“燕王習氣”做了別樣的展示。
不一樣的蒙古人
有關明代內遷中原的歸附蒙古人,中、日、英文學界在過去的數十年間產生了齊頭并進且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日本學者中,萩原淳平、河內良弘、川越泰博等老一代學人由宏觀到微觀、由《明實錄》到《武職選簿》,對明代歸附民族研究的推進做出不小貢獻。中國學界則在張鴻翔先生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所做的一系列工作的基礎上,于上世紀末涌現出諸如寶日吉根、王雄、邸富生等一系列學者的研究成果,并在彭勇、奇文瑛的相關研究中體現出由政治史向社會史的視角轉向。而英文學界則有柯律思(Henry Serruys)于二十世紀中期首先關注相關議題。近年來,魯大維先后發表文章,或從文化史角度探討明代歷史書寫對蒙古人的形象塑造,或從參與宮廷政變的蒙古人事跡切入,討論十五世紀中期的族群張力與政治文化(David M. Robinson, “Images of Subject Mongols under the Ming Dynasty,”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5, No. 1, (2004), pp. 59-123; “Politics, Force and Ethnicity in Ming China: Mongols and the Abortive Coup of 1461,”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9, No. 1 (1999), pp. 79-123.),這兩個面向皆在《盟友》中的相關章節有所呈現。
朱棣對草原的執著在漢族朝臣的筆下遭到淡化,蒙古人在明初朝廷中扮演的角色亦是如此。《盟友》第三章為一群歸附達官描繪群像,以刺激讀者重新感受明代前中期宮廷文化和王朝特性中的內亞感。在朱棣第四次北伐時,東蒙古領主也先土干投降明軍,獲賜名金忠,并封忠勇王。其在太宗、宣宗時代的北征中立下赫赫戰功,并被宣宗贊為左膀右臂,所謂“卿,朕金日磾也”。金忠外甥把臺一起歸降,得漢名蔣信,正統皇帝土木遭擄之時,把臺伴其左右,后從駕還。兩代歸附達官為明廷盡拳拳之心,恰與劉定之《否泰錄》中全然不提大量附明蒙古人戰死于土木的選擇性記敘形成鮮明對比。除卻效力于明廷的達官以外,蒙古女性亦是明代宮廷中不可忽略的一個群體。明初來歸的達官恭順伯吳允誠于涼州耕牧,其三女入宮為太宗皇帝妃、孫女入宮為宣宗皇帝妃。朱祁鎮外孫楊璽亦娶達官懷柔伯施聚之女為妻。可以說,歸附蒙古人不僅與明代皇帝并肩作戰、同甘共苦,還與皇室成員存在廣泛的聯姻關系。
為了體現對歸附達官的重視與信任,朱棣不僅指派高級朝臣楊榮、鎮邊大將陳懋等負責具體的接收及安置工作,更有對金忠于宮廷宴會上“御前珍饈悉輟以賜之”“上乘馬時,金忠一騎后隨”的特別照顧,并許以封號、官職、田宅地產等諸項禮遇。歷仁、宣直至景泰、天順朝,達官群體多持續保有特別的政治、經濟特權。傳統敘述多將此類非常待遇視作明廷對歸附蒙古人群體的獎賞,甚至說收買,魯大維則認為這其實構成了明代王權的關鍵一環,即皇帝通過與內亞非漢群體的互動來鞏固統治的合法性,借由達官的歸附與認可將自身確認為合格的統治者。作者引用楊榮為吳允誠所作的神道碑中“遐方絕域之士,能識天命”的表述(第95-96頁),力圖表明明代帝王不僅僅是漢地皇帝,更是東部歐亞大陸諸政權的共主。
在討論了達官群體地位陡升的過程及原因后,魯大維亦對服務于明廷的蒙古人在天順朝以后漸漸淡出史籍的現象做出解釋。作者認為,隨著歸附蒙古人數量的日益減少,尤其是早期歸附達官逐步將政治舞臺從邊疆騰挪到京城,他們作為“中間人”的價值亦隨之褪去。十五世紀中期,尤其是土木之變以后,文官群體崛起后逐步掌握了歷史書寫的權力,明初廣泛活躍在帝國軍政領域的蒙古人遂逐漸消失在歷史記憶中。及至明末,歸附蒙古人與明廷的互動,甚至如黃景昉在《國史唯疑》中“時以降虜王子為功,賞賚無算,要以明中國廣大氣氛而已”的敘述一般,遭到簡單化的處理。
不一樣的“土木之變”
作為明代歷史上具備轉折點意義的重要事件,“土木之變”的具體過程及歷史意義無需贅述,既往研究也已相當豐碩。但在《盟友》中,魯大維則提出新穎視角理解此一事件。本書第四、第五章聚焦“土木之變”,通過檢審1449年前后東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互動,考察明朝、瓦剌、韃靼/東蒙古、女真、朝鮮一干政體如何共享蒙古時代的政治遺產。作者認為,這些政權對政治合法性、外交禮儀、地緣聯盟等意識形態與現實政治的準則與實踐存在同源卻互有差別的認識和理解,這是十五世紀中期重要的歷史語境。
在將“土木之變”置放在一個跨地域地緣架構下進行檢審之前,魯大維先就事變中明軍傷亡人數展開討論。作者將一手文獻如《否泰錄》《國榷》《明實錄》與中、日、英文學界的二手研究并置,發現關乎明軍傷亡人數的諸種記載之間存在無法自洽的矛盾。在作者看來,這恰恰提醒我們要對文士與史官主筆的歷史書寫保持警覺,因為在當時混亂的政治局勢下,夸張的敘述和尋找替罪羊的操作是必不可少的。這里的討論讓筆者想到自己在北京智化寺的游覽經歷。智化寺于正統八年仿唐宋“伽藍七堂”規制而建,先為王振家廟,后得敕賜寺名為報恩智化寺。英宗北歸以后,在寺內為王振立精忠祠,并塑像祭祀。《英宗諭祭王振碑》至今仍存寺內,碑文感人肺腑,可見主仆情深。這似乎與傳統敘述中王振大奸大惡、為立邊功而挾英宗親征的記載背道而馳,顛覆今人歷史想象。以此,筆者贊同魯大維所倡,即關乎土木之變的很多敘述當審慎看待。
魯大維認為,“土木之變”發生的歷史語境其實是諸多東部歐亞大陸政權對后蒙古時代地緣政治威權的爭奪。在描繪瓦剌崛起的過程以后,魯大維尤其將注意力放在也先與脫脫不花如何籠絡包括哈密、女真諸部與朝鮮等諸多政權的努力上。這里值得稱道的是作者對史料的使用方式。一方面,《盟友》大量援引域外史料,尤其是朝鮮方面的《李朝實錄》來探討瓦剌方的外交策略。作者對《李朝實錄》中包含的大量細節,比如外交文書及外交使節的派遣方式等進行分析,大大彌補了明朝方面史料的浮泛與不足。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作者利用《李朝實錄》中對也先“天成”可汗的記載去討論明代史籍中“田盛”可汗的表述。另一方面,作者嘗試從漢文史籍中讀出非漢視角。除了剝離漢文史料可能帶有的意識形態偏見以外,更專注于細節,將明朝一方只言片語的記載與包括《李朝實錄》《拉失德史》的域外文獻比對,從而恢復事實原委。《盟友》第四章著力探討了也先如何組合聯姻、外交斡旋、軍事威嚇等一系列手段向歐亞大陸東、西方擴張,從而樹立自己后蒙古時代草原霸主的形象。
也先的崛起提醒了明廷維系歐亞共主地位所需要的持續不斷的地緣政治運作。《盟友》第五章將目光移到幾個小型政治體上——哈密、關西七衛、兀良哈三衛——并關注明朝與瓦剌在爭取跨地域支持時的努力與碰撞。雙方對政治聯盟的運作方式有頗多相似性,但最為重要的不同在于也先對政治聯姻的高度依賴。而不論是封號、宴請、禮物交換或貿易特權,其實都是后蒙古時代歐亞大陸普遍流行的政治智慧。由此,作者力圖展現明代王權統治的內亞維度。本章第二部分提出“通約性”(commensurability)的概念以提煉其時東部歐亞大陸共享的政治語匯與外交規范。作者認為,發源于共同歷史經驗的政治準則形塑了東到朝鮮、女真,西到哈密、察合臺汗國的王權形態,而十五世紀前半期由明朝和草原政治體主持的地緣政治競爭則進一步刺激并鞏固了這一政治文化的通約性。與之相伴者,則是人口、經貿、技術的跨地域交流與融合。縱然蒙古帝國于十四世紀中后期逐步崩解,但它留下的政治遺產則持續影響著東部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面貌與格局。
視角游移與范式轉換
針對《盟友》一書,中、英文學界皆尚未有書評問世,筆者不揣谫陋,對全書內容及價值做簡單評述,希望引起讀者關注。《盟友》一書是魯大維對“另一種大明”之形態與性質的最新思考。作者以鮮明的問題意識縱貫全書,即就“明初帝王與內亞領袖的互動體現出明代王權怎樣的特質”進行發問。在筆者看來,縱然書中對若干史料的文本解讀有過度詮釋之嫌,又就敘事戛然而止于天順朝、對十五世紀后半期依舊焦灼的明蒙爭鋒缺乏足夠解釋,《盟友》一書變換視角以挑戰傳統范式的價值仍值得肯定。作者近年來的一系列寫作嘗試展現明代中國較少為人關注的面向,甚或可以理解為美國明史學界對“新清史”作品中扁平化處理明朝方式的反撥。“新清史”作品多有將明朝視作單一族群、單一文化的政體的傾向,甚或拒絕以蘊含多元性的“帝國”(empire)一詞稱呼明代中國。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已經指出,中國歷史上的王朝都多多少少具備所謂的內亞性,明清之間不存在質的差別,不過是表現方式或程度不同。在《簡析明帝國的內亞性》一文中,鐘晗便提出,“新清史”學者筆下清帝國“內亞性”的三個特質。所謂“共主”的政治象征,多語種合璧文獻的出現,與靈活而富有彈性的宗教政策,其實在明代皆已具備。以明初漢藏交流為例,因為對藏傳佛教的諸般禮遇,明初帝王如太祖與成祖便分別在藏地的世界觀中被表述為文殊菩薩的轉世以及轉輪王。這符合所謂的“共主”特質,即在面對不同族群的治下百姓時,帝王展現不同性質的統治者形象。至于“合璧”,即漢文與非漢文多語種對照、體現所謂“共時性”(simultaneity)的文本特征,在永樂宮廷所制作的《大寶法王建普度大齋長卷》中便能體現。長卷以漢、藏、波斯、蒙古、回鶻五種文字并列描繪噶舉派大寶法王在中土展演的宗教奇觀,堪稱“合璧”文獻的典范。與此同時,明初帝王支持藏傳佛教僧眾的傳法活動、贊助他們的譯經、印經事業,賦權佛教大寺統轄邊區社會,奉行靈活的宗教政策。在這個層面上,明代帝王的統治模式與風格與“新清史”學者筆下清朝王權的“內亞性”并無二致。由此,筆者贊同魯大維所提倡者,即將明朝政治文化置放在更為廣大的歐亞政治文化語境中進行認知,而不僅將其理解為華夏文化傳統的延續。
責任編輯:于淑娟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41774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