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發、齊劉海,交談時常常發出爽朗的笑聲,澳大利亞華裔作家許瑩玲(Julie Koh)給人的印象很親切。這不是許瑩玲來中國,卻是她和中國文化如此接近。在,亞裔的身份常讓她無正融入白人的世界,而扎推在中國這些相似的面孔中,許瑩玲也依舊無法自在:她時不時地要回應“你英文很好呀!”這種讓人哭笑不得的贊美。
許瑩玲出版有兩本短篇集:《資本失格》(Capital Misfits)與《輕小奇妙事》(Portable Curiosities)。其中《輕小奇妙事》入圍多個獎項短名單,包括“新澳大利亞——閱讀獎”、“昆士蘭文學獎——斯蒂爾·拉德獎”、“新南威爾士文學獎的獎——科技大學格蘭達·亞當斯獎”,以及澳大利亞科幻基金會頒發的“諾瑪·K·恒明獎”。2022
年,許瑩玲入選《先驅晨報》澳大利亞優秀青年家,2022
年受邀擔任斯特拉獎評委。短篇作品在多個刊物發表,并在2022年至2022
年連續三年入選《最佳澳大利亞故事》合集。她的作品也在美國、愛爾蘭、日本、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等國出版。她同時也是新加坡獨立書店Books Actually年度文學選集《Books Actually的黃金標準》的編輯、諷刺歌劇《主廚爭奪戰》(Chop Chef)的編劇。
今年3月,第12屆“澳大利亞文學節”,作為嘉賓的許瑩玲被邀請至中國,一同而來的還有她的諷刺短篇集《輕小奇妙事》(Portable Curiosities)。
《輕小奇妙事》里的短篇故事極盡想象力,“肚里上長了第三只眼的女孩和一只蜥蜴在對話”, “戴著遠的從泡沫塑料杯里啜飲甘菊茶”,“野心勃勃的美食家制作出吃下就有一半幾率喪生的冰激凌”……她筆下一個個光怪陸離的故事,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洞察著和世界。而這不僅要歸功于許瑩玲個人的天賦,還有跨文化背景給予她的獨特視角。

許瑩玲, Hugh Stewart 攝
“我只是碰巧生在了這副軀體里”
許瑩玲出生于,父母是馬來西亞華裔。兒時,許瑩玲并不能接受自己的亞裔身份。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她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有著藍色眼睛的“白人小男孩”,因為她所沉浸的文化中——從媒體到書籍——幾乎所有的主角都是白人。她還拒絕上華文學校,總之,她花了很長時間來適應自己亞裔女性的身體。到了今天,在“澳大利亞文學界”的開幕上,或許是為了迎合觀眾對她身份的期待吧,許瑩玲用“你好”眾打招呼。
高中時,許瑩玲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導演,但父母希望她能選擇現實的、能賺錢的職業。許瑩玲覺得這可能是家庭父母的特點,期望子女有穩定的生活和地位。最后,許瑩玲還是聽取了父母的意見,成為了大學一名文學和雙專業的大學生,大一結束時,許瑩玲又從文學系轉至系。這件事,一度讓她頗感后悔,她笑著說,“如果當時我繼續學下去了,現在別人再問我
文學理論上的問題,我就可以回答了,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能說自己是隨性而為。”
轉系之后沒多久,一個年輕的導演
到她,說想要改編她在高中時創作的一個故事。這件事成為了許瑩玲人生的轉折點,時隔多年提起,許瑩玲依然難掩興奮。她說,“那時候我意識到,雖然我沒有學習制作,但我可以試著寫作,我很期待把文字放到一起后的化學反應”。很巧的是,這位導演也是一名亞裔。許瑩玲說,盡管在成長過程中,她與亞裔群體很疏離,感情也不深厚。但是進入以后,恰恰是亞裔群體給予她最多的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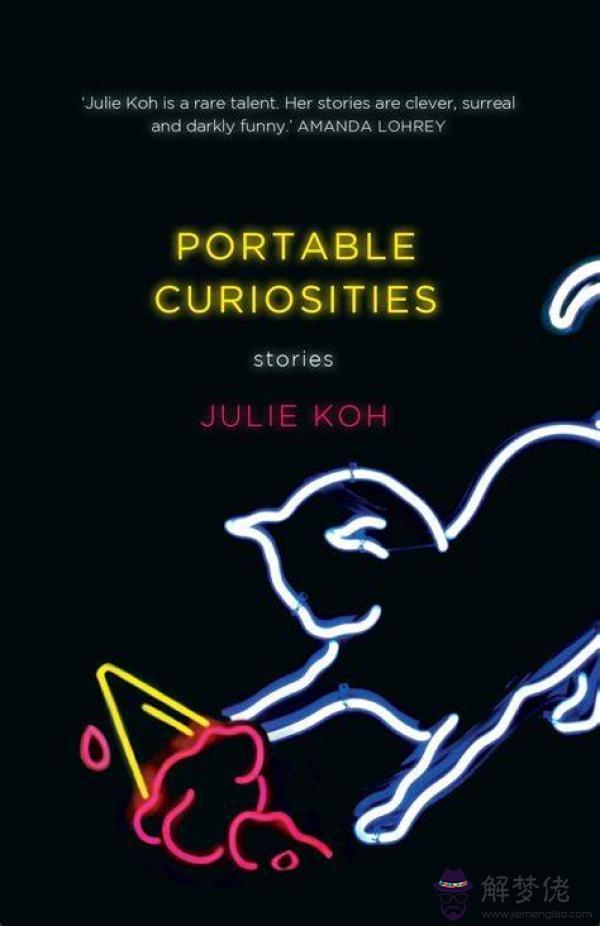
《輕小奇妙事》書影
畢業以后,許瑩玲進入一所律所工作。工作兩年半后,她選擇辭職并開始專職寫作。談到這個選擇,許瑩玲說:“我知道我可以成為一個好律師,但是很難成為那個最好的。我還是想要把各種想法和日常生活用充滿想象力的方式寫成故事”。不過這些經歷讓許瑩玲得到了一個“半途而廢者”(quitter)的稱號:她常常改變方向,從未堅定地選擇過某一行業。這和她的創作風格如出一轍,不拘泥于形式,隨性而為。她調侃自己的“壞”名聲,說自己還在繼續發掘更多的新領域,目前正在為歌劇院寫劇本。
一開始許瑩玲只是復制自己受到的文化熏陶,她坦言影響她較深的是白人男性作家,因此在早期創作的故事也總是以白人男性為主角,書寫他們人到中年,家庭不幸的故事。她在《衛報》的采訪中提到,她成長的城市并不是一個適合寫
的城市,“作為整個澳大利亞的中心,的城市風格即是逐利的。”這也影響了許瑩玲初期的創作風格,她稱其為“在廚房水槽發生的白人中產故事”。
“在,有錢人永遠是有優勢的”,隨著年齡增長,許瑩玲對問題的認知更成熟,曾經的成為了她如今寫作中所的。許瑩玲發現中很多人的成功并不建立在美德的基礎上,反而是家庭關系、地位起到了巨大作用。對現有經濟體系的反思讓許瑩玲感嘆,“我們把自由掛在嘴邊,但這卻不是一個自由的體系。我開始重新
作為一個亞裔,我的真實體驗,和中權力的運作規律。”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永遠不懂平等的意義”
許瑩玲坦陳,“雖然‘碰巧生在了這幅軀體’中,但并不代表我要按照對亞裔的刻板印象活著。”她通過自己的“亞裔軀體”所感知到的問題,是深刻和普世性的。
在許瑩玲創作的短篇中,種族是她長期
的議題。《三維的黃種人》(《The Three-Dimension Yellow Man》)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正在放映的《白忍者的回歸》里走出來一個黃種人——忍者“十三”,想著“或許三維的世界會好過些”。“十三”有自己的興趣愛好,走進現實世界后便開始研究費德里科·費里尼里的女性形象。他被邀請參加很多,可是人們和媒體只會問他“作為黃種人是一種什麼感受”。接著,一個亞裔女性也走出了熒屏,人們驚訝于她的皮膚竟然不像想象中亞洲女子那麼光滑,還有她沒有口音的英語。
不久后,更多的“黃種難民”從屏幕里走出來,終于形成了對于黃種人的恐慌。書中這麼描寫道,“我們正面臨著被‘’淹沒的危險。這些黃種人在一起,形成了貧民區。他們還偷走了我們的工作。所謂的正確正在毀滅我們的!”故事的最后,一個憤怒的金發男子將“十三”毆打,而富有同情心的路人著“十三”的慘死,卻無人伸出援手。
從這個故事中,無論是被調侃的“口音”還是“身材”,不難看出許瑩玲生活的影子。她一直很
澳大利亞主流媒體中有色人種的呈現方式,其中刻板印象的滲透幾乎無孔不入。比如電視節目里,存在于背景里的亞裔角色,不是員,就是在打太極。又比如“虎爸龍媽”,或者極度懦弱的女性和偏女性化的亞裔男性。這些讓許瑩玲感到不適號,都變成了她諷刺中的素材。不過涉及亞裔群體之外的因素鮮有涉及,許瑩玲表示,“少數族群的寫
應該明確到底誰可以寫別人的故事。我只是從我的經歷出發進行創作,這個特殊的身體是不同于別人的。有關其他和族群的創作空間應該留給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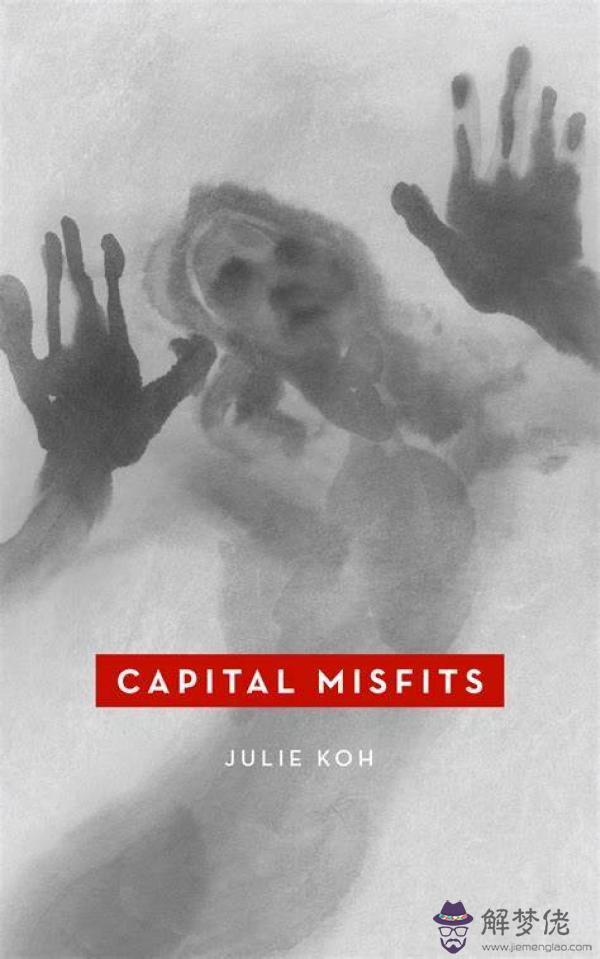
《資本失格》書影
通過使用女性、亞裔作為主角,在挑戰對這類角色的刻板印象的同時,許瑩玲想要改變人們閱讀的習慣。讀完她的故事以后,讀者或許會反思,面對一個,“亞裔”的特色不該是你腦海中出現的第一個印象。盡管許瑩玲書中呈現的都是嚴肅的話題,但她并不想讓讀者陷入悲傷的情緒。所以她將“憤怒”和“幽默”的元素結合到一起,讓讀者可以笑著思考嚴肅的問題,這是對她而言最舒服的創作方式。
當談到最近發生的新西蘭恐襲,許瑩玲表示,“我看到報道,很多少數族群都表示對這次恐襲不驚訝,因為媒體一直在鼓噪‘反對’的風氣。種族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概念,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永遠不懂平等的意義。”她覺得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于主流群體的態度,自發地意識到癥結所在。很多家利用人群的恐懼和憤怒為自己贏得選票,而不是把精力放到懲罰種族者身上。許瑩玲覺得,首先需要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在層面,人們在時,應該多支持那些追求平等的,而不是被弄權之人利用,給家帶來更多的權力。至于文學作品的意義,雖然不在于提供一個解決方案,卻可以將“暗潮涌動”給更多的人看。
“用我的故事改變人們的觀點?我并不樂觀”
性別問題近幾年在全球范圍得到
,作為的亞裔女性,“雙重壓力”的另一半——性別問題,也是許瑩玲創作中的主題。曾經在律師行業工作的許瑩玲表示,盡管有一些女性工
,部門仍是由男性主導,這種問題是全球性的。
在《美妙的》這個故事中,進行選美大賽,不僅可以自由行走,還極受追捧。物化女性的現象而《歷史上的胖女孩》疑問則反思了過度減肥的問題。
針對女性在文學作品中總被塑造成極度在意外貌的群體的形象問題,許瑩玲覺得,女性應該對自己身體的自,遵從自己的喜好打扮自己。過分在意外貌是一種壓力,費時且傷人。而導致女性物化的原因
兩方面,其一是消費橫行,人在媒體上的形象也變成一種商品,其二是“父權”的,讓女性成為某種“財產”。
盡管許瑩玲在創作中談論了許多女性面臨的困境,她表示,“對于用我的故事改變人們這件事,我并不樂觀。現在,我只想我的作品可以接近那些本來就和我看法一致的人。”在《美妙的》一文里,許瑩玲用詼諧的方式討論了家暴的問題,她把注意力放到施暴者的心理,以及日常細節如何構筑起“父權”對于女性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家為總是從非常小的,諸如“她最近胖了很多”的評價開始,逐漸發展成為精神情感上的。這樣的故事總是那麼相似:從開始,到建立關系,再到家為,最后以原諒結尾。
不過她還是很高興自己的作品可以被一些高中作為閱讀材料使用,因為有很多道理她是希望自己在進入前就已經了解到的。許瑩玲認為,女性群體內部依舊存在分歧,焦點就在于她們是否真正理解人的多元化和多樣性的意涵是什麼。盡管澳大利亞人在某些方面是進步性的,但當報紙上提到多樣性時,談論的依舊是讓更多女性進入職場的問題。許瑩玲覺得大多數人在“多樣性”的意義上依舊存在盲點。面對這種分歧,女性群體應該以合作的方式,而不是疲于內部分化。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41739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