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女性學者,你會想起誰?這份名單一定不長,這是因為——女性,從來不是學術界的主流。無論是高校教席,還是學術成果發表,越往象牙塔的頂端走,女性的數量就越少。
事實上,當一個女性決定從事學術事業,她所面臨的限制無處不在:
“女博士是第三種人類……”
“歷史證明學術界不是女性的地盤……”
“讀書有什麼用,女孩子總歸要嫁人的……”
在高等教育階段,諸如此類的聲音試圖阻止女性踏入科研大門。而當她們進入高校系統,生育、家務勞動等“天職”,則將她們擠出更多的機會之外……
然而,即便不斷遭遇貶抑與打壓,我們依舊看到,越來越多女性投身學術志業,匯流進學術共同體。對她們來說,學術研究不僅是事業、愛好,更是體認自身,尋找與世界相處的方式。
于是,我們有了一個樸素的想法:讓更多女性學者被看見。
當女性決定投身學術事業,她們需要克服多少阻礙?是否存在屬于女性的學術傳統?在“重男輕女”的學術體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學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參照?她們的同行者又是誰?
帶著這些疑問,我們邀請了來自社會學、歷史學、新聞傳播學、文學等不同領域、不同國別的女性學者,有些是大眾所熟知的,更多的則還在聚光燈之外。她們的經歷很相似,也很不同。她們代表了不同代際的女性知識分子,對知識懷有熱情,也曾經歷困惑與挫折。她們的故事講述了大部分現代女性的不滿與困惑,野心與夢想。
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必在“學者”之前加上“女性”二字。
這是“女性學者訪談系列”的第五篇。受訪者是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毛尖。受新媒體篇幅所限,本文為節選,完整版本將收錄于新書《女性學者訪談系列(第一輯)》,希望大家持續關注“女性學者訪談系列”。

歲末年初,一部《愛情神話》引發了迷影圈不小的波瀾。你方唱罷我登場,“爭奪著”海派精神的話語權。紛擾中,不少讀者呼喚,毛尖老師怎麼不說兩句。之后,毛尖果然發了影評。三言兩語,就道盡了所謂中產電影的脈絡與內核。她寫《從此,沒有鐵證如山的愛情》:“太陽升起,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都從生活那里領到溫柔的諷刺。革命的六十年代結束,高達的洶涌過去,中產登場,不要再用熾熱的燈火,不要再玉石俱焚,不要眼花繚亂的貴胄也不要哭哭啼啼的窮人。”
沒錯,還是“毛尖體”那熟悉的勁頭。戲謔與莊重齊飛,寫意共準確一色。寫影評這件事,毛尖已經做了25年。大多數讀者認識她,也是從影評開始的。《非常罪,非常美》《例外》《有一只老虎在浴室》《我們不懂電影》,這些作品已經成為討論當代電影評論繞不開的文本。但毛尖又不僅僅是影評人。能在漫長的時間隧道里,保有文字的鋒芒,同時開掘電影的歷史感與當下感,這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非常罪,非常美(增訂版)》,毛尖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4月。
上世紀90年代,毛尖進入華東師范大學英語文學系,從莎士比亞到簡·奧斯汀,新鮮的滋養撲面而來。但幾乎與此同時地,毛尖羨慕著隔壁中文系的兄弟姐妹們。問及原因,她插科打諢,“人家陰陽調和,不像英文系的男女比例跟肉絲和面似的”。于是乎,研究生階段毛尖轉入中文系,師從王曉明研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同門師兄師姐有金海、羅崗、倪偉和李念。那段求學時光,洋溢著熱烈的學術熱情與動人的同門情誼,他們熱情的文學討論被結集到《無聲的黃昏》一書中。他們談及了“后朦朧詩”與80年代以來的新詩發展,還討論了彼時中國的散文寫作與日趨技術化的文學批評。20余年過去,如今讀到這本小書,仍然激發著我們當下的敏感、悟性和想象力。
1997年,毛尖進入香港科大,跟隨主治古典文學的陳國球先生讀博。毛尖苦讀古典文論,“算是補古典方面的缺”。彼時,李歐梵也在香港科大任教,剛剛完成《上海摩登》的書稿。李歐梵的課程大量涉及上海文學和電影,這一時期對毛尖后來的研究方向影響很大,她的博士論文就做了上海三四十年代的電影研究。讀博期間,毛尖還翻譯了李歐梵的作品《上海摩登》,這本扎實通達的譯作也成為上海都市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文本。
博士畢業后,毛尖進入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任教。從西向東,再從東向西,毛尖的研究游走于東西之間,也貫通于古今之中。這樣的碰撞令毛尖保持著一種深刻的傳統性,同時又從這傳統性中生發出了一種先鋒性。

毛尖。受訪者供圖。
2006年開始,毛尖和她的師友一起在上海開設跨校的“文化研究聯合課程”,為大學生講授當代文化理論。這一課程在2010年停了一年半后繼續,前后持續十年。課程會介紹前沿的文化研究理論,但主體還是經典理論。她一方面經歷了對文化研究理論的“狐疑”,另一方面又在這種狐疑與警惕中繼續前行。課程講稿《巨大靈魂的戰栗》出版時,毛尖在序言《最好的時光》中感嘆,那些坐在一起討論文學的時光,正是她“想象的頭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大學的意義青春的形狀”。她還在其中寫道:“希望這文學課堂成為生活的意志,成為修正生活的意志。”
對于女性學者的身份,毛尖調侃,“在我自己的研究生涯中,可能我比較麻木不仁,我沒太覺得受到歧視。”她警惕太執著于單一話語視角,這肯定會造成理解的粗暴。但是她也觀察到對于更多的年輕女性來說,要進入學術,受到的壓抑性力量越來越大。
在采訪中,毛尖提及,當我們批評這個世界的時候,也要守住自己的體溫。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當下,這同樣可以為我們的思考與行動提供一些線索。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對毛尖的專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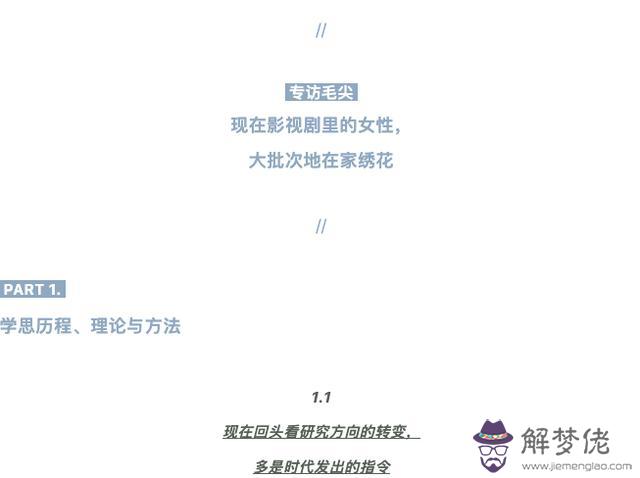
新京報 :在大學教育之前,你的閱讀經驗是怎樣的?
毛尖 :我們上世紀七十年代生人,少年閱讀從一開始就是分裂的。社會主義文學是主流,手抄本、海外文學是暗流,叛逆年代,坐在教室里賣身不賣藝,心思全在金庸梁羽生身上,老師家長越苦口婆心“朱德的扁擔”,我們就越不三不四。那時錄像廳跟著一起進來,雖然被我們看成黃片的港臺片,最多也就衣服滑落一下,但是,大銀幕上,接吻還主要是企圖,《少林寺》里,壞人王仁則一把扯破牧羊女的褲子,就能紊亂我們的小心臟,看到海外電影中的床上鏡頭,哪里受得了。
但與此同時,主流閱讀也從來沒有真正退場,或者說,集體主義這些概念,已經構成我們的潛意識,只不過時間走到八十年代,六十一個階級兄弟是兄弟,“燕云十八飛騎,奔騰如虎烽煙舉”也是兄弟,看到喬峰段譽虛竹,在天下英雄面前義結金蘭,準備同生共死,我們沸騰的熱血,和看《保密局的槍聲》一樣一樣的。

電影《保密局的槍聲》(1979)劇照。
新京報 :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決定走學術之路的,為什麼決定留在學校里做學術研究?在之前的采訪里你調侃說做學術是因為留戀學校、寒暑假。又“反省”說自己是一個坐不住的人,很好奇這樣的性格特點是如何影響你的學術研究與寫作的?
毛尖 :進了華東師范大學英文系,進教室,男女比例跟肉絲和面似的,去文史樓上課,看人家中文系陰陽調和,就想著得換個專業。如此大學畢業就轉到中文系跟王曉明老師讀書,同門師兄師姐有金海、羅崗、倪偉和李念,他們每個人都是我老師,尤其羅崗,常把福柯、羅蘭巴特掛嘴上,搞得我們這種文藝青年馬上自覺文盲,也跟著裝神弄鬼苦學了一年新批評、結構主義,不過其時王老師已經轉向人文精神大討論,我們也自然席卷其中。
今天回想,這場討論雖然在很多議題上沒有真正說服我,比如在王朔問題上,我至今覺得當年把王朔看成虛無主義是很大的誤會,但王老師、徐麟他們投入這場討論時的不舍晝夜和嚴肅認真,卻長久地影響了我們,讓我覺得成為一個人文學者,也有十面埋伏短兵相接,有一個意識形態較量的疆場。所以,你要問我一個坐不住的人,怎麼能成為學者,這個問題,當年研究生面試,王老師也問過我,估計他也覺得我生性好動,宅不住學者生涯的寂寞,但是今天,反過來我倒也想說,一個特別坐得住的學者,在這個壞人壞事層出不窮的世界,是不是也算不上特別的優點?當然,這麼說,帶著點滑頭離題的成分,不過我的意思很直接,很多太坐得住的人,也不一定適合成為一個人文學者吧。
新京報 :你大學求學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是一段寄寓了國人復雜情感的時期。一方面是席卷而來的文化熱,另一方面又揭開了一個劇烈變動時代的序幕。你曾在主編叢書的序言中寫道:“上世紀80年代我們求學那陣,為了一個講座去坐三小時的公車。”那段時期對你的閱讀和思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毛尖 :最近剛看了一個日本電影,《駕駛我的車》,算是2021年日本最佳吧,具體內容我不描述了,其中男主有個習慣,他是戲劇導演和演員,喜歡一邊駕車一邊練習臺詞,為了這習慣,他去別的城市,也故意選擇住在離劇院很遠的地方。回到你的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時為了聽一個講座或會議,經常會從華師大跋涉去別的學校或作協等機構,交通不便的年代,三個小時很正常,但從來不以為累,一方面當然是年輕,另外一方面,這路上的時光,也很豐富,尤其聽完講座,趁熱回鍋,有一次,過于激動,集體忘了買車票,又不甘心被罰,和售票員吵架,然后被趕下車,索性一路沿蘇州河走回學校。聽的什麼講座,記不得了,但是傍晚蘇州河的骯臟景象,觸動我們,坐在公共汽車上,只看到蘇州河波光粼粼。這種狀況,蠻有時代隱喻。
文化熱帶來文化爆炸,剛好也是我們自己身心爆炸的時代,爆炸對爆炸,有時會有特別璀璨的結果,我們如狼似虎地閱讀各種西方名著,把《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當教材看,把所有的課程都變成西方文學課,談情說愛不引用普魯斯特就顯得不夠全乎,校園里最轟動的講座,也都是作家學者的先鋒文藝主場,像今天海報上的大公司CEO、CFO根本不可能占據學校禮堂,詩人能帶走校花,總裁還不能。但爆炸對爆炸,常常也會彼此閃瞎對方眼睛,就像我們呼啦啦登上公交,呼啦啦又集體下車。
所以,回望那段日子,過去我們都喜歡講那個年代抒情的一面,每個人都是猛虎薔薇,如今時代翻頁,倒是可以更誠實地來談談那時蘇州河并不干凈的景象。比如當年全國人民奉為偶像的人物,今天看看,有些也就是《萬尼亞舅舅》中的謝列勃里雅科夫教授,自私自戀又自大,領著時代往個人主義道上發酵。

電影《萬尼亞舅舅》(1970)劇照。
新京報 :從上海到香港再回到上海,求學地點的變化也伴隨著專業選擇的變化。從英美文學到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研究再到影視劇研究,你如何回顧這20年的學術研究轉變?是什麼促使你探索、鎖定最終的研究方向?除了在專業上的轉變,還有什麼重要的節點標志了你在學術研究上的重大變化嗎?
毛尖 :就我自己而言,這些轉變更像是時代發出的指令,或者說,我們就像時代的APP,時代的每一次版本升級,也會拖著我們作出改變。大一寫作課,格非和宋琳給我們上的,先鋒作家先鋒詩人,搞得班上不少同學,白天課堂睡覺,晚上帶瓶墨水去通宵教室寫作,我也去了幾次,小說沒寫出來,但結識了不少中文系朋友。他們對我們外文系言必稱莎士比亞很看不上,覺得沒個性,如此一邊逼著我們去看冷門作家,一邊對中文系生出一些莫須有崇拜,所以,我后來轉到中文系讀研究生,前面說的養生愿望,雖然也真實,但更主要的是,那個年代的中文系有一種邪魅感,好像他們守著另一條道路,和傳統不同,和課堂不同,他們和藝術系一樣,生產著一些離經叛道的人物,光頭或者長發,長衫或者亂穿,他們向站在世紀轉角處的我們示范什麼是混亂和思想,后來我們泥足深陷,才發現他們的邪魅也不過是套路。
如此,等到王老師持續推動人文精神大討論,在文科大樓一場又一場激烈直接的討論中,我第一次體認到現當代文學的學科精神。那時候,王老師給我們上課,經常是用沉郁的語氣,大量使用問句,“你想想,中國現在的危機是什麼?你再想想,讀書人該對國家負什麼責任?”這個“你想想,你再想想”被文尖推廣后,成了我們的口頭禪,而研究生三年,在我整個的求學生涯中,是最重要的時段,尤其王老師用他剛剛完成的《魯迅傳》和我們討論魯迅,使得未來,我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總覺得背后有魯迅的目光。
我自己后來寫專欄,無論是思考還是語言上困頓的時候,都會去魯迅那里找資源。再后來,我從香港讀完博士回到華師大任教,一邊上課,一邊也和煉紅一起旁聽了薛毅的魯迅課。對我們這一代影響最深的學者,也一大半是魯迅研究專家,包括王富仁、錢理群、李歐梵和汪暉老師等人。因此,雖然我不敢說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是魯迅,但魯迅從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在所有的中國作家和思想家中,只有他能以表情包的方式活在全中國人心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他的思想和修辭從來沒有過時。
新京報 :師從王曉明時期,文化研究進入了你們這一學術共同體的視野?又是如何從文化研究轉向影視劇研究的?
毛尖 :很大程度上,正是魯迅式的追問,使得王老師帶著我們在上個世紀最后幾年轉向了文化研究,那時候我們相信,用我們的高溫,向這個越來越低溫的社會,吹點“熱風”。我們一起做熱風網站,起早貪黑地在網絡上發聲,也確實聚攏了不少人。一邊,我們聯合上海六所高校的老師,周末做文化研究聯合課程,迫使一大批研究生博士生周末來上課,現在想想,當年真是愚公的力氣,集體備課集體授課,到處借教室,還給看門的大爺買煙。當然,后來我們這群人也各自轉向,但熱風時期的熱情已經舍利子一樣存在于歲月中。
至于我的影視劇研究,和陸灝很有關系。1997年,陸灝辦《萬象》,我開始寫電影,似乎還受讀者歡迎,陸灝就一直催我寫,他催一次我寫一篇,直到《萬象》易手。后來陸灝編文匯筆會,他叫我開了一個“看電視”欄目,我又開始轉向寫電視劇。所以,我做影視劇,本質上是業余的,但因為是業余的,也就沒什麼習氣吧。

《萬象(第七卷第五期)》,《萬象》編輯部編,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
新京報 :你們的“文化研究聯合課程”,為大學生講授當代文化理論,課程講稿《巨大靈魂的戰栗》出版時,你所作的序言感動了許多讀者,那一段經歷給我一種強烈的共同體情誼之感,教師之間、學生之間、教師與學生之間都構成了一種由學術熱情聯結的共同體。也有評論指出,其中的文本解讀還是較多偏向傳統的文學理論,當時授課的初衷是結合更多的前沿文化研究理論嗎?后來,你曾經提及自己對文化研究產生了很多的“狐疑”,這種“狐疑”主要指向什麼,可否展開講講?
毛尖 :從2006年開始,2010年停了一年半后繼續,前后大概十年,課程會介紹前沿的文化研究理論,但主體還是經典理論,比如第一節課就是文尖講的《表征》,那時文尖腿上還打著鋼釘,拄著拐杖講了半個學期,薛毅又接著講了半個學期的盧卡奇。《巨大靈魂的戰栗》是其中一門課的結集,我在序言中寫過,為什麼要在文化研究聯合課程里開一門看上去如此傳統的經典作品選讀,是因為,當我們批評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要守住自己的體溫。而經典文本,是建立體溫的一個途徑,一種傳統。
今天回頭看,當年開這門課的決定是多麼正確,文化研究后來發生的一系列問題,包括你提到的我的“狐疑”,都跟研究者體溫的消失,或者說,歷史感的消失有關聯。粗糙地說,我的狐疑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文化研究在國內短暫地成為“顯學”后,政治正確的立場很容易被學生習得又隨便操作,學生一面手機里反復播放著她喜愛的歌曲,一面在作業里對這首歌各種批判。好像只要政治正確,學術研究就一勞永逸。“永遠站在弱勢者一邊”成為機械空洞的口號后,文化研究連內卷都卷不起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常常又顯得沒門檻似的,學個半學期就能對人民生活指手畫腳,好像全中國就他們洞穿了節日是資本家的陰謀。
當然,這些狐疑主要來自我對自己卷入其間的上海文化研究的一些觀察,我討厭站位高調門花的研究,如果一個富士康工人歌唱他的工作,是不是就該死?如果廣場舞大媽穿著LV舞蹈,大爺是不是就該送大媽去上文化研究課了?文化研究喜歡批評官僚主義,但有時他們自己的調門,就非常官僚學術體,既得不到生活認證,也得不到身心檢驗。

《巨大靈魂的戰栗》,毛尖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4月。
新京報 :你曾提及著名學者李歐梵對你的學術之路產生很大影響,他對你的影響具體是在哪些方面?你在香港讀書時翻譯了李歐梵的著作《上海摩登》,為何當時會選擇這本書翻譯?其中的文化研究、都市研究對你的學術研究興趣、研究方法產生過怎樣的影響?
毛尖 :1997年,我到香港科大跟陳國球老師讀博。陳老師主治古典文學,我在陳老師的教導下,苦讀了一年古典文論,算是補古典方面的缺,但終究不敢寫古典文學方面的論文,陳老師博雅通融,讓我自己選。當時歐梵老師在香港科大任教,剛剛完成《上海摩登》書稿,給我們上課也大量涉及上海文學和電影。老師的課對我影響很大,后來博士論文就做了上海三四十年代電影,寫得不好,你別追問我博士論文。老師用他的《摩登》書稿上課,他叫我翻譯,我就一邊上課一邊譯。一個學期課程結束,書稿譯完。中文稿《上海摩登》第一版因為用的是老師的英文未出版稿,內容比后來正式出版的英文稿還多了點。說實話,不是我翻得有多快,真心是老師的論述系統漂亮又明確。他創造了一個摩登話語體系,所有的概念都絲絲入扣歷史和文學史,加上他有自己的修辭追求,整個翻譯過程對我而言,不僅是學術訓練,也是寫作訓練。之后,我花了比翻譯長得多的時間找《上海摩登》中的引文和注釋資料,老師很多資料扔在美國,我回上海找,有些上窮碧落下地庫也找不到,也因此知道,這個摩登宇宙用了多少周邊資料。
現在回頭看,歐梵老師對我的影響,是全方位的。記得有一次,我們幾個學生和歐梵老師一起去銅鑼灣看侯孝賢的《海上花》,因為確實很沉悶,加上還滬語,就有人不耐煩,在座位上弄出聲響,歐梵老師輕輕一句“鏡頭真美啊”就把我們鎮壓了。本質上,歐梵老師是藝術家、學者、作家三位一體。桑塔格對偉大的作家有個分類,要麼是丈夫要麼是情人,借用這個分法,歐梵老師跟加繆很像,他是一個有著情人外表的正派丈夫,或者說,他是一個有著狐貍品格的刺猬。有的人看到他出入摩登場合的風光,有的人看到他在圖書館皓首窮經的堅毅,有人覺得他高調戀愛太不像個大學者,有人覺得他一件西裝從芝加哥穿到哈佛太不修邊幅,但所有的矛盾在他身上匯聚,顯得毫不違和,好像是,他重新定義了生命中的很多概念,用這個方法,他擴大了學術的邊界,讓原來彼此反對的范疇可以互相疊加,他的“上海摩登”就是這樣撐開了上海研究和摩登論述,霓虹燈下和霓虹燈上,都可以在摩登界域里被理解。《上海摩登》也因此在全球范圍內推動了上海熱。

《上海摩登》,李歐梵著,毛尖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
書中關鍵詞都是時間空間和人物的三一律交匯處:舞廳、咖啡館、公園、跑馬場、娛樂場、電影院、飯館、百貨公司以及大馬路,歐梵老師用本雅明注視巴黎的激情注視上海,但他的批評框架并沒追隨本雅明對巴黎的構造,20世紀的上海也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紀的帶拱門街的巴黎,老師從“上海是如何被寓言化”這個問題出發,重新整理了一百年前的都會時空,然后把它們兌換成一個能指所指新宇宙,上海也在“摩登”這個總的意象里敞開,用這種方法,歐梵老師重新發明了現代文學重新發明了上海。這種本雅明-李歐梵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一直讓我很膜拜。當然,二十五年過去,我自己對“上海摩登”這個框架也有一些零星再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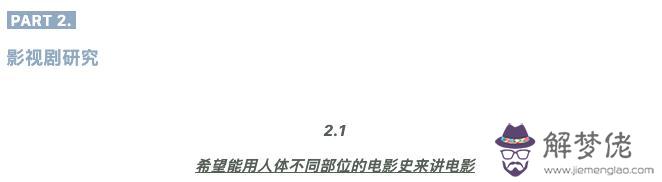
新京報 :你曾經從五官的呈現來講授法國新浪潮電影的特點,剖析它在電影史上的位置和創新。這一角度很少有學者關注。你會經常進行類似的(在課程與研究上的)新嘗試嗎?這樣的嘗試反饋如何?在電影研究或授課中是否還有其他類似的嘗試?
毛尖 :用人體不同部位的電影史表現來講電影,確實是我的一個想法,但我至今也只零星地上過兩次課,沒有能力用一門課的架構來實踐。也許以后。主要我一直覺得,電影研究應該有自己的脈絡史,目前而言,無論是導演研究還是主題研究,大量沿用的是小說研究法,我之所以講“嘴唇史”“眼睛神話”“屁股進化史”,就是想徹底從影像角度,讓電影研究獲得自己的屬性。這些年看很多學生電影論文,他們基本是對電影進行內容概括,然后一堆分析,完全不顧阮玲玉的眼神葛優的手勢,這就離題了。
所以現在有很多小視頻論文,雖然常常簡易又粗暴,但在影像層面倒是更貼合,因為當張曼玉說我們分手時,她的身體語言可能是渴望更進一步的,這些,在大量書面論文中,單一地被臺詞篡奪了。影像時代,對直接影像的關注,其實是非常容易引導的,比如昨天我們上到白沉導演的《大橋下面》(1984),先討論了一番新時期的人道主義思潮,弄堂現實主義,然后我們聊到龔雪的臉,這樣就從龔雪的臉說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演員的臉,說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臉,以及今天的臉,在臉的線索里,龔雪的臉構成美學轉向的實錘,影像討論很能接入學生的身體經驗,他們未來的電影研究也不可能不管身體語言、風景語言。
新京報 :在你主編的《巨大靈魂的戰栗》一書中,你的好友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羅崗老師提及,電影和女性特別是女性身體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歷史:“……影片呈現了中國婦女和電影之間曖昧的歷史——電影科技既給她們帶來身體解放和社會地位變動的承諾,又對她們的身體加以商業化、物化,從而導致了新的誘惑和危險。”你如何看待電影的歷史與女性身體的關系?電影(攝影機)不可避免地征用和展示女性的身體,這一凝視關系也被很多學者討論,你認為電影與女性身體的關系是否影響到了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態度?
毛尖 :羅崗的觀察非常精準。雖然女性身體被物化的危險自古存在,經典文本里的美人很多都有被送去傾國的作為,但是電影毫無疑問加劇了這種誘惑和危險,加上電影的發生和資本主義的發達時期共生共構,攝影機的凝視和女性身體關系,更加歷歷在目,這方面的討論已數不勝數。不過,時間已經走到2022年,羅崗在聯合課程講這番話也有十五六年,我們再打開這個議題,是不是得有雙邊視角,尤其當代男主越來越被當女主用的今天。前段時間《風起洛陽》播出,王一博的影像位置和攝影機注視方式,遠超當年阮玲玉的份額。或者說,今天的女明星已經失去影像C位,那麼,該如何看待當代女性的銀幕失落和重返C位的努力呢?籠統地說,很容易得出美男登場是對女性物化的加劇此類結論,但這樣的結論有什麼意思呢?雌雄同體或中性美學怎麼看呢,一定要從消費視角看的話,美男不也是一種分流?但電影生態主義者同意分流說嗎。

電視劇《風起洛陽》劇照。
你說到電影會不會影響到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態度,我的關注重心其實已經倒轉,可能首先,我們要問的是,今天的電影,還有多大的身體權威,攝影機的凝視更危險,還是我們一天到晚凝視著攝影機,讓攝影機怕了?男色登場,在影像的意義上,可能更是電影危機的一個信號。今天,決定女性對自己身體態度的,與其說是電影,還不如說是淘寶是美圖秀秀。膠片時代的電影權威一去不復返,在新人類的文化份額上,電影已經遠不如抖音快手,逼著我們倒轉思路了。再說,元宇宙電影已經在路上,身體問題,已經不光是凝視的問題。
新京報 :你在此前的采訪中提及,“國產劇中的女性主義往往表現為對失戀的應激反應”。可以看出主創對女性的生活想象很缺乏,人物也很單薄,除了圍繞家庭與情愛的糾葛很難給予女性角色更多的成長契機。以你的觀察來看,為何國產劇創作會在女性問題上如此狹隘?有沒有哪些(國產/非國產)影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創作值得借鑒?
毛尖 :國產劇,絕大多數都是懶惰劇,也就是套路劇,等到套路擴張到女性主義場域,也會出現一大批神兜兜的面具女權,所以,國產劇不是在女性問題上如此狹隘,國產劇是整體性的狹隘。當然,體現在女性表現上,特別觸目。拿2021年的電視劇來說,女性的主要工種,又回歸女紅。《風起霓裳》(2021)、《驪歌行》(2021)、《錦心似玉》(2021),女主都是刺繡專業戶, 靠繡藝上能進入最高級宮廷政治,下能拯救失業女性于水火,當然,最重要的是,嫁得深情官人。滿屏刺繡,刺繡跟古代女郎的高考似的。這也算了,畢竟古代,然后,《你若安好便是晴天》(2021),現代劇也蘇繡,實在轟毀。這一整年的刺繡,沒一個有東方不敗的精氣神。大敵當前,林青霞扮演的東方不敗天女散花,一枚枚繡花針奔騰而去,遠勝令狐沖們手中的劍,那樣凌厲又浪漫的刺繡才有點現代精神啊。反正,當今的女性影像平臺上,有男人愛,有兩個以上男人愛,有多民族男人愛,是女性等級的表征,如此,一旦失戀,剩下自己面對自己,只好去搞事業,這種應激的獨立是女性主義的話,那狗跳墻就是物種進化了。
所以,有時我還寧愿去看影像政治效果不正確的劇,比如《美國夫人》,劇中,女主菲莉絲·施拉夫利領導了一場反對平權法的運動,擊敗了當時風頭強勁的女性主義者,且永久地改變了美國。理論上,施拉夫利的勝利應該讓觀眾,尤其女性觀眾痛心,但是觀眾的態度是曖昧的,因為恰好是在保守者施拉夫利身上,呈現了女性主義需要面對的現實bug。劇中有一幕,支持平權法的隊伍和反對的隊伍在相反的道路上互相回頭彼此打量,前者多是年輕女性,后者多為家庭婦女。隊伍的割裂就是歷史的天塹,這方面,我們的電視劇倒是油光水滑,因為我們連一支平權法的隊伍都沒有,年輕女性貌似要和男人攜手天涯,但奮斗的終點都是遇到一個更有條件更有資產愛我的人。

美劇《美國夫人》劇照。
新京報 :在此前的采訪中,你提及中國的影視劇很多是“偽現實主義”或者是“粉紅現實主義”,而極度缺少“硬現實主義”作品。在近一兩年的作品中,你這一觀察是否有變化?有沒有印象深刻的更接近“硬現實主義”標準的作品出現?
毛尖 :我強調“硬現實主義”,就是希望我們的影視作品能對現實發動強攻。2006年開始,中國電影大規模市場化,大資本涌入,電影井噴,但硬現實主義越來越少,大量影視劇都在表現次要矛盾或者,矛盾的次要方面而不是主要方面,鋒利度下降,粉嘟嘟一點,自然安全又好看。就此而言,我會覺得去年的《山海情》特別好,因為此劇直面了當時最重大的社會矛盾。《山海情》出來后,有不少知識分子認為此劇對少數民族表現不力,的確《山海情》沒怎麼表現回族,但撇開大家心知肚明的影視政策,劇中中國,首先要解決的是貧窮問題,這個絕對貧困是我們的首要問題,需要老少邊窮總體性解決。在這個元級別敘事里,少數民族問題完全可以留待未來展開。

電視劇《山海情》劇照。
而從知識分子的這個批評可以回看我們電視劇的總體問題,就是真正的國家劇太少。現在我們很多劇,也在各種觸碰社會問題,比如倫理劇中的老人問題,孩子教育問題,比如懸疑劇中的城鄉問題,貧富不均問題,這些都是重大問題,編導也因此覺得自己硬杠了現實,走的是現實主義路線,但是,在大的倫理或懸疑框架下,這些問題都只能分集性呈現,一旦夫妻矛盾敵我矛盾解決,這些矛盾也跟著打包消失,像2020年熱播的《三十而已》,女主為兒子上幼兒園費盡心思,童叟無欺是當代中國家庭正在經歷的巨大煩惱,但這個問題是外掛在男女主情感問題上的一個議題,當他們情感轉向的時候,這個議題也就不了了之。也是在這個邏輯里,我會覺得《覺醒年代》中,雖然北大或蔡元培絕對被過度美化,但沒有影響建黨主敘事,《覺醒年代》也依然是好劇。這是電視劇的大局觀。
說實在,大平臺太應該出手打造國家劇了,借此,也能打造人民的大局觀。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的《讀書》,曾經有這個大局觀,現在這個時代任務已轉手影視劇,但我們沒接好。有時候,看著這麼多情智雙低的爛劇在網上消費群眾,真心有一種恐怖感,這些影視劇在生產什麼樣的沙發人群啊。
新京報 :上海一直是中國電影當中重要的背景/故事發生地。從你的研究視角回顧,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到近來的《三十而已》《愛情神話》等影視作品,上海在影視劇中的呈現與互相影響,有怎樣的變化?
毛尖 :新中國成立前,上海是中國毫無爭議的電影中心,當時的上海形象不僅可以從《馬路天使》(1937)《十字街頭》(1937)這些影片看出來,還能從好萊塢歐洲電影中的上海表達看,比如《上海風光》(1941)。靡靡之音串場左翼歌聲,世界級的藏污納垢交疊世界級的貧富分化,上海以“夜”的形象自我代言。共和國電影里的上海改變了面貌,雖然霓虹燈下還埋伏各種危險,但《今天我休息》(1959)《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以白天的上海,健康的上海,揭開了上海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銀幕好天氣。然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夜上海路線回歸,夜來香百樂門,唱啊跳啊到今天,越來越把上海符號化。在這個勢態里看上海電視劇,就能看到電視劇和電影的不同追求。無論是《孽債》(1994)還是《兒女情長》(1996)《奪子戰爭》(1997),都有非常結實的上海普通百姓生活。

電影《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劇照。
坦白說,這些劇當年上映的時候,我還不是電視劇觀眾,對于當時深受現代主義美學影響的我們,光這種劇名本身,就會覺得電視劇屬于父母行為。不過,偶爾在電視上看到,常常又挪不動步子。像《孽債》,開場五個西雙版納小孩跑到上海找父母,五個孩子展開的不同的家庭關系,從里弄到外貿大廈,橫切了一個時代截面,巧妙又貼切,而且不同年齡層不同階層的上海話,各種腔調,如同不同區域的上海,支持不同人物的行動邏輯。在看得見東方明珠的高樓里辦公的男人,和在電影院里當放映員的男人,雖然當年同是插友,但環境分疏了人群,兩人氣息就很不同,雖然階層表現也略有刻板之嫌,但整體非常接地氣。
不像現在,影視屏幕上各種上海符號,但上海顯得越來越沒性格,也越來越單面。上海成了背景板,街道里里弄弄,不再構成人物的成長因子。比如《流金歲月》(2020)里的朱鎖鎖,她身上完全沒有上海弄堂的系譜。你說的《三十而已》(2020)也是,三女主和上海的關系,就像P上去的,換個其他大城市,這個故事可以一模一樣照搬,全部成立,上海就等同于這個劇組的服化道。不過最近出來的滬語電影《愛情神話》,又讓上海活回自己了,鏡頭貼心又信仰地表現了上海生活的散文流,估計會引起一些文化批判。

電影《愛情神話》劇照。
新京報 :技術的變革引發了電影的巨大變化。流媒體、高幀率電影、VR等等,近來“元宇宙”的概念也越來越吸睛,這一設定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電影的敘事邏輯。你認為這些變化會如何影響電影的未來?你曾經說對電影的未來是悲觀的,在什麼意義上理解這樣的悲觀?
毛尖 :VR會是和電影院并存的一種介質,就像3D電影、120幀不會一統江湖。當然,這個話題很容易吵成一團,像嚴鋒老師就認為未來影視劇會成為游戲的分支。未來影視劇,包括網劇的體系會經歷一個重構,那是一定的,流媒體殺入后,影視劇的美學會經歷革命性變革,也是一定的,Vlog美學會強有力地滲透進來,時間革命、空間革命會大過其他方面的所有革命,個體體感會改造群體體質,這些都是可見的未來。
但我相信,即便是傳統意義上的電影,也還會經歷一個長衰期,在這個總體悲觀的長衰期里,電影也不是完全沒機會。就中國而言,社會主義時期的電影美學沒有被真正打開過,這個國家光輝跌宕的歲月也沒有被好好表現過,銀幕依然是貘,就看我們喂它夢還是虻。
而技術上看,就算在元宇宙界面里,元宇宙的電影想象也還是能夠提供方法論,用來殺滅一批當代爛橋段,比如元宇宙的生死概念,可以改寫當代電影中的大量爛情爛死爛失憶。當然最后,這個問題,也不能在電影內部來回答,就像改變出租行業的,不是汽車,是支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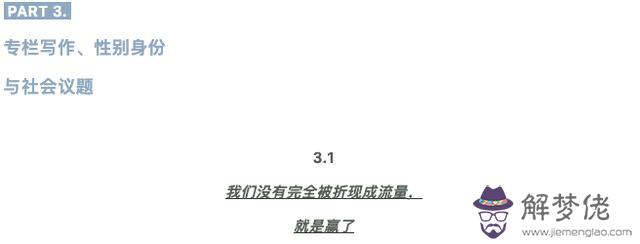
新京報 :你的影評寫作獨樹一幟,形成江湖人稱“毛尖體”的高辨識度文風。你如何看待這種旗幟鮮明的寫作風格?這一風格是如何形成的,是渾然天成還是逐漸打磨尋找的結果?同時,你的寫作也跨越多個文體,從論文到雜文、影評,你如何平衡不同文體的寫作?
毛尖 :江湖所謂“毛尖體”,不過就是以麻辣快的方式,以普通讀者的視角寫文章。于我很簡單,這是長期專欄的一個結果,千字卡死,賦比興一通的話,剛開頭就得結束了。因此,毛尖體,往上說是接地氣,往下說是不怕死。精力旺盛的時候,我同時在十家報紙上寫專欄,一天能得罪好幾撥朋友。不過,除了作家,我的另一個身份是大學老師,“毛尖體”也說明我不太會用學院派的方式來寫影評。
至于說在不同文體間平衡,我也沒那麼牛逼。而二十多年專欄寫下來,關于文體,我自己的界定是,1000字屬于一種文體,5000字以上,又是一種,所以,約稿,我都第一時間問字數,超過2萬,我打退堂鼓,那得虛構。寫小說要換體質,也不是沒想過,好多師友鼓勵過我,崔欣都催了我好多年,偉長把小說名字都給我取好了,《鐵證如山》。還是我自己沒準備好吧。

《凜冬將至:電視劇筆記》,毛尖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6月。
新京報 :影評寫作是一份很容易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它要求極高的準確性但卻常常被誤認為門檻很低(劇情簡介+觀后感)。同時,圍繞影評寫作、影評人,還有諸多其他爭議。比如拿紅包給好評,拿紅包刪差評,“你行你上”“不會實干就會扯淡”等等言論。你如何看待圍繞影評人寫作的諸多爭議?
毛尖 :影評門檻確實不高,這個,反過來理解,也應該是好處,這樣可以席卷更多群眾加入。諾貝爾文學獎的影響力遠大于其他獎,就因為文學獎,誰都能嗑上幾句。加上這些年的影視劇,一大半是爛劇,罵罵咧咧,誰還不會呢。所以,我從來都說,我們影評人,干的是清道夫的工作。在這個平臺上,我對拿紅包這件事,也并不嚴厲,雖然我也可以問心無愧一句,我自己從來沒有為紅包寫作,但這也因為,我不是專業影評人,不靠影評謀生。再加上,我寫影評,雖然起源是約稿,但也自帶了一些自以為是的使命感。對我影響很大的學者,很多也跨入過這個行業,包括歐梵先生。因此,最初,我是非常自大地以為能改變點影像生態而成為一個影評人的,當然,馬上被按倒在地了。有一次一個制片人打電話給我,讓我給他做的電視劇寫篇文章,我脫口而出,沒法寫啊這麼爛,他一點不覺得被冒犯,興奮地說,那你罵呀,往狠里罵。所以有時想想,影評人寫作,有爭議,在今天這個大環境里,不算壞事情了,我們沒有完全被折現成流量,就是贏了。
新京報 :對于青年女性學者,很多人曾提到感受到當下社會中結構性的性別制度與歧視問題。在你過往的研究生涯中,有遇到過類似的困惑與阻礙嗎?對于有志于學術事業的青年女性學者,你有哪些建議?
毛尖 :在我個人的研究生涯中,可能我比較麻木不仁,倒沒太覺得受到歧視。當然,雞零狗碎的女性降維事件總是有,但是我也不太想把這個說成是歧視。二十多年前,研究生報選題,我要說我寫周作人,王老師馬上就會CUT我,羅崗說他做周作人,王老師立馬就同意,不過也沒覺得是歧視,因為羅崗確實強,加上還有合適不合適的問題。不過,我的心態跟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學校,一直生活在弱循環環境中有關系,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我的成長年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還為我們撐著天干地支。
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走到今天,我有時候會覺得,我們在文化上是越來越封建,由此年輕女性要進入學術,受到的壓抑性力量也會越來越大。現在的文化事件,動不動就是劈腿被人肉,離婚揭老底,加上政治正確和沒有偏見又是時代政治的一部分,赤橙黃綠青藍紫任何一種膚色都不能得罪,上層和下層哪一層都不能罵,文化變成溫吞水。在這個溫吞水大鍋飯里,女性會是首先被煮熟的青蛙。加上以前的歧視很容易被識別,現在喜旺們也學乖了,絕不會說出你就在家繡繡花做做飯這樣的話,他們也讓李雙雙去面試,但用其他題材勸退李雙雙。
而且,就像我前面說的,現在影視劇里的女性,大批次地在家里繡花,被勸導成為新世紀劉慧芳,或者畫眉入時地在高樓大廈隨時準備跟總裁發生碰撞,不像社會主義時期的影像,女性用結結實實的勞動站在天地間,女性能直接跟壞人壞事做斗爭,現在好人壞人都長差不多了。所以真的是難。
新京報 :有沒有哪位女性學者/作家/寫作者的作品對你產生過重大影響?
毛尖 :2018年上海師大做了一次許鞍華電影周,我的三個女性榜樣有過一次同臺,她們是:戴錦華,王安憶和許鞍華,我主持了她們的對談,是我特別認真準備但一句話沒敢亂扯的一次。我自學電影,就是看戴錦華老師的書。這些年,我們做電影研究文化研究女性研究,也大量地是在戴老師的延長線上工作。戴老師做冷戰諜戰,我們跟著追到《天字第一號》。戴老師談切格瓦拉,我們把切格瓦拉掛在墻上。戴老師始終在前沿,始終比我們年輕,她身上混雜了強烈的十九世紀和二十二世紀感。無數年輕女學者,都或多或少受到過戴老師的影響。安憶老師,一直在上海寫作,她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進入文學史了,但她至今都在勻速地持續地高質量在寫作,雷打不動天天在寫,別說是上海,整個中國如果沒有王安憶的創作,都畫不成一個版圖。許鞍華老師,是我最敬重的華語電影導演,她的電影定義了香港新浪潮香港電影史,她本人定義了愛和藝術的強度定義了生命的寬度和深度。她們三個人身上,都有無比強烈的少女感,一種任何痛苦和時間都奪不走的斗志,每次和她們在一起,都有吸氧效果。

電影《天字第一號》(1946)海報。
而在我的同代人中,也有三位女性深刻地影響了我,她們是,張煉紅,賀桂梅和董麗敏。我們幾乎一樣大,有非常相似的歲月記憶。煉紅為她的《歷煉精魂》豪擲二十年,桂梅除了抽煙,麗敏除了打牌,幾乎都從不浪費時間,她們永遠在綿密地推進自己的思考,她們,包括前面講到的王安憶戴錦華許鞍華老師,都在讓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最強悍的天賦,就是勤奮。我自己不是懶惰的人,很多朋友,也覺得我看書看劇很勤奮,但我仔細想想,我是憑淫欲學習,她們是紀律,我很容易陷入虛無,她們則不。她們都給自己的才華加上了紀律,如此才能用一生來過關斬將。能和她們一起成長,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事情。
新京報 :你曾經在散文中提到父母的相處,“當我翻翻現在的文藝作品,影視劇里盡是些深情款款的男人時,我覺得我父親這樣有嚴重缺陷的男人,比那些為女人抓耳撓腮嘔心瀝血的小男人強多了。而老媽,用女權主義的視角來看,簡直是太需要被教育了,但是,在這個被無邊的愛情和愛情修辭污染了的世界里,我覺得老媽的人生干凈明亮得多。”這段話非常動人但透露出某種“政治不正確”的危險,如何理解這一段話?我在此前的(你的友人)文章里讀到,說也是你照顧兒子、照料家庭更多?你會覺得這造成困擾或負擔嗎?
毛尖 :沒錯,這段話有嚴重的政治不正確傾向,但我說這個話有一個語境,它的話語對象是,當代文藝中的蒲志高。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為了愛情耽誤工作的男人,成了影視劇中的抒情對象。比如《我的前半生》(2017)中,寶馬男追離異女主,為了給她兒子過生日,放棄工作放棄大生意,如此,女主感動死,觀眾見證真愛。對比一下社會主義時期的文藝,真正是天差地別啊。《今天我休息》(1959)中,女主聽說男主是為了幫助群眾誤了約會,馬上不別扭了,一直到八十年代都這樣,《煩惱的喜事》(1982)里,電機修理工田建,加班加點為人民服務結果耽誤第一次見丈母娘,女朋友玉婷也沒什麼怨言。反正,在那個年代,勞模愛勞模,先進工作者喜歡先進工作者,都是天然。工作高于家庭,集體大于個人,婚姻向社會讓渡出一點家庭時間,天經地義的事情。我媽之所以愿意伺候我爸一輩子,是因為我爸確實把他的精力都奉獻給學校了。一個中學校長沒有家庭的支持,很容易心力交瘁的,當然我也不能說我媽完全沒怨言,但是,那個時代的情感法則鼓勵為人民服務,大環境如此,我們家這樣,鄰居家也這樣,沒人因此鬧離婚。

電影《煩惱的喜事》(1982)劇照。
在這點上,我們這一代女性應該也還算同時繼承了社會主義的為國奉獻和為家庭奉獻的精神的,而照顧家庭照顧孩子,其中樂趣也不容抹去。當年,《真是煩死人》(1980)中,家庭主婦覺得一個洗衣機就能解決家務煩惱,現在我們什麼機器都有了,所以,困擾和負擔,一定程度上也是時代情感的一個變量,也是在這個議題里,今天的愛情修辭絕對是個污染源。
新京報 :談到女權主義議題時,很容易引發諸多難以解釋清楚的負面情緒與爭議。你提及很害怕公開談論女權問題,是否有此擔憂?你認為涉及女權主義話題,為何總是產生如此多的對立情緒?
毛尖 :這其實不是女權主義領域的特殊問題,當我們太執著于單一話語視角時,肯定會造成理解的粗暴。而由于粗暴引起的爭議,又是媒體樂見的,所以,稍微一觸動,就花火四濺了。曾經有一次做活動,我對#MeToo運動說了句擔憂的話,馬上被下面一個女生站起來教育一通。當然,也不是說我真的害怕,只是這種情況,會讓人覺得,武俠挺好的,如果能動手,就不動口了。
新京報 :以前讀到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說“不要成為你所反對的東西的對應物”。在女權主義的問題上,一方面我們提醒自己需要時刻警覺,我們批判父權話語與壓迫,但同時我們又要避免成為他的對應物,以至于思考與生活局限于性別視角。雖然出發點可能不同,但你肯定也有注意/思考到這種批判與現實之間的張力。或者說,理論與現實之間總存在齟齬,理論無法完全指導生活。但你似乎很好地處理了這種不對應關系,作為一名學者,你如何看待理論與現實之間存在的縫隙?
毛尖 :誰拿著理論生活,誰肯定一敗涂地啊。理論要是能指導生活,理論界的幸福指數不該全球最高了?看看我們小說和影視中的主人公,搞理論的,最后不都活成了時代的壁紙?《獵場》里,祖峰扮演的文藝理論家,是不是死得最早?作品中直接搬理論,編導不弄死你,觀眾也處死你。至于你說我處理得好,事實是,我從來沒有把學者當成我的主要身份。我的生活中沒有這些嚴肅的矛盾,我的痛苦和理論沒關系。所有和我的身體經驗八字不合的理論,我進不去也用不來。
題圖來自電視劇《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劇照。
作者 | 張婷
編輯 | 青青子、羅東
logo設計 | 郭鑫
校對 | 賈寧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7823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