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平
徐賡陛是暮年李鴻章的“總文案”,晚清最著名酷吏,曾活埋疑犯致死,也是查封繼昌隆機器繅絲廠的罪魁,為人“棱角峭厲”,怨家甚多,卻又極善鉆營,總能化險為夷。徐賡陛跌宕起伏的一生,突出反映了一些酷吏的行事風格,有助于加深對晚清官場的認識。

李鴻章、徐賡陛在天津
活埋鄭承望
徐賡陛(1847-1907),字次舟,浙江烏程(今湖州)人,1867年以副貢生報捐福建通判,因回避改省廣東,歷署遂溪、陸豐、南海知縣。徐賡陛聰穎異常,筆頭了得,在廣東官場歷練數年,窺見做官的底蘊。他為人極有主見,作風雷厲風行,頗得一些上司賞識,也經常得罪各方勢力。徐賡陛當州縣官以嚴酷著稱,多次被人控告濫殺濫捕濫施酷刑,其中以活埋鄭承望一案最為聳人聽聞。

徐賡陛
光緒七年底,有京官參奏,徐賡陛光緒五年“在陸豐縣任內,下鄉催糧,一鄭姓老人年七十余,因語言觸犯,該通判令兵役將其活埋致死,掩至半體,令勇目黃德用加砍一刀”。朝廷降旨要求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嚴查。次年農歷三月,署兩廣總督曾國荃復奏,因當事衙役供詞游移,鄭承望之子事發時不在現場,以“事關濫殺,亟應嚴究”復奏。朝廷收到復奏,重申“徐賡陛著即行革職,聽候訊辦。鄭承望被埋身死一案,情節甚重,必須嚴切究辦”。接奉上諭后,曾國荃派人查辦,以“城廂內外并無徐賡陛”奏請通緝。(1883年10月2日《申報》)徐賡陛在衙門有內應,在下達通緝令當天馬上自首,這樣可以洗脫“負罪潛逃”罪責。

曾國荃
惠州知府將鄭承望之子鄭媽厚、勇丁黃德勇、門役鄭安三人解到省城審問。羈押期間,重要證人鄭安在候審公所病故。1884年,張之洞接任兩廣總督,傳集更多當事人、證人,指定廣州知府等官員會審,最后由張之洞親審定讞。按張之洞1885年給朝廷的奏折所述,鄭承望“素性兇橫”,與分居胞弟鄭承霖不睦,時相欺凌。光緒五年七月十八日,鄭承霖雇人挑稻谷到圩市售賣,鄭承望教唆其子鄭媽厚糾集人眾把稻谷搶走。鄭承霖妻向縣里呈控,差役抓獲搶稻谷的鄭牛建,在解縣途中被鄭承望帶人將鄭牛建搶走,并毆傷衙役。
當時,徐賡陛正下鄉催征,即于八月十六日率領勇役來到鄭村,將鄭承望抓獲,朝村外走,鄭承望一路高聲叫罵,徐賡陛叫衙役拿刀勒在鄭承望脖子下,想讓他停口,不料鄭承望繼續叫罵,衙役即用刀戳傷鄭承望喉嚨,倒地不起。徐賡陛察看傷情,認為不能存活,下令在路邊挖一個兩丈多深的土坑,把鄭承望反縛雙手放入坑中,填土至肚臍眼處。不過,填土高度,民間另有一說是到胸口處。不久,鄭承望死于坑中。當時,鄭承望妻重病,其子鄭媽厚畏罪回避,沒有親人在現場,次日由鄭承望兩個女婿收尸下葬。
張之洞奏折的立場明顯,即想盡辦法為徐賡陛脫罪,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鄭承望的罪名加重,認為犯了“應死”之罪,這樣徐賡陛虐殺鄭承望就變成“擅殺應死罪人”,按大清律例定擬,最多只判杖責。(《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111輯第572-582頁)其實鄭承望搶奪胞弟鄭承霖稻谷,僅值一兩五錢,應是兄弟之間因細故而發生的欺凌行為,稱不上“搶劫罪”。徐賡陛一定要殺死鄭承望,主要是他極大地冒犯了官威:一則是毆傷差役、放走了鄭牛建;二則是在解縣途中破口大罵。通過虐殺鄭承望,徐賡陛以雷霆萬鈞之勢,給陸豐縣一眾“豪強”“土棍”敲了警鐘,也給尚未繳納錢糧的花戶極大的震懾。
張之洞早就耳聞徐賡陛能名,欲加以重用。候審期間,徐賡陛不斷給張之洞上呈稟稿,提出各種建議,還替張之洞寫壽序;同時,徐賡陛也幫當時省里面的中高級官員代寫條陳,這些官員都會在張之洞面前為他說情。全面檢視張之洞奏折,各個環節都可以看到徐賡陛積極運作的痕跡。他發揮自己熟悉律例條文的優勢,把鄭家罪名加到最大,自身責任減到最輕,“刀筆吏”形象躍然紙上。
張之洞出任兩廣總督后,下決心改革相沿已久的幕府制度,把幕友改為文案委員,削弱資深幕客對權力的把持。當時廣東勢力最大的師爺沈彬,與徐賡陛有過節。張之洞利用徐賡陛收集的黑材料,將沈彬驅逐,然后把徐賡陛等人引入督署,作為文案委員,代替之前“師爺”的工作。徐賡陛就這樣以待罪之身,在張之洞幕府中充任“總文案”。(《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六卷第218頁)張之洞為徐賡陛脫罪,正是看中他的利用價值。
俗話說,“天上雷公,地下海陸豐。”廣東海陸豐地區民風驃悍,彭湃同志能在此率先開展農民運動,與此不無關系。案發時,徐賡陛正在鄉村征糧,他擔心的是民間抗糧,必須用強硬手段處置民間反抗行為,以此威懾全縣,讓花戶知所畏懼,乖乖納糧。活埋鄭承望是徐賡陛立威的手段。對省級高官來說,徐賡陛的做法固然過火,但目的在樹立官府權威,無論如何必須加以支持。故而,歷任兩廣總督張樹聲、張之洞都想盡一切辦法包庇他。鄭承望罪不至死,而各級官員卻一定要給他定“必死之罪”,這是由官場共同利益所決定的。
查禁機器繅絲廠
光緒七年(1881年),徐賡陛從署陸豐知縣調署南海知縣。南海為廣東首邑,兼轄省城西關,是廣東經濟最發達縣份,以絲業聞名于世。我國第一家機器繅絲廠陳啟沅創辦的“繼昌隆”即誕生于此,徐賡陛則是破壞機器繅絲業的罪魁。
1881年嶺南酷暑時節,南海縣官山圩舉人陳植榘向縣署報告,八月十三日下午兩點鐘,來自大崗圩的1000多名手工業工人沖進官山,將“裕昌厚”繅絲廠大門打爛,搶走廠內物品后逃逸。“裕昌厚”是機器繅絲廠,由舉人陳植榘、陳植恕于光緒五年(1879年)開辦。陳植榘請求知縣派出武營兵丁到場彈壓,維護正常治安秩序。這一年,是陳啟沅創辦繼昌隆機器繅絲廠的第9年。
徐賡陛立即派人下鄉探查,聞知:南海縣學堂鄉有“裕厚昌”“繼昌隆”“經和昌”三家繅絲廠,采用機器繅絲,每付機器每天可繅絲四五十斤,與400個手工工人的產出相當。大崗圩手工工人對此積有怨氣,遂以“錦綸堂”名義糾集人眾,搗毀“裕厚昌”絲廠機器,乘機搶掠絲繭、銀錢、衣服,并有殺人情事。徐賡陛批詞曰:“匪徒借端搜搶,固屬罪不容誅;而市儈專利病民,亦屬情難曲恕。”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但傾向性十分明顯,把事件的發生歸咎于機器繅絲廠“專利病民”,并勒令所有機器繅絲廠立即停工,“概行封禁”;當然,查辦鬧事主謀以及殺人嫌犯,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徐賡陛《不自慊齋漫存》卷六)
徐賡陛出示曉諭的第二天,仍有手工業工人二三千人持械搖旗攻撲學堂鄉,雖經兵勇彈壓,依然吶喊沖鋒;學堂鄉也有了準備,增筑圍墻,雙方槍炮齊施,打死1人。徐賡陛這才意識到,手工業工人依仗人數眾多,仗勢欺人,甚至藐視官府。他不得不派出大隊兵勇,赴華夏鄉、莘涌鄉抓捕匪徒馮亞敬、馮兆炳等人,首犯馮亞津、馮亞蒂則已聞風潛逃。
徐賡陛對此事的認識,深刻地反映了鴉片戰爭四十年后,與西方接觸頻繁的廣東南海地方官對世界經濟發展、技術進步毫無了解。他認為“各省制辦機器,均系由官設局、奏明辦理,平民不得私擅”。徐賡陛以為絲業大量采用機器導致手工業工人失業,實際上并不成立。幾年后,候補知縣李長齡在給張之洞的報告中說:“自用機器以后,窮鄉貧戶賴以全活甚眾,而向來繅絲工匠執業如故。緣機器所繅絲經,質細而脆,以銷外洋,頗獲厚利。若內地機房,既不肯出此厚值,且因其絲過細,不甚堅韌,以織綢緞故不相宜,仍以土車手繅為便,故兩不妨礙。”
觀念陳腐的州縣官扼殺近代工業,不僅徐賡陛一個例子。1872年,南海知縣杜鳳治處理中國第一家機器紡紗廠案件,也是不公不平,在債務金額甚小的情況下逼迫大股東賤價拍賣機器,初步形成的近代生產力被消滅在萌芽狀態。廣州厚益紗廠的債務問題,很容易通過債務重組、招徠新股東注資加以解決,重獲生機,但南海知縣不覺得這是他的職責所在。
勒索香港首富計劃
1882年,徐賡陛賦閑時,為廣東官場人物捉刀寫了不少稟稿,其中一份《請詰究奸人密揭》可謂驚世駭俗,提出以莫須有的罪名指控香港首富李陞家族、勒罰巨款的詭計。這個詭計最終沒有被上司接納,但李陞家族事后聞知應該嚇出一身冷汗。

香港首富李陞
廣東新會人李良、李陞兄弟,饒于資財,咸豐年間廣東各地發生洪兵起義,為安全計避居香港,經營金山莊(從事北美、澳洲貿易)、當鋪、銀號、賭場、鴉片、包辦苦力出洋等生意,迅速發家,1876年列香港納稅額第12位,1881年躍升到第1位,是名副其實的香港首富。李良早逝,李陞負責管理整個家族生意,兄弟子侄眾多,在商業上均各有成就,其中李陞、李德昌1882年出資創辦廣東華合電報公司,鋪設從廣州至九龍電報線,對中國在中法戰爭收集傳遞法軍情報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徐賡陛摭拾浮言,誣指李陞兄弟曾隨英軍北上參與進攻京津,提供十幾萬元給英軍作軍費,戰后從英軍索取的賠償中得到數百萬元,家中還保留著從圓明園劫掠的皇家珍寶古玩。徐賡陛做了一點調查,李氏家族在本籍新會縣有財產20萬,在廣州、佛山約30萬。徐賡陛進一步誣陷,說法國此次侵略越南,李氏家族還在經濟上接濟法國人。徐賡陛私下給李氏家族判了十惡不赦的大罪:“以中國臣民,叛向外酋,協助軍資,攻犯京闕,跡其罪狀,本可夷族。……該犯擁貲如此之多,所犯如此之罪,若能誘獲到案,從重罰捐,則一二百萬餉需不難立致。”(徐賡陛《不自慊齋漫存》卷七)當時法國侵略越南,兩廣總督張樹聲正發愁軍費無著。徐賡陛向張樹聲獻計,把李陞引誘回內地,用莫須有的罪名加以恐嚇,隨便勒索一二百萬不成問題。好在張樹聲并不糊涂,這個詭計最終沒有實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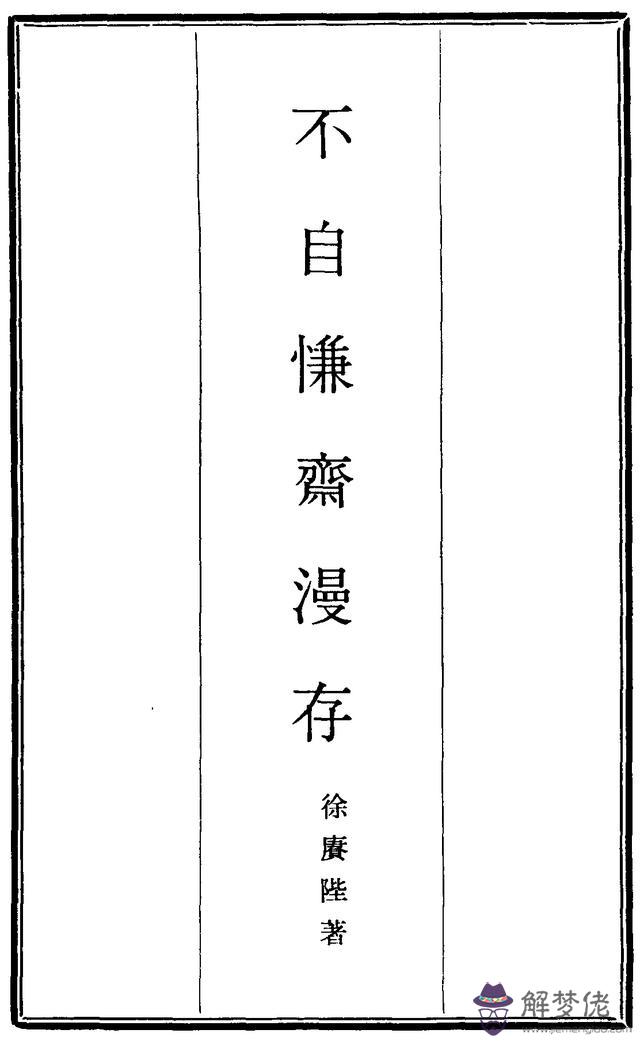
徐賡陛《不自慊齋漫存》
徐賡陛詭計體現了當時不少官員對商人、企業家的態度。毋庸諱言,早期香港企業家曾經從事過諸如鴉片貿易、販賣豬仔這樣的生意,道德有虧,但當時的法律并沒有明令禁止。清廷嚴禁豬仔貿易之后,李氏家族已經收手,法律的一般原則是不究既往。所謂跟隨英軍進犯京津,查無實據,至于說從中國戰爭賠款中取得數百萬元,則完全是無稽之談。徐賡陛只是想用這些莫須有的“罪名”進行恐嚇,目的是敲詐一筆巨款,向上司邀功。當時廣東省每年的歲入(財政收入)也就四五百萬元,若此計得逞,確實能拿到一大筆意外之財。李陞家族早年的經營活動中確有道德污點,可以勸諭他們捐款辦理慈善事業,事實上他們已通過向香港東華醫院捐款,幫助救助華人難民,也協助內地救災。若僅從法律角度看,李陞家族可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張之洞力助脫罪
徐賡陛這樣一個兇狠毒辣的酷吏,卻是“清流”張之洞心目中的寶貝。督撫治理廣闊的地域,為完成維持治安和錢糧征收兩大任務,有賴于任用一批能干的酷吏,這是在明面上不能說出來的官場秘密,以學問著稱的張之洞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徐賡陛是官場文案寫作的頂尖高手,張之洞也需要這樣的刀筆吏。
徐賡陛在知縣任上突然被撤職,還有應納錢糧任務未完成,也即官場常說的“虧欠”。為給徐賡陛脫罪,張之洞下令給一些優缺州縣官,讓他們一起出錢替徐賡陛彌補虧欠,據李鴻章所述這筆數額巨大,應在萬元以上。1889年,廣東雷瓊道朱采寫信給李鴻章,把張之洞幫徐賡陛脫困、脫罪的秘事披露出來,引起李鴻章的極大注意。李鴻章回信說:
徐賡陛自是奇才,夙聞毀之者、譽之者俱不遺馀力,心識其人斷非庸品。來示評騭,符于向者之譽詞,然譽一而毀百矣。今日有如此人,何可多得,聞其年方壯盛,正可有為。曩者振軒拔之冗中,而任以首劇,今香帥復脫之罪籍,而令其典軍,又隸旌麾,鄉里深知,與為推挽,不可謂不遇,而再起再躓,詎非數奇,殆亦不善用其才之過。然以模棱巧避為善用,則更無任事之人。香帥能以萬金彌其官虧,必不令去粵可知矣。異日有事,此材必見思也。(《李鴻章全集 34 信函六》第528-529頁)
李鴻章之意,徐賡陛勇于任事,張樹聲重用他當首邑南海知縣,張之洞集資萬金為其彌補官虧,為之脫罪,雖然毀之者眾,譽之者少,仍是奇才,來日有事,此人可當大用。徐賡陛于1891年由山東巡撫張曜奏保,開復原官,以直隸州知州發往山東,1894年奉旨交張之洞差委,1896年被參降三級調用,1900年初調入李鴻章幕府。
跟隨李鴻章北上
光緒二十五年年底,慈禧立大阿哥,北京的形勢對洋務一派十分不利。李鴻章走榮祿的路子,得以署兩廣總督,離開是非之地。此前廣東在李瀚章、譚鍾麟兩個老邁的總督治下,盜匪遍地。李鴻章此來,借助徐賡陛霹靂治盜的經驗,“以毒攻毒”,殺人無數,一時之間,“地方亦賴以小安。”(梁啟超《李鴻章傳》)
1900年農歷五月十九日,慈禧上諭“李鴻章著迅速來京,兩廣總督著德壽兼署”。李鴻章收到電諭,告訴廣東巡撫德壽,他準備二十五日啟程。徐賡陛判斷北京形勢不對,提醒李鴻章延遲入京。后來,張之洞親信幕僚錢恂寫成《金蓋樵話》,認為慈禧此時召李鴻章入京,又不明言何事、調任何職,令人生疑,認為慈禧有殺李鴻章之意。李鴻章自恃功高,有些托大,幸虧徐賡陛及時提醒,止住腳步。
農歷五月二十五日,慈禧發布向列強開戰的上諭,宣稱要向各國“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并嚴厲警告各省官員“……茍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朕即刻嚴誅,決無寬貸”。這時從北京往外省的電報線已被義和團挖斷,這份上諭在短時間內未能廣為傳播,二十七日才送達山東巡撫袁世凱手中,轉發給李鴻章。
五月二十九日,徐賡陛為李鴻章起致盛宣懷、劉坤一、張之洞的電報稱:“二十五矯詔,粵斷不奉,所謂此亂命也。”(《凌霄一士隨筆》)這封電報行文斬釘截鐵,一字千鈞,盡顯徐賡陛風格。李鴻章以首席大學士兼兩廣總督,被視為疆臣領袖,電報奠定了“東南互保”的基礎,雖由李鴻章決策,電報起草人徐賡陛也功不可沒。
六月十二日,李鴻章被慈禧授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不方便繼續滯留廣州,決定到上海觀望形勢。六月廿一日,李鴻章乘輪起行,隨行幕僚為王存善、曾廣銓、劉學詢、徐賡陛,洋務唐紹儀,另有專任醫官麥信堅。次日,李鴻章在香港會見港督卜力,有一張著名的合影保留下來,李鴻章左邊第一人即徐賡陛。李鴻章左側第二人是醫官麥信堅,被錯認為劉學詢達數十年之久。

李鴻章與卜力、徐賡陛等合影
數年前,微博網友“浪客湛心”從1900年12月1日英文《海陸軍畫報》(The Navy and Army Illustrated)中發現了徐賡陛照片,標注為“Chui Kung Beh, Chief Secretary of Li Hung Chang”,意謂“李鴻章總文案徐賡陛”,Chui Kung Beh是按粵語讀音拼寫。借助這份畫報,“浪客湛心”還辨認出了李鴻章與卜力合影中的徐賡陛、麥信堅。筆者受此啟發,也在Underwood & Underwood公司發行的一張1900年的明信片中,認出徐賡陛在天津時與李鴻章的“合影”,照片中李鴻章倚靠茶幾端坐,氣定神閑,徐賡陛站在茶幾另一邊,神情有點緊張。
此次北上議和,徐賡陛一直陪伴在李鴻章身邊直到病逝,其間不僅起早了不少重要文件,李鴻章病情也大都由徐賡陛負責對外發布。李鴻章死后,徐賡陛加捐候補道,到江蘇任職,先后經管屯墾、鹽務緝捕多項事宜,1907年去世。
馀論
迄今為止學界對徐賡陛這個人物尚無專文研究。臺灣作家高拜石將傳說中徐賡陛斷案故事加以鋪張渲染,塑造出一個所謂“徐青天”形象,未作深入考證,多不太可信。
徐賡陛這樣的酷吏,具備混跡官場的特殊才能,卻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世界大勢全無認識,依然用陳舊的士大夫意識形態看待新生事物。1885年1月3日,日本學者岡千仞訪問廣州,與徐賡陛、文廷式有過一次筆談。徐賡陛質問岡千仞:“貴國學歐米(美),以三千年禮義之邦,一旦棄其舊,不可痛惜乎?”岡千仞回答道:“敝邦國是,在學萬國之長,而補其短。”(中華書局2009年《觀光紀游 觀光續紀 觀光游草》第170頁)兩國士大夫胸襟、眼界之差距,于此可見一斑。
甲午中日戰爭以前,沿海、沿江地區初步具備發展近代工業的條件,也涌現了不少企業家,他們開礦設廠的努力,往往受到州縣官的阻撓和壓制。一些香港華商早著先鞭,掌握較先進的技術和經營理念,擁有充足的資本,廣東地方官本應邀請他們回來投資;徐賡陛想的是誘致香港首富回來加以勒索,這也讓有意投資內地的港商望而卻步。徐賡陛自我塑造的所謂“強項令”形象,在實際做法上往往與近代以來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馳。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施鋆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6967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