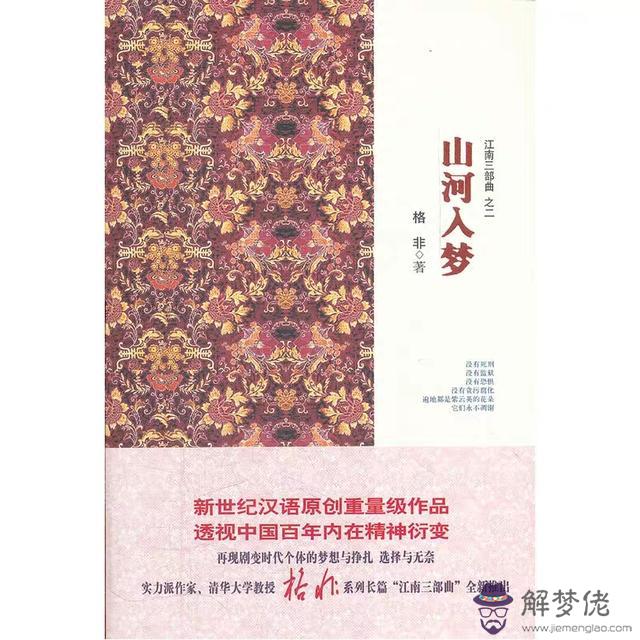
前言:
《山河入夢》是“江南三部曲”的第二部,故事的背景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江南。故事的主人公是《人面桃花》中陸秀米之子譚功達,譚功達繼承了陸秀米的烏托邦的理想。他是新中國的梅城的縣長,意欲將普濟的風雨長廊變成普濟的水庫大壩,將“桃花源”建成“人民公社”,實現理想中的“烏托邦社會”。
從上海流落到梅城的姚佩佩因偶然的事件而成為了他的秘書,二人有情感牽扯。譚功達下放到“花家舍”之后,憧憬著美好情感的姚佩佩難逃命運般的魔咒,落入了痛苦的深淵,走向了逃亡的悲劇命運。
評論家張清華曾這樣評價格非,“以較小的格局介入重大的命題,是格非寫作的一個特點”、“將社會歷史的重大命題,裝入到線條簡練的人物關系與結構形式中來處理”。張清華將格非這種敘事手段稱之為“歷史的個人化”。格非筆下的姚佩佩就是這樣的人物,透過個體在巨大的歷史中的無能為力,從而來思考現實與歷史,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個人的存在價值。
在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懷抱著自由理想主義的姚佩佩卻難逃宿命般的悲劇命運。本文將從意象入手來分析姚佩佩這個人物形象,揭示她悲劇的命運。
 一、意象的闡釋
一、意象的闡釋所謂意象,就是客觀物象經過創作主體獨特的情感活動而創造出來的一種藝術形象。簡單地說,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來寄托主觀情思的客觀物象。
在比較文學中,就是主觀的“意”和客觀的“象”的結合,也就是融入詩人思想感情的“物象”,是賦有某種特殊含義和文學意味的具體形象。簡單地說就是借物抒情。
奧地利作家卡夫卡曾說過,“我總是企圖傳播某種不能言傳的東西,解釋某種難以解釋的事情。”
深受卡夫卡的影響的格非是借助意象來“傳播”或“解釋”一切難以“難以解釋”或“不能解釋”的事情。
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學王國,魯迅的王國在魯鎮,莫言的王國在高密東北鄉,而格非的王國在那個江南水鄉,在那個“記憶的樞紐和棲息地”。
在江南三部曲中,來自江蘇丹徙的格非使用大量極具江南地域色彩的意象:“花”、“雨”、“夢”等意象。這些意象的大量使用,既表現作者的審美理想,也是作者寫作風格的轉變,回歸傳統小說敘事方式。
對文本中的意象的分析,不僅能更好地把握文本中人物形象,而且還能更好了解小說的文本內涵。
筆者將從“花”“夢”、“雨”等意象來分析姚佩佩的人物形象,揭示其命運悲劇性。
 二、“花”——修辭性的隱喻
二、“花”——修辭性的隱喻“花”與“女性”從來都是相關聯的,古今中外的作家都喜歡以花喻人。如:“美人一何麗,顏若芙蓉花”、“娉娉裊裊十三余,豆蔻枝頭二月初”、“一枝紅艷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斷腸”。
在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中,曹雪芹給十二金釵的每一位女性都挑選了相關聯的花。跟林黛玉相關的花的意象有:芙蓉花、桃花、菊花、柳絮等等,這些花朵意象的變化除了象征她的命運走向,還構成了她獨特的女性氣質。
深受《紅樓夢》影響的格非同樣為姚佩佩選擇了相關聯的花,而這些相關意象的花是:菊花、桃花、紫云英。
A、菊花:傲立霜雪,天生的原罪“我這種人,或許生下來就是有罪的呢!”
“我是一個孤兒,在這個世界上并沒有親人。”——《山河入夢》
姚佩佩原名姚佩菊。父親在建國初期因犯革命罪而被逮捕槍決,母親隨后上吊自縊,從此她的命運恰似菊花,受盡磨難。親戚們埋怨是由她的名字“佩菊”乃“佩帶菊花”而帶來的煞氣和詛咒,并把她視為不詳之人。
因此姚佩佩選擇改名字,除了想掩蓋不愿提及的過去,還想忘記痛苦的記憶。
13歲的姚佩佩遭逢家破人亡后,從此遭受了“寄人籬下”的痛苦,受盡姑媽的冷嘲熱諷,過著“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風刀雪劍嚴相逼”的日子。后來遭到姑媽的驅逐,她先是在梅城浴室里賣籌子,后又到曾經是妓館云集的胭脂地的絨線鋪里賣絨線。
她如菊花般,一生凄苦,無依無靠。后在譚功達的幫助下,進入縣委的機關單位。
對于姚佩佩來說,政治上“天生的原罪”讓她過上了寄人籬下的苦難生活,她似乎只有不斷地逃離。當她掙脫了下層苦難的生活,來到了體面的縣委,生活軌跡似乎改變,卻依然沒有改變苦難和悲劇的宿命。
她如同菊花一樣,品性高潔,可身世凄苦凋零,難逃命運的捉弄,受盡寒風的摧殘,陷入了漩渦的陰謀,走上宿命般的逃亡之路。
 B桃花:春意盎然,萌發的愛意
B桃花:春意盎然,萌發的愛意姚佩佩因家庭的緣故,她的生活從云端墜入了泥里,從此她冷眼旁觀這個社會。面對殘酷的社會生活,她毫無反擊之力。她只能把所有的憤怒及所有的哀傷深埋在心里。
當她被譚功達帶到了類似于“大觀園”的縣委機關里,可“來路不明” 的原因遭受到同事的冷眼與嘲諷。官場知識的匱乏讓她“不知道這個縣到底有幾個鄉、幾個鎮、少個自然村就是縣機關到底有幾個下屬單位都沒有明確的概念,”因此每個月的評優她只能墊底。
她的苦悶無人傾訴,她的憂慮無人可解,她只能在洗手絹的時候默默流淚。這時譚功達把手搭在佩佩的肩上,給她無聲的安慰!正是這無聲的安慰、有形的大手讓佩佩想起自己的父親,讓她感受來自塵世間的溫暖,“它真的就像我爸爸的手”,“他那麼大,那麼溫暖”,她在同事的起哄喊譚功達“爸爸”時,心里默默地叫著“爸爸”。
“直到有一天,這個秘密被另一個更瘋狂的秘密取代”,她愛上那雙給她溫暖的大手的主人。而她與譚功達的感情在文章雖一直不甚明朗,但桃花卻隱喻她與譚功達的感情正如初春的桃花一樣春意盎然,美好。在縣委機關短暫安定的生活正是姚佩佩家庭變故之后最為美好的時光。
桃花隱喻姚佩佩美好愛意的萌發,及對純真之愛的向往。桃花代表的是孑然一身的孤苦女子心中執著的愛情,雖花期不長,卻也絢爛動人。
 C紫云英:自由和希望,精神的烏托邦
C紫云英:自由和希望,精神的烏托邦格非曾說:“我在這個人物里面融入了自己對世界的態度——疑問和絕望,她一直躲在陰暗的角落里守著脆弱的自我,身上有一種強烈的內省的東西,她不是混沌不清,而是無可奈何。”
高曉松曾說:“這世界不只眼前的茍且,還有詩與遠方。”
紫云英是非常不起眼的小花,生命力極旺盛,只要種子一撒,風一吹,雨一淋,那漫山遍野都是紫云英。姚佩佩也正如紫云英一般,生命頑強,她向往美好和自由。家庭變故之后,哪怕她面對慘淡的事實,可她卻依然渴望親情,當她“用全部羞恥堆積起來的勇氣”叫了姑媽一聲媽媽,換來的從睡夢中驚醒的姑媽的一口唾液、一個耳光,及無窮無盡的難以入耳的羞辱之語。
此后的歲月里,姚佩佩只剩下“盡快逃走”,“逃走”似乎成了她躲不了的宿命。從上海流落到梅城,從姑媽家被趕走到了梅城浴室,從胭脂巷的絨線鋪到了縣委機關,在錢大鈞的陰謀中而被迫踏上了逃亡之路,從梅城逃走又回到了梅城被槍決。
正如姚佩佩心中所想的:“苦揀樹和紫云英地上的烏云永遠不會移走······永遠不會”

個體命運受到時代的沖擊, 對姚佩佩的心靈形成巨大的創傷,這種創傷并沒有停止,相反她承受的暴力接踵而來,小說對于女性的心靈苦難作出了一種切入骨髓的解剖。
譚功達把姚佩佩從舊時妓館云集地胭脂井“絨線鋪”的下層生活“解救出來”,她被提拔到體面的縣委機關單位,甚至還有機會往省委機關單位調動,可依然難逃宿命的安排。她雖身處權力中心,可她“不求上進”,追求愛與自由,而她的自由主義烏托邦理想注定只能被強權政治擊落得粉身碎骨。
姚佩佩是錢大均討好上司、謀得前程的法寶。當譚功達是縣長時,他自以為窺視了上司的“隱秘的心思”,將她分配到譚功達辦公室當秘書。當市委秘書長金玉對姚佩佩表示有興趣時,他更毫不猶豫伙同湯碧云設計佩佩,她不過強權政治與男權下的一個犧牲品。
“女性生命沒有過多受制于歷史的羈絆,而‘偶然事件、異乎尋常的外來事物、卑微甚至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情形’則可能無意見對其精神命運產生深遠影響。”
政治的天生原罪讓她敏感,讓她厭惡當官的人,更想遠離權力的中心。當譚功達被撤職后,她知道金玉對她有非分之想。上至錢大鈞下到姑媽都是金玉的說客,威逼利誘。她都不為所動,辭職,遠離縣委,逃離一切想掌控她人生的人。
她立馬辭職拒絕權色交易,回到底層的生活。可從此貧困地度過她的余生并不是她的宿命,她低估了人性的惡,好友湯碧云的妒忌及狠心出賣了她,將她帶到了宿命的風暴之中。
她被金玉強暴之后,屈辱讓她殺了金玉,成了被通緝的殺人犯,走上了注定“逃亡”的宿命中。命運給她的歸宿是:從出逃的那天,她就注定逃脫不了被送上刑場的命運。
“天空又高又藍,一棵孤零零的大揀樹矗立在花地中,一看到那蜿蜒起伏的煤渣公路,看到那棵大揀樹,我的眼淚馬上就流了出來······我知道自己來到了什麼地方”

她曾夢想去尋找一個荒島隱居,“她要把小島的每個角落全部都種上紫云英”“隱姓埋名過一輩子”。在那個如火如荼的建設年代,她的不思進取、敏感,她固有的純真、自由主義思想都與周圍的一切都格格不入。正是姚佩佩的抵觸,毋論是否金玉之死,在當時的制度姚佩佩是否要抵命;或哪怕金玉沒有出現,也會有下一個錢大鈞、下一個湯碧云將她推入命運的漩渦!
時代的洪流裹挾著每一個人前進,而時代容不下一個固守不變的多余人。當她逃亡之際,她不怕泄露行蹤依然寄信給譚功達,表現她對人類純潔愛情的執著追求,及她在苦難面前的堅韌及頑強。
她逃亡之路戲劇性是繞著高郵湖轉了一個大圓圈,似乎預示著她難逃宿命,冥冥之中每個人都有命運的軌跡,梅城的山河最后成了姚佩佩掛在眼角的一滴殘夢。姚佩佩注定難以走出宿命,難以走出現實,難以走出自己的影子!
紫云英隱喻姚佩佩的自由和希望,她的精神烏托邦是去一座孤島上隱居,而這種烏托邦的建構體現了社會的后退,從歷史意義上及主觀能動性來說,宣告具象烏托邦的虛妄。
 三、“夢”——串聯歷史的密碼
三、“夢”——串聯歷史的密碼中國古代文學家特別善于通過夢意象建構和夢境描寫,突破現實障礙,而展示自己的理想世界,實現自己的感情超越。——《夢與中國文化》
格非也借助“夢”的意象這個超現實空間的敘事,將宿命之玄滲透于無意識的領域,既是描寫人物心理、塑造人物性格、解釋人物行為的一種手段,又將對個人和社會、對存在本質的困惑拋給宿命論和讀者。
開篇姚佩佩夢見閻王爺在清明節派鬼抓她,而緝拿她的鬼就跟剛才攔車的警察長得一模一樣。這跟安娜·卡列妮娜一樣,姚佩佩一出場就和自己的命運邂逅,她看著警察留下莫名其妙的的淚,是因為她已預見自己的命運。
這個夢看起來荒唐可笑,可行文至末尾卻給人恍然大悟之感。孤島的“烏托邦理想”一直在姚佩佩的心中,盡管她已預見自己順流而下的命運,可逃亡不過是她宿命的向導,在河山之間的逃亡正是她在尋找那個荒無人煙的烏托邦似的小島。
在逃亡的路上,她忍受饑餓,不畏困難,反抗權威,無懼死亡,從追求身體自由到追求精神自由,是她對自由主義的生命追求的完美演繹。
另一個的夢境更富有傳奇性及神秘性的色彩,如同莊周夢蝶一般。文中這樣描述:
“他夢到十六七歲的姚佩佩扎著羊角辮,穿著紅紅的新嫁衣,站在滿是灰塵的大路上。那天剛好沒有風,云層壓得很低,而桃花全都開。”
接著姚佩佩的下一封來信,姚佩佩寫了她的夢境,竟然跟譚功達的夢一模一樣。連譚功達也嚇了滿身大汗,發出這樣的感嘆:“是我夢見了她的夢,還是相反?”
這個夢象征是此刻兩人心意相通,可一再地錯過及遲來地表露將故事推向了高潮了,而姚佩佩的愛情悲劇及命運的悲劇意味更濃了。
理想與現實,個人與歷史的二律背反是每一個存在的個體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姚佩佩一生都在追求“愛與自由”,她沒有經歷過人們所謂的美好愛情卻為了個體的尊嚴及純粹的愛情而亡命天涯,可到死的那一刻,她的愛情也沒有實現。
佩佩要自由,要追尋所愛,而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自由,死亡才是愛情的出路。
 四、“雨”——解讀文本的鑰匙
四、“雨”——解讀文本的鑰匙陳曉明曾說過:“在那些‘陰雨綿綿’日子或‘梅雨季節’,他們在難捱的等待中充分磨礪了感覺力,在辨析水珠滴答的聲響中感應到某種超自然的神秘性。”
生長在南方的格非在《山河入夢》中也多次運用到了“雨”的意象,這意象的運用推動了情節的發展,也成為了讀者循跡解讀文本的鑰匙。
文本的開始,姚佩佩與譚功達前往解決普濟水庫的糾紛的路上,那天也正下著雨,姚佩佩因想到傷心往事而落淚,借口臉上的是雨水來掩藏淚水。這暗示了佩佩的身世凄涼,如浮萍般無依無靠的個人復雜情感。
姚佩佩與譚功達初次在梅城浴室相遇,“天空中拋拋灑灑地落著雪珠”,姚佩佩臉上流著淚,“梨花帶雨”的臉吸引住譚功達的目光。當譚功達將錢遞給她,她“刷地以一下從他手里抓過錢來”并劃傷了譚功達的手。情境的設置,下雪天,臉上“梨花帶雨”的淚水,最初的相遇,便有這命運注定之感,也推動著情節的發展。
讓兩人的情感的升溫進入高潮,也離不開“雨”這個催化劑。因傾盆大雨而被困在辦公室的兩人,在辦公室認真討論退隱在“世外孤島”。因大雨困住的“孤島”烏托邦情境竟類似于賈寶玉跟林黛玉“葬花”。他們的愛情注定無法實現,正如他們的“孤島”烏托邦理想地不可實現。
因對好友湯碧云的輕信而遭到錢大鈞的設計被金玉強暴的那天,天氣是這樣的:“雨后的夕陽絢麗無比,烙鐵一般的火燒云,中間雜夾著翡翠般的淺綠,把西山襯托的如墨如黛”,大雨后的夕陽暗示了姚佩佩遭受暴風雨之后,夕陽般的命運,即將亡命天涯的蒼涼之美。
姚佩佩更在一個“細雨蒙蒙的清晨”被押往軍區槍決,結束了她的生命。在雨中開啟了她的故事,而她的故事也終止于“雨中”!
本文中的“雨”是她命運轉向的見證者,見證她一生的“雨”就如林黛玉的眼淚,終究有流盡的一天。“雨”意象常在人物精神變化處被運用,使人物形象更立體,也豐富了小說深刻的精神內涵。
各種意象經過作者的攫取和加工成為作者敘述的起點,塑造經典人物形象的道具,并推動著故事走向,深化主題;也是讀者循跡解讀文本的鑰匙,從而與經典人物會面,理解文本的內涵。
 結語:
結語:格非在研討會上說:“讀者對《山河入夢》小說本身如何評價我并不介意,我更在乎讀者對姚佩佩這個人物是否有誤解。這是我用心創作的人物,她的心理變化和世界的看法同我的內心世界很難分割。”
由此可看出格非高度贊美姚佩佩高貴的人格,姚佩佩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獨立,厭惡官僚化的體制,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她的悲劇在于她不肯放逐自我,跟當時的社會同流合污。
格非從悲劇現實出發,個體生命連隱居孤島理想都難以實現,展現個體生命無路可走的精神苦悶和生存困境,但個體生命仍要向黑暗和虛無做絕望地抗爭,從而掙扎出一種抗爭希望的力量,去證實死亡的虛無,證明希望和光明的存在。這種不妥協、不屈服的反抗意識展現了姚佩佩人格的偉大和生命的崇高。
她除了能自我拯救,連譚功達都能在姚佩佩身上獲得精神的慰藉,靈魂得到棲息,使得姚佩佩這個人物產生了一種無法阻擋的美麗。
正如羅曼·羅蘭《米開朗基羅傳》中所寫:“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熱愛它。”
高曉松曾說過,“愿你一生溫暖純良,不舍愛與自由。”
姚佩佩正是這樣的人,愿你我一生都是不舍愛與自由的人。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6862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