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鎮口有個老太,賣麥芽糖的。
只要愛甜食,誰都想和她套套近乎。
老太眼角有顆痣,姓寧,脾氣卻沒這個寧靜的意思,小孩見她都怕得很。給幾塊錢就是多少糖,老主顧都不會多送你一點兒。
麥芽糖講究功夫,講究細致,她一個年過半百的老太,好像能把五味都融進麥芽糖里似的,極吸引人。
糖是糖,是甜的。
我向來都不喜歡寧老太,但我喜歡她的糖。
我家里窮,實在沒錢買這個糖,又沒法學那些男孩去做工,只好和村里幾個淘氣包商量,說明天去她作坊里偷上兩塊。
小孩子的偷,怎麼能算是偷呢。
結果第一次就被她抓個正著。
男孩跑得快,丟下我就跑。我急得跺腳,眼淚嘩嘩地掉下來,心想慘了,寧老太得好好治我了。
霎時,藤條竹鞭的想象冒了出來,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寧老太果然陰著臉,拿著藤條出來了。
我怯怯地道寧老太,對不起。
她怒吼一句,女孩子家家的,偷雞摸狗算什麼本事,啊?
我被她吼得眼冒金星。
她剛抓起我的胳膊,將那藤條懸在空中,卻仿佛時間靜止般,停滯在空中。
咦,這是怎麼了。
我鼓起所有勇氣看向她。
她死盯著我手腕上的胎記看,眼神恍惚而驚愕。
寧老太低語道,你叫什麼。
我這胎記是生來就有的,有點烏黑發青,像是繩索纏了好幾圈留下的痕跡,算命的說,這是上輩子大喜大悲的痕跡。
于是娘給我取名叫楠。
于是我顫道,楠,我全名是吳楠。
諧音是無難。
不過長輩老對我娘指指點點,說這名字可真是好啊,無難,無男,怪不得連個男孩都生不出。
所以我娘死了。
寧老太突然放下了手中的藤條,只是緊緊抓著我的手。
我被她嚇壞了,眼淚依舊嘩嘩地往下掉。
后來我什麼也不記得了,只記得她破天荒地塞給我一包麥芽糖,最后不知是自言自語,還是問我了一句:
“你嘗嘗,甜不甜。”
糖是甜的,我愧疚地嘗著糖,心里依舊不解,怎麼這寧老太,還會對人好不成?
不過,好像有點太甜了呀,我想,要是再淡那麼一點點,就好了。
其實說我們小孩不懂,那是不對的。
村里的大人,見她都繞著走,又從來不說原因。
小孩接近她也只是為了糖。
要不是她的麥芽糖成為了特色,能吸引不少旅人,估計早就被鎮長勸搬了。
我娘走了后,我是一直寄住在二舅的家里。他早年喪妻,有個比我小的男孩,人腿腳不方便,但至少還是個善良的人。
這世道,善良有什麼用呢,鄰居這樣嗤笑著,一個怕老婆的廢物,還不是窮得連米都買不起?
我喜歡寧老太的糖,好像也有點喜歡她了。
我這樣說,是因為從她那兒回來之后,那群不要臉的淘氣包,聽說我不僅沒挨打,還白拿了一包糖,氣得哇哇直叫,直接就在放學路上堵了我。
喂,打頭的那個男孩子笑道,用了什麼法子,說說唄?
我撅著嘴,我說,她就是喜歡我,怎麼了!?
我自己都沒想到,脫口而出的話居然可以這麼自豪。
結果那群男孩就怒了,嚷嚷著不要臉,三四個男孩把我圍了起來,舉起拳頭就——
“個小不要臉的,滾開。”
一個中氣十足的聲音把他們嚇壞了。這群男孩,倒也是識相,頭也不回地逃走了。
我轉身,萬般委屈忽然涌了出來,化為了大滴大滴的淚。我不敢向她撒嬌,只是在原地喚道,寧老太……
她一個箭步上前,捏著我的臉,似乎想檢查下我有沒有受傷,但又掌控不好力度,直到我的臉被她掐出了一道紅印子,她才恍然大悟地撤去。
寧老太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她又從口袋里拿出一包糖,說送你吧。
我連忙擺手,可她力道確實大,一包糖又穩穩地落在了我口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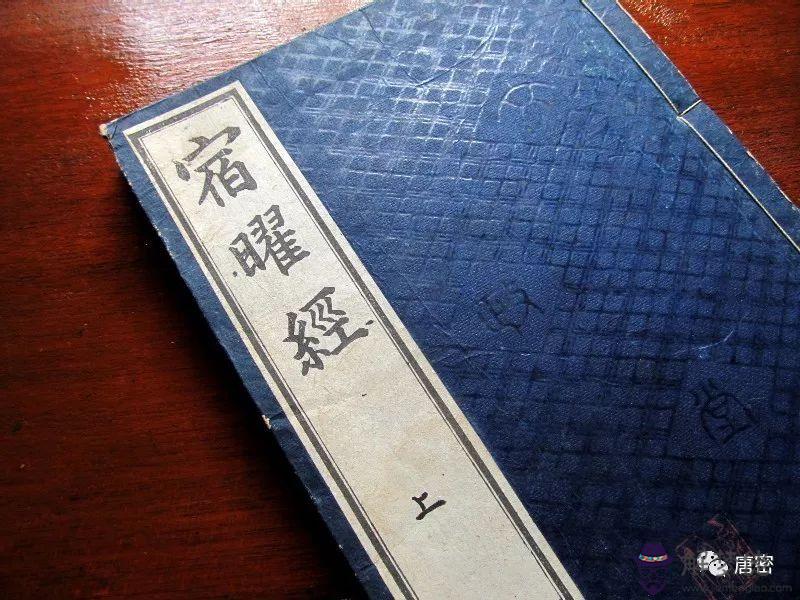
我忽然想起她上次的問題,于是我鼓起勇氣道,但是,糖有點太甜了,要是再淡一點兒……
她猛地回頭說,你再說一遍。
我重復道,糖太甜了。
我無法形容她那時的神情,卻好像透過我的眼,在看另一個人。
她問,糖太甜了,要加些什麼呢。
我搖搖頭。
她眼里的希望終于熄滅了,盡管我不知道她在期待些什麼。
人事跟著時間在轉,她的糖還是甜的,還是比我想象中多甜了一度。
她依舊時不時地給我塞糖吃,好像這是她表達情感的唯一方式。那群孩子見狀,再不敢找我什麼麻煩。
那日我出嫁了,她窮得叮當響一老太,卻不知哪里湊了錢,竟送了我一副金手鐲。
她硬塞在我懷里,像是第一次送我的那包麥芽糖那般沉重。
我驚道,寧老太,不用不用。
她只是硬氣地道,我當年沒結成婚,這副手鐲,我藏了四五十年,不送給你也是得跟我進墓里的。
旁邊的人都嫌聽了晦氣,我卻知道,她是真的愛我。
新郎挽著我的手,要帶我離開這個小鎮。我明知他那是個好人,卻不知怎的,有些舍不得這座小鎮。

它好在哪里呀。
它生我,卻不歡迎我;它養我,卻奪走我的至愛。
但或許是有寧老太偏甜的麥芽糖,有那不變的五味。
寧老太沒有再回頭看我,只身一人回了自己的作坊,我覺得她的身影更加瘦小了。
但也許,是我長大了。
很多年后,我和丈夫,帶著孩子回了這座鎮。
我見到了我的表弟和他的妻子,還有他們的孩子。
我還見到了當年欺負我的那群淘氣包,打頭的那個大聲笑道,他當年可是發誓要娶我的。
可我好像再也找不到寧老太。
我讓丈夫和孩子留在原地,然后只身一人去了她的作坊,那里空空如也,但似乎剛搬不久。
一個搬家的工人從里邊走出來,我連忙攔住他說,哎,大哥,請問一下,這里住著的人去哪里了?
死了,他冷冰冰地說,尸首都臭了,早兩天扔進河里了,不過這里倒是還有點晦氣的東西——
他指了指一個不大不小的木盒子。
我忍住自己的悲憤,對他說了聲謝謝。
盒子里有什麼呢?
不過是一疊亂糟糟的紙幣,幾個發簪,再加上一張相片罷了。
相片上是兩個女人,穿著旗袍,面容姣好。我端詳了一下,左邊那個大概是寧老太,因為眼角有顆好認的淚痣。
那麼右邊那位是誰呢?
我將相片翻了過來:
“寧和楠。”
我的手一抖,相框砸在地上,哐當一下,那位搬家工人又斜眼看向我。
切,兩個女人,惡心。他說道,活該被淹死。
我震驚地問,什麼。
他抬頭望天,我才注意道,他的年齡也很大了。他只是點了根煙,然后說,當年要拆散她們倆,那個叫楠的,被村里幾個人捆起來,手腕上死死地綁了根繩,接了塊大石頭,就丟進河里了。
我忽然想起我手臂上的胎記。
那麼多的好。
相框砸碎了,我看過去,里面掉出來一封封的信:
“嘿,楠。我把我的糖做甜一度,要是你回來了,趕緊罵我的糖太甜了,我好知道那是你。”
“你看,就好比水是淡的,鹽是咸的,而你是甜的。”
“我再也不奢求我幸福。可我想看那個小時候的你,想看你長大,想照顧你,想看你嫁人,要給你帶上金鐲子。”
“往后余生,我只要你幸福,好嗎。”
我不相信的事情太多了。我不相信轉生,不相信命,我有愛我的丈夫和孩子。
可那一刻,我似乎看到很多年前,有個穿著旗袍的女人,向我走來。
我笑著想,那是夢。
你說呀,寧。這世間,道不盡人生五味,共存相生。
物如此,事猶是,人亦然。
《五味》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6672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