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戴海斌
按:光緒七年(1881)三月二十九日,李鴻章因張佩綸之介,往拜京城張之洞宅邸,晤談餐敘,為目前有記錄之二人平生初見。同光之交,以二張(之洞、佩綸)為代表的“清流”人物,以“知洋務”自許,較諸實際從事洋務事業的李鴻章,視野非局限于因應現實需要的一艦一炮,而主張“用人”“經武”并重,規畫更加宏闊。究其知識來源,則又不出書生聞見。他們對待被外界奉為“清流領袖”的李鴻藻,多有“假借”和“挾持”之意,兩者關系近于“交而非黨”;與李鴻章反而多有互動,并非如晚清世論“以罵洋務為清流,以辦洋務為濁流”那般疆界分明。李鴻章籠絡“清流”的用心,張佩綸而外,在張之洞身上體現得最為深刻。不過,“清流”與“洋務”固有觀念交集,然終究“各有門面”,尤其對和戰問題存在根本分歧,最終清流亦以戰而敗亡。李鴻章與張之洞的這一段早期交往,也是二人在庚子年(1900)以“書生意氣”與“中堂習氣”互駁公案的前史。本文利用新刊《張佩綸家藏信札》《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等一手材料所做的回溯工作,旨在反思有關“洋務”“清流”的既有認知,為理解這一公案厘清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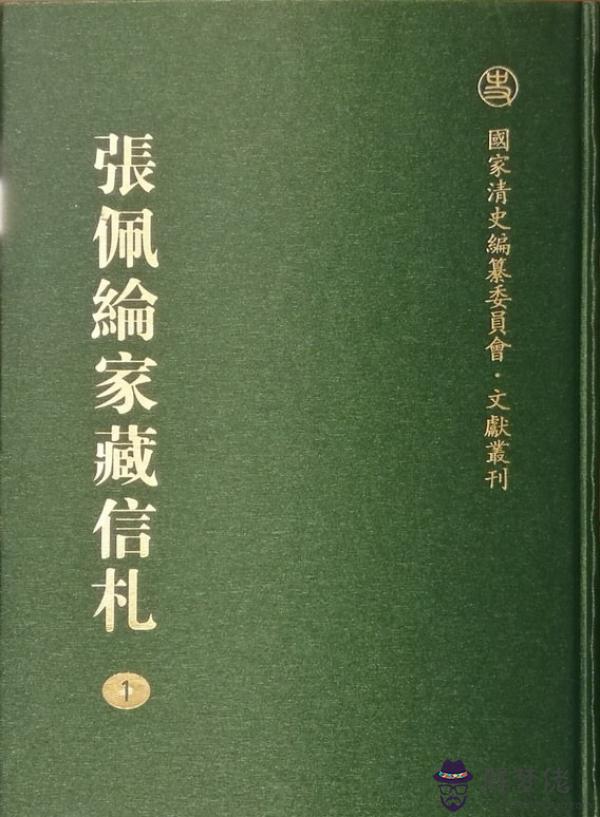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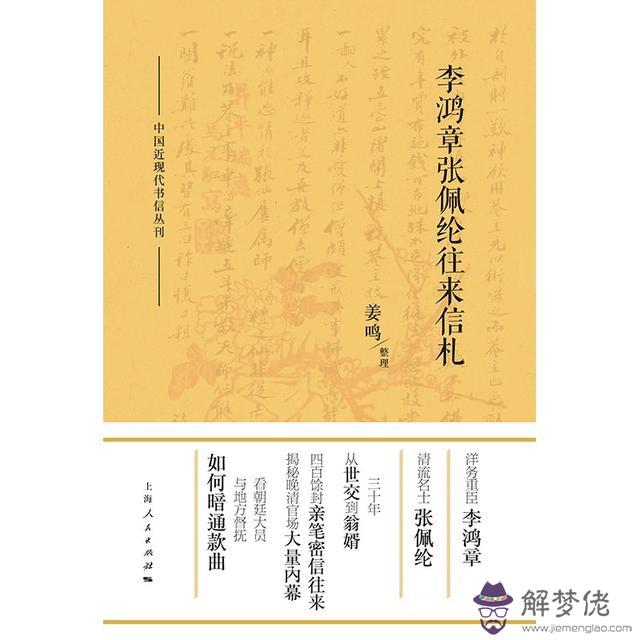
小引
光緒五年(1879)十一月二十一日,張佩綸過訪京師南城張之洞宅,同輯《畿輔先哲錄》,飯后清談:
論道光[以]來人才,當以陶文毅(澍)為第一。其源約分三派:講求吏治,考訂掌故,得之者在上則賀耦庚(長齡),在下則魏默深(源)諸子,而曾文正(國藩)集其成。綜名核實,堅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林則徐)、蔣礪堂(攸铦)相國,而琦善竊其緒以自矜。以天下為己任,包羅萬象,則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直湊單微,而陶(澍)實黃河之昆崘,大江之岷也。今左恪靖(宗棠)大功告成,而論才太刻,相度為宏,絕無傳衍衣缽者。閻丹初(敬銘)得其精而規模太狹,李少荃(鴻章)學其大而舉措未公,未知將來孰作嗣音也。(《澗于日記》)
二人縱論當世人才,皆趨經世/洋務一線,言下繼往開來,大有為之四顧,躊躇滿志之態。甚而當時已有“坐鎮北洋,遙執朝政”之勢的直隸總督李鴻章,竟也不在話下。陳寅恪嘗論“同光時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為少年科第,不諳地方實情及國際形勢,務為高論。由今觀之,其不當不實之處頗多”(《寒柳堂記夢未定稿(補)》)。石泉發揮師說,雖見及清流士大夫中“亦頗有留心外事,其見解較新者”,不過仍強調“與實際任事之人如李鴻章輩,則又常相水火,雖亦侈談洋務,而與實際之洋務工作,則無甚關聯”(《甲午戰爭前后之晚清政局》)。
為張之洞幕僚的辜鴻銘作過一段有關“儒臣”“大臣”的著名議論,認為同光清流“之所以不滿意李文忠者”,在于“其僅計及于政,而不計及于教”(《張文襄幕府紀聞》)。與李鴻章淮系更接近的劉體智,則觀察到張之洞“用人行政,惟以洋務為重,于李文忠,則亦步亦趨,尤極其揣摹之工”,清流之中“惟余南皮一人,如碩果僅存,銳意新政,實得文忠心傳” (《異辭錄》)。前者解釋清流何以“不滿”于李,尚有“教”“政”判分,后者干脆指認張之洞在“洋務”一端,實得李“心傳”,二說重心不同,然均提示“清流”與“洋務”并非實質上對立的關系。
庚子(1900)事變后,中外和議,身為“全權大臣”的李鴻章與在京外負“會辦”之責的張之洞意見不合,以致以“不料張督在外多年,稍有閱歷,仍是二十年前在京書生之習”與“合肥謂鄙人為書生習氣,誠然,但書生習氣似較勝于中堂習氣耳”相互譏嘲。晚清名臣間的口舌紛爭,演成近代史上知名掌故,也幾乎成為二人政治性格具體而微的象征。(此典故變體及評論甚夥,如辜鴻銘《張文襄幕府紀聞》、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凌霄一士隨筆》、瞿兌之《杶廬所聞錄》、梁啟超《李鴻章》《鄧之誠文史札記》、李伯元《南亭筆記》、《清朝野史大觀》等處,不贅述。)不過,回到二十年前,“中堂”與“書生”的關系,倒遠不至如此劍拔弩張,甚至有過一段堪稱“蜜月”的時光。利用二者相關文獻,結合近年新刊之《張佩綸家藏信札》《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等材料,可以鉤沉出李、張二人初晤一幕及其前后的歷史情境,從而反思“洋務”與“清流”關系的既有認知。
“二張”與李鴻藻關系再探
同治九年(1870)八月,為平息天津教案,李鴻章代替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由此開啟煊赫的廿五載督直生涯。同年,張之洞湖北學政任滿回京,寓南橫街,與潘祖蔭、王懿榮、吳大澂、陳寶琛諸人訂交,論列金石文字。翌年(1871),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十二年放四川鄉試副考官、四川學政,光緒三年(1877)返都,再充教習庶吉士冷差,至五年(1879)始補國子監司業。是時張之洞已屆不惑,而官運蹇滯,經濟拮據,其譜傳謂為“處境清約”,用張本人更直接的話說“詞曹清簡”,紀事之詩有道“高車蜀使歸來日,尚藉王家斗面香(余還都后,窘甚,生日蕭然無辦,夫人典一衣為置酒)”。約略同時,其治學與言論取向亦有一變,“自是究心時政,不復措意于考訂之學”。他與侍講學士張佩綸因穆宗升袝位次一折而“造廬訂交”,又與黃體芳、陳寶琛、吳可讀、何金壽、寶廷等人相互引援,隱奉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李鴻藻為魁首,倡為清議。
光緒五年(1879),張之洞開坊,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轉司經局洗馬。翌年(1880),晉右春坊右庶子,旋轉左庶子。七年(1881)二月,轉補翰林院侍講,六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二月外放山西巡撫。短短不到兩年,官階從正六品升到從二品,從翰院諫官一變為封疆大吏,可謂官符如火,節節高升。之所以如此,除去“簾眷”因素,也離不開李鴻藻的推挽之力。
關于“清流”與李鴻藻的關系,過去有些記載“過于夸張”。(樊百川已有揭示,見《清季的洋務新政》第一卷,頁467注1,本節予以申說。)《李鴻藻年譜》一則謂“張之洞、陳寶琛、張佩綸多以公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折,亦先得先生之同意”;再則謂“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等,皆公所領導‘清流’之健將,彼等一舉一動,皆與公事先議之”。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則敘及二者關系中“假借”和“挾持”之兩面:
吳江(沈桂芬)病逝,高陽(李鴻藻)柄政,意在延納清流,以樹羽翼。南皮張香濤閣學、豐潤張幼樵侍講、宗室寶竹坡學士、瑞安黃潄蘭侍讀均以清流自居,慕東漢士風,輒以平章國故,摩厲群僚為己任。文正(李鴻藻)一一延攬,假借講官之力,排斥異己。仁和(王文韶)竟不安其位而去。當時清流橫甚,文正亦為所挾持,聲望頓為之減。
以上“多以公馬首是瞻”“文正亦為所挾持”等語,實有分辨必要。光緒五年冬,中俄伊犁交涉事起,崇厚使俄辱命,主持總理衙門的沈桂芬袒護之,張之洞、陳寶琛等上疏力攻,學者高陽稱此為“南北之爭的又一回合”,“而幕后則有李鴻藻主持”(《同光大老·南北水火》)。六年,沈桂芬病卒。按《李鴻藻年譜》的說法,“沈與公為中樞兩大勢力,沈卒后公勢大增”。此實“清流”風頭最勁、風光最盛的時期。張之洞致李鴻藻密函甚夥,多錄入《李鴻藻年譜》,其中一函“本應閱后即毀,故多暗語,亦無日期”,考其事實,當作于光緒六年,文如下:
總之,吳江(沈桂芬)昏謬私曲,既無公事之法,又不實修戰備,調將帥,籌將帥軍火,籌借餉,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敗壞而后已,輔之以嘉定(廖壽恒)、常熟(翁同龢),禍不可言,事不可為矣。某苦口言之,欲公燭悟其奸耳。……丙。
函內斥沈“昏謬私曲”,可與張佩綸同時私信中“吳江謬見”“吳江陰狠”“吳江病在全用小人”“吳江入柄大權,為陽極陰生之象”“吳江勢焰愈張,中國危端立至”諸語并看。李鴻藻一系集矢于沈桂芬,兼惡廖壽恒、翁同龢,情勢豁然。但細繹“公此時必不信,他日當知”一語,則李鴻藻的派系斗爭觀念并不強,只是其門下媒蘗之。
李鴻章屢說李鴻藻“才短口訥”“才具太短”,張佩綸對友人坦白相告:“高陽秉政,遇事虛心諮訪,略得藉手,而處事遲回寡斷,論人博采旁搜,亦有千慮之失”(《澗于集·致顧暤民觀察》)。這句話實有兩層意思:李鴻藻身處政壇高位,而能“虛心咨訪”張佩綸在內的清議諸人,使“略得藉手”,從而推行主張;但究其實際,無論“處事” “論人”,都不愜人意,所謂“遲回寡斷”,即繼承沈桂芬輩“應付之法”,二張在沈去世后所抱“但愿群工協力,破沈相十年因循瞻徇之習,方可強我中國”的希望無疑落空了。
與清流關系勢同水火的李慈銘在日記中痛斥“二張(佩綸、之洞)一李(鴻藻),內外倡和,張則挾李以為重,李則餌張以為用,窺探朝旨,廣結黨援”(《越縵堂日記》光緒八年五月初八日條),可與前引陳夔龍“清流橫甚,文正亦為所挾持”一語相互發明。清流諸人與李鴻藻實乃互為利用,所謂“挾持”“挾以為重”之語,正說明清流自有宗旨,并非只為李代言,二者因緣際會,一度聚合,甚至有“黨援”跡象,不過落實在政治層面,合作并不投契。究其結果,“清流”未必能行其志,而李鴻藻亦“聲望頓為之減”。故而,后來進入總理衙門的張佩綸遂有“土人之勸木梗人”之嘆,據其自況之言,與李鴻藻的關系實乃“交而非黨”。
清流人物之“洋務”見解并其來源
光緒五、六年之交,張之洞就中俄伊犁交涉連上折片,發言激切。初上《熟權俄約利害折》內稱崇厚所訂條約“不可許者十”,“可改議者四”,要求“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又詰責北洋大臣李鴻章“高勛重寄,歲靡數百萬金錢,以制機器而養淮軍,正為今日,若并不能一戰,安用重臣?”此后多次條陳海防事宜,并建議“促令左宗棠迅速來京,籌畫戎機”。
身處北洋的李鴻章,對京中“清議”向來敏感,尤以“南城士大夫每謂弟辦夷務過軟”耿耿于懷。中俄交惡后,條陳軍事者眾多,李鴻章面對“言路龐雜,風波迭起”,以為多局外談兵,致函友人,對主戰派大發牢騷:
俄事之壞,自去臘寶(廷)、張(之洞)諸君慷慨陳言而起,直至今日,節節貽誤,仍日進讜論。其源自左相發之,亦實由政府導之,而自詒伊戚也。……因寶、張之請,商調左相入都,謂可以主戰嚇俄,豈知俄人藐視太沖(左宗棠)已久?……清議之禍與明季如出一轍,果孰為之耶?(《復周福陔中丞》)
李鴻章深惡“清議”,誠事實之一面,但出于“憂讒畏譏”,又不惜以利祿籠絡,亦不容諱。當時尤注意接納張佩綸、吳大澂等人,已為先行研究所證實(參見姜鳴《張佩綸與李鴻章的關系》、張曉川《〈李鴻章全集〉所載吳大澂書信系年考證及勘誤》)。光緒六年(1880)初,他有專函論及清流諸君之出處歸宿:
近日廷臣中,如二張(佩綸、之洞)、黃(體芳)、寶(廷)諸君,皆鯁直敢言,雅負時望,然閱歷太少,自命太高,局外執人長短,與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騖虛名而鮮實際。尊意能使在外歷練,所成當未可限量,實為當今儲才切要之圖。惟此中機括,不在疆吏而在朝廷。……倘朝廷欲陶鑄人才,不妨使諸君出而揚歷,始計資格而授以司道,繼課成績而任以封圻,似亦實事求是之一法。張幼樵已奉諱在籍,敝處現訂于三月間來幕襄助,亦冀其練習時事,他日可不僅托之空言。(《復徐鑄庵部郎》)
李鴻章以為清流人物病在“閱歷太少,自命太高”,相應的“陶鑄”辦法是“出而揚歷”,即放諸地方歷練實務,雖然婉轉表示決定者“不在疆吏而在朝廷”,但身為北洋大吏,為國“儲才”、講求“實事求是”,終歸是題中之義了。當時正值李鴻藻守制期滿重歸軍機、總署之際,李鴻章急于向李鴻藻系清流釋放善意,張佩綸入幕,恰逢其時。
同年二月,張佩綸自京赴津,將入李鴻章幕府,張之洞為之送行,謂“君之才氣,一時無兩,但閱歷尚淺,遇事可加一番講求,加一番思索,然后出口,則完全無弊矣”,聲口語氣與前引李鴻章函逼肖;又諄囑“此行可至太沽、北塘各海一覽形勢,蚊子船、碰船式樣亦宜留意”,表現出對海防洋務的關心(《澗于日記》)。
光緒三年入都后,張之洞于“時政”更為究心,他與張佩綸、陳寶琛“分考史事切于實用者”,擬輯為《皇朝經世文續編》,便很能體現其“高談經世”的趨向。光緒五年,他就俄事奏陳籌兵、籌約之策,蒙慈禧太后嘉許,以詹事府洗馬奉諭“隨時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備諮詢”。張之洞在《詳籌邊計折》中對歷年來清廷之“洋務”實踐有所反思:
竊念自咸豐以來,無年不辦洋務,無日不講自強,因洋務而進用者數百人,因洋務而靡耗者數千萬……事閱三朝,積弱如故。一有俄事,從違莫決,縉紳束手,將帥變色,即號憂國、持高論者,亦徒吁嗟嘆太息,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泄泄悠悠,委其憂于君父,今猶中興時也,不知十余年后又將何以處之?
張之洞出入總署,侃侃論列,儼然以“知洋務”自許,一時間也以此“負盛名”。他自覺區別于那些“號憂國、持高論”的守舊派,并不固拒西法,虛聲言戰,而提出“急修武備”,仿效西法,購造新式武器,指出:“戰必資火器,守必藉炮臺,防海必須戰艦。而土槍土炮,萬不如洋槍洋炮;舊式炮臺,萬不足以資捍御;木質兵船,萬不如西式裹鐵諸兵船”(《請修政弭災折》);“兵無利器,豈能徒手搏戰?李鴻章津防緊要,豈能供眾人之取求。若姑以各省舊存鈍朽土槍、土炮充用,亦非致勝之策。惟有立發數十萬金,飭南北洋大臣向上海洋行迅速購買各種精巧后膛洋炮、洋槍”(《條陳防務片》)。后來出任山西巡撫,見晉地軍械簡陋不堪,也函告張佩綸:“此間軍裝局直同兒戲,所存有狼牙棒、月牙鏟、三股叉之類,全是戲劇,辦軍需二十年,糜費千馀萬,而其械如此,可恨!可惜!”黃濬評論此札“可見光緒初軍備窳弛,官吏侵吞之狀”,而對作者頗加揄揚:“南皮于此等處,視昔之紅燈照卻槍,今之大刀隊勝敵者,其智識自迥不同也。”(《花隨人圣庵摭憶》“張南皮集外書札節錄”條)
不過,以翰林講官談洋務、經濟之學,立論常逞臆想,“侃侃論列”終覺不倫。茲舉兩例,光緒五年張之洞上《詳籌邊計折》,在檢討咸豐以來“洋務”“自強”不足恃的同時,建議“責以義”“折以約”“怵以勢”,阻止沙俄侵吞我疆土,如不成功,則“出下策,擲孤注”,以西藏阿里地區賜英,以臺灣賜日,換取兩國出兵,夾擊沙俄,解決邊患。此說連張佩綸也看不下去,私信中批評“游詞之說,非縱橫之策,時人誤以煙云為堆垛耳”(《致容舫安圃侄》)。
同一折中,張之洞又謂“李鴻章新購蚊子船,頗稱便利”,建議北洋盡量多購新式“蚊炮船”。可惜,他在此時的艦船知識并未絲毫領先于李鴻章,對蚊炮船與鐵甲艦的功用短長、性能優劣一無所知,及發現北洋所購蚊船全不合用,一變為贊成購買鐵甲艦,又想當然地表示:“戰艦以多為貴,蟁(蚊)船既不可恃,鐵船不必阻止,勿購廢壞者而已!……中國今日人材物力,海防易,海戰難,控大連灣旅順是海戰也。戰倭易,戰俄難,兩鐵船僅足備倭耳。”石泉評論同光清流“所講求之洋務,大都著眼于國際情勢之縱橫捭闔,而不甚注意于人我國力之實況,與夫增進中國國力之實際辦法”,于此可得印證(《甲午戰爭前后之晚清政局》)。張之洞的洋務見解雖然“頗動視聽”,與實際之洋務工作確有不小的距離。
若深究這些“新進少年”的知識來源,多數不出書生聞見。張之洞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講求西域畿輔水利、厘金、東三省等“考今不考古之事”,“惟在稽諸近日奏牘,或訪之故吏老兵”。此外,或讀過《海國圖志》以及江南制造局譯介出版的少量西書,借此略窺“西政”“西學”概貌。如光緒六年奏請頒發《防海新論》一書,內謂:“近年西人著有《防海新論》一書,經上海道譯出,刊板通行,于外洋爭戰,防外海、防內河,種種得失利鈍,辯論至詳,京師洋書肆現有其書,擬請先購數十部發交東三省,一面令沿海各督撫向上海多購,分發諸將領,細心講求,觸類引申,必有實效。”(《謹陳海防事宜折》)
據說陳寶琛“曾借譯署歷年檔案”,屬人“分手抄之”,從而研究洋務,得習故事(何剛德《春明夢錄》)。張佩綸自稱早年“常肆力為經濟之學”,實際亦不外讀書、考古兩途,尤其重視讀史,以為“經濟之學,讀官書尤須讀史傳”(《花隨人圣盦摭憶》“張南皮集外書札節錄”條)。當然,還有較特別一點,他與李鴻章“累世通家”,有“父執”之誼,故有機會被邀往北洋佐治軍務,“因得周覽北洋險要,討究水陸戰守之略”。他的許多洋務見識,說是從李處偷師學來,亦不為過。樊百川便注意到“張佩綸在1879年以前所上的奏折,雖然也有二三篇談論洋務的,但皆簡略,沒有什麼獨特見解。此后從1881年起復,在1882-1884年兩年多時間內,談論洋務的奏折、書札不下一百篇,其所提出的許多獨特見解,自與在北洋佐軍有關”(《清季的洋務新政》第一卷,頁473注4)。
入李鴻章幕府后,張佩綸有意為“清議”正名,兼為自己爭地位:
眾論群言,在曾侯目之曰“書生”,鄙之曰“酸子”,而佩綸略涉曾文正之書,則故尊之曰“清議”。吾師偉略忠忱,故清流爭附,而吾師平日言論亦甚愛護清流,惟前月十六夕談,乃頗有非笑之意,此實吾師之微失,佩綸亦不敢為諱也。
此函委婉承認洋務派對“清流”不屑、不滿,乃至“非笑”,但仍表彰清流“爭附”李鴻章的事實,奉承李為“愛護清流”之人,心態相當糾結。無獨有偶,張之洞對外間視清流為“書生之見”、“不曉洋務”也格外敏感,伊犁交涉時期在總署“備諮詢”,援引曾、左故事為前例,亟亟為己背書:“縱樞臣以臣為書生之見,獨不思左宗棠曾連篇累牘而上陳乎?縱使臣(指曾紀澤——引者按)以臣為不曉洋務,獨不思其曾國藩固嘗腐心切齒而力爭乎?”(《議約期迫請籌挽回折》)
在張佩綸自我認知中,其“洋務”理解,能夠貫通中西,超越畛域,要遠高于一般辦洋務者。他說:“近日不明洋務者固執不通,而所謂[明]洋務者,亦是固執不通(但知洋理,不知中國之理,在彼以為大通,而自鄙人觀之,正是固執不通也)。”(《復奎樂山中丞》)張之洞也有過類似大話,所謂“立身立朝之道,無臺無閣(執政皆閣之屬,言路皆臺之屬),無湘無淮,無和無戰……中立而不倚,論卑而易行,當病而止,而不為大過”(《致潘伯寅》),要旨在于處事圓融、通透,實發出了后來《勸學篇》標榜表里、本末,講究“會通”的先聲。
李鴻章與張之洞的初晤及政治互動
光緒六年(1880)五月,張之洞就俄事上陳二策,一曰“守正”,即嚴懲崇厚,二曰“變通”,即“欲釋崇厚,則必將南北洋大臣立加嚴譴”,抨擊李鴻章、劉坤一“身為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戰而以解君父之憂,但恃曲赦以為僥幸”(《敬陳經權二策折》)。然而未到半年,張之洞與李鴻章的關系即見緩和跡象。察其原因,一則李鴻章簾眷尤隆,攻之不智。二則身處李幕的張佩綸在協調北洋與清流關系方面出力甚大。當年下半年,張之洞致函稱:
得天津發書甚慰。合肥事,以求杰士、汰宵人為第一義。……尊論洞達,朝夕贊畫,宏益必多。……合北洋三口之稅以養水師,沿海屯防,自是勝算,能力贊之否?(《花隨人圣盦摭憶》“張南皮集外書札節錄”條)
函中呼應張佩綸之言,對“合肥”近論已表贊和。七月,崇厚“蒙曲赦”,張之洞“憤懣”之余,不得不改變策略,建議重用淮軍宿將備戰俄事,列首位者即劉銘傳,請“責令速起赴津,會同李鴻章辦理防務”(《謹陳海防事宜折》)。十月,迎合慈禧,奏請崇厚“戴罪立功”,劉銘傳“亟宜促召北來”,李鴻章“節制北洋三口防務,責令通籌方略”,折內評價李鴻章語氣較前一變,謂“該大學士究系更事重臣,精力猶壯,儻專其責,當可力圖御侮,固勝于今日之散渙推諉者遠矣”(《請飭李鴻章節制防務片》)。
在伊犁、琉球交涉案件中,張之洞原主聯日拒俄。十月,上《日本商務可允球案宜緩折》,對前說作出重大修正,轉將“商務”與“琉案”作分割處理。這一擱置琉球問題的立場,實出于張佩綸等人提示。同月,李鴻章上《妥籌球案折》,奏請“日本議結球案,牽涉改約,暫宜緩允”。結果,俄事展限兩月,琉案暫允日本改內地通商之約,分琉球南島與中國。
無論如何,在琉球問題上,清流、北洋竟然合作,迫總署就范,這是一個新的局面。張佩綸事后稱:“會譯署與倭定約,結中山案,倭以南島歸我,我許其內地通商。潛(陳寶琛)、達(張之洞)均上言極論,合肥(李鴻章)亦龂龂稱其不便,要津頗疑弟從中主持,可謂不虞之譽。”(《致顧暤民觀察》)自詡之情溢于言表。經此一役,李鴻章與張之洞的距離亦迅速拉近。
光緒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慈安皇太后猝崩。李鴻章自津啟程,叩謁梓宮,張佩綸隨行,二十三日到京。這段時期,可謂李鴻章與清流之蜜月期。三月二十八日,張佩綸向幕主進言“香濤忠誠博懿,十倍于佩綸,深愿公延清傾談也”。李鴻章樂從其請,復函表示:
手示敬悉。前專程往拜香翁,未值為悵。茲承訂于廿九辰巳間枉顧,屆時當撥冗祗候。相距過遠,便留午飯,一傾積愫,乞代尊意。(以下數段引文均見《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
在京期間,李鴻章專程往訪張之洞,未遇,故張佩綸再為約定本月二十九日張之洞回拜,并留餐敘,此為二人平生初見。
李鴻章原擬于四月初二日陛辭,因張之洞、寶廷奏請,奉懿旨留京數日,“與樞垣籌商洋務”,至十三日始離京。其時,李鴻章籠絡“清流”的用心,在張之洞身上體現得最為深刻。本年六月,張由翰林院講學遷升內閣學士,李即請張佩綸致意,“香翁超擢閣學,賢才登進,極可慶幸,晤時乞先道賀”。然而,張佩綸意猶不足,暗示“孝達超授閣學,但清而不要,亦未能稍有展布”。至光緒七年下半年,李鴻章函稱:
洋務如做理題文字,有不容操切凌躐者,錯在昔日,非在今日,威德何自而施,愿吾賢更加究心耳。周公于閣下似尚心許,非外人所能譖毀,然其褊衷抑何可嘆。宜興復值南班,方冀南皮匯進,或有沮格之者。
按“周公”,指恭親王奕䜣;“宜興”,周家楣,江蘇宜興人,總署大臣,五年丁憂,七年十月再入值。“方冀南皮匯進”,意在希望張之洞亦入總署辦事,可見政治上已視張為同黨,惟恐有人“沮格”。
光緒七年十一月,張之洞外放山西巡撫。李鴻章聞信,第一時間函詢:“香翁先以晉試手,漸調東南亦佳。聞小恙未愈,何時出都?念念”。在張佩綸看來,“香濤出撫山西,晉亦仕國,但今日卻非要地。公所論當事力不能辦,知其無志于天下。按張之洞任晉撫出于李鴻藻所保,此處“當事”,當指李鴻藻而言。但張佩綸對此人事安排不滿,并以為張之洞必不能如李鴻章所愿調任“東南”,此皆由于李鴻藻之“無志于天下”,他為此抱怨:
南皮之事,高陽先不謂然。以洋務得名,而置之無洋務之省分。論用才,可謂捉蟾蜍而使捕鼠;論為己,可謂翦六翮而欲傅天;論謀國,可謂縱騏黃于牧而策駑駘也。
十二月,張之洞出都赴任。李鴻章函詢“香翁十二日果否出京?屬抄各件容即面交”。按“屬抄各件”,實由張之洞之請求狀而來。據張佩綸函稟:“孝達撫部一函屬為專呈。渠一切求教,并欲祈洋槍隊章程,懇公處借洋教習兩人,望與前輩并垂察也。”張之洞履任之際,已未雨綢繆,就制訂章程、購運機器、聘洋教習等節,向“洋務”前輩取經。李鴻章積極回應,提供檔冊抄本,同時也提示晉地“洋務”存在的現實困難,“晉處萬山之中,機器笨重,似難運入,其章程隨時隨地核實為之,原無定格外”。(張之洞真正著手西式武器與訓練,采礦冶煉、興修鐵路等事宜,實現所謂“洋務轉向”,尚待西人麥士尼(Mesny)、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啟蒙”,及在廣東受何獻墀、鄭觀應等人熏陶,此是后話,參看陳曉平《麥士尼與張之洞的洋務轉向》)。
十二月十四日,張之洞到保定,晤李鴻章,“勾留暢談”,十六日辭行赴山西。除切磋“洋務”外,二人所談多關政事。十九日,李鴻章函告張佩綸:“香翁密商叔度(閻敬銘)出山,頃擬密片再薦,明日拜發。鄙言未足增重,吾宗(李鴻藻)力量能之否?”二十五日再函:“叔度品詣、學識在同輩中不可多得,昨因南皮商催密疏上陳……高陽(李鴻藻)素以扶植正氣為心,諒能設法推挽。”張之洞離京時,已與李鴻章密商中樞人選,事后上疏奏薦,自然屬于有的放矢。(參見張之洞《閻敬銘定期赴闕折》。按張之洞與閻敬銘有交,且多書函往還,徐一士嘗言“張之洞素推服敬銘”而“勸出山”,并論及張督鄂時期與前后總管的戶部閻敬銘、翁同龢之三角關系,見《凌霄一士隨筆》“閻敬銘張之洞與翁同龢”條。張、閻之歷史淵緣,尚多追索、發覆的空間。)
當時張佩綸對樞、譯大臣,也多不滿,以為“宜興(周家楣)復入譯署,與荊公(王文韶)比周,恐外務更將廢弛”“瞻徇、顢頇、驕蹇種種習氣全有”。外間視為“清流領袖”的李鴻藻,在他眼里“才不逮志”“無遠謀”,實屬差強人意。
張之洞入晉后,也有向隅之感,眼前棘手者為“晉省事可辦者頗多,惟同志無人”,心中不愜意者實“僻在一隅,大事都不聞知”,故向張佩綸示意:“如蒙朝命,洋務亦許與聞,下采芻蕘,則當抒其管蠡,不致后時發議,徒為不切題之文章也”(《致張幼樵》)。
張佩綸不但答應張之洞“外事自請與聞”,并有與之同進退之意:
……以公為帥,而佩綸如驂從靳,未始不收駑馬十駕之益,不然亦絆驥馬而求致千里也。近蘭相(李鴻藻)力任此事,而義興(周家楣)治賓客,軍旅不問,商政不問。合肥(李鴻章)書至,焦急萬端。他日遲回展轉,終出于召,而不兼兩府,安足有為?元祐調停之政,豈柄不專哉?司馬公有喜蔡京、惡東坡之一念致之耳。(《復張孝達中丞》)
按照張佩綸設想,由李鴻藻出力,設法將他與張之洞雙雙召入總署,而且最好同入軍機,如此身兼“兩府”,專執政柄,才能“有為”,不復蹈北宋元祐黨人調停新舊黨爭失敗之覆轍。
光緒八年(1882),云南報銷案發,張佩綸奏劾王文韶,提議由張之洞、閻敬銘為替人,直言:“文韶之才,皆以譯署推之,其所承者,沈桂芬應付之法耳。以言商務,則綜核不如閻敬銘;以言防務,則操縱不如張之洞也”;更明白指出“修內攘外,要在樞廷、譯署,若兩府之地,或有僉壬,則臣下修攘之策,固未必行”(《再請罷斥樞臣王文韶折》)。至此,其安排軍機處、總理衙門人事布局,謀求實掌朝權之政治意圖已曝露無遺。
然而,事與愿違,張佩綸推舉張之洞、閻敬銘均以“洋務”立言,李鴻藻卻“不以二公為是”,后來恭王奕䜣、醇王奕譞舉薦工部尚書翁同龢、刑部尚書潘祖蔭為軍機大臣,且均不兼總署差使,張抱怨“舍頗、牧而用文學侍從之臣,在圣明初無成見,決策由懿親貴近,言者將如之何!此事不得不歸過于高陽矣”(《復黃漱蘭侍郎》),可見對于李鴻藻怨懟之深。舊說多謂攻倒王文韶,為清流派排除政治異己的空前勝利,但就所得而言,卻相距初望甚遠。
“清流”“洋務”終究“各有門面”
光緒九年(1883)底,張佩綸受命以署左副都御史充總署大臣,但深惡“譯署事事遷就,人人疲玩,殆難自立”,行事已感力不從心。
光緒十年(1884)三月,慈禧太后一諭推翻以恭親王奕䜣為首的全班軍機大臣,命禮親王世鐸、額勒和布、閻敬銘、張之萬、孫毓汶入值軍機,并啟用醇親王奕譞參與政務,慶郡王奕劻管理總理衙門。“甲申易樞”猝發,朝局為之翻覆,此事緣起于盛昱彈劾張佩綸,波及奕䜣、李鴻藻,惟張事后“獨中流容與”,圣眷未受影響。姜鳴注意到“這是整個事件的吊詭之處”,并論及張佩綸從反對“樞(軍機)、譯(總署)分置”的思路出發,謀劃挽回局面的嘗試。(《“甲申易樞”與政局大變動》)張佩綸一面抱“內隙可弭”的一線希望,“涕泣一陳,冀回天聽”,一面致函李鴻章,仍圖有所補救:
時事如此,果得賢才輔世,誠宜舍舊謀新。奈丹老(閻敬銘)于洋務隔膜,于治理苛碎,斷非救時宰相。香濤(張之洞)召入,聞將屬以譯署,若鄙人所請不行,謹當拜手稽首,讓于夔龍耳。興獻(奕譞)既欲轉圜,劻(奕劻)、禮(世鐸)亦愿調處,公能以重臣出片言相助否?
張佩綸不僅努力保全恭王,且猶作“舍舊謀新”之圖,希望因中法戰事內召的張之洞能入主總署,合力“救時”。而后者適時地保持了沉默。
中法戰爭之際,李鴻章以“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為由,堅持“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張佩綸則針鋒相對地批評:“言和之害與戰敗之害正同,而戰敗猶有不敗之道在也”“為國家長久之計,疆宇遠大之謀,正不如奇,守不如戰。”雖與李鴻章關系密邇,但不諱言“合肥怯敵”“肅毅慎葸”“合肥過于慎重,將涉畏葸”。
張之洞由翰苑清流一變為地方大吏,議政立場自然有所轉移,但“主戰”思維仍然一貫,屢言:“法事即決裂,亦復何妨?橫逆太甚,一味容忍,何所底止?”“鄙人則明知法強華弱,初戰不能不敗。特非戰不能練海防,不敗不能練戰。只要志定氣壯,數敗之后,自然漸知致勝之方。”(《致張幼樵》)
光緒十年(1884)春,李鴻章為接受法方條件,對朝中清議深致不滿,張佩綸面對“主和一線到底”的“師相”,坦承“有主戰堅持之語”,戲言為其“損友”。尤值玩味的是,他有關“清流”立場的一番辯白:
鄙人昨請丹老(閻敬銘)代奏,云張某之論,言路主戰者多,轉于和局有益,愿朝廷不以異議為嫌。(今日又言之興獻[奕譞],作清流須清到底,猶公之談洋務,各有門面也。一笑。)……至鄙人來津議和,斷不遵命(寧死,斷不附和和議),幸公勿為此言。
“清流”“洋務”,在張佩綸看來不過是對外門面語,而非政治歸屬或學術取向的實質,但既然是“門面”,就必須貫徹到底,不能動搖。二者觀念不乏交集,但于和戰大端仍存根本分歧,而最終結果,清流亦以戰而敗亡。甲申(1884)四月,張佩綸奉旨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南下福州,在前線作“屯馬尾、護船局”之計,而只“香濤以兩船及五營來援”,由是慨嘆“沿海各督撫舍香老外,無一有天良者,將奈之何!吾不憂敵而憂政也”(《致安圃侄》)。以后視眼光來看,此時“清流派”風流云散的命運將臨,而二張終究堅持“門面”到了最后一刻,也算得其所哉。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徐亦嘉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6360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