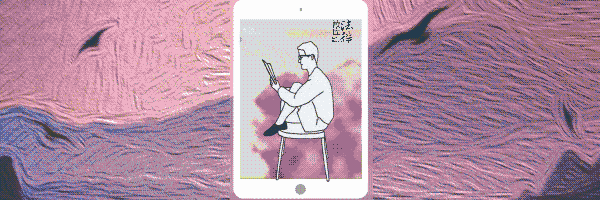
撰文/麗鹿
春節將近,表姑家的兒子毛蛋,開著面包車,從靈寶來三門峽進貨。
他搬了一箱冰糖桔,放到客廳里,然后到我屋里,動手把那張舊床和沙發拆走,拉回他家用。

毛蛋以販賣水果養家糊口,才三十多歲,看起來很顯老,背也有點微駝。
我問他生意咋樣,他說不賴,上個月掙了八千多。
我又問他有女朋友沒,他說有了,我問啥時候結婚,他說不知道,得看那女的啥時候能離婚。
我暈,這算哪門子女朋友啊。
說起毛蛋的婚事,還得從他媽說起。

表姑在山里算是個知識分子,她讀完初中后,又到縣衛校進修半年,回村成了一名赤腳醫生。
上世紀七十年代,身材健壯、潑辣要強、梳著兩條烏黑大辮子的表姑,斜挎著一個畫有紅十字的藥箱,走在山道上,常被頑皮的小孩們,追著喊《朝陽溝》里的“銀環同志”。
八十年代初,表姑嫁到鄰村后,當了婦聯主任,表姑父從部隊復員回鄉務農,他性情和順,表姑當家作主。
表姑相信人多力量大,接連生了三個兒子。因為超生,村干部的職務也被免了,表姑父也被拉到鎮上做了絕育手術。但她仍不滿足,又從外村抱養了個小女兒。
家里地里忙得團團轉的表姑,對孩子們疏于教育管理,連名字都懶得用心取,只是毛蛋、二蛋、三兒、妮子順嘴叫。
老大毛蛋小時候過年放炮,崩壞了一只眼,高中畢業后當不了兵,只好到縣城工地上打工。二蛋參軍退伍后,到鄭州給戰友開大貨車。三兒自幼頑劣,誰的話也不聽,高中沒讀完就輟學了,在縣城網吧里打工。
孩子們還小的時候,表姑說話總是口滿氣盛,底氣就來自她有三個兒子。她常說:“娃子多,不受氣,誰敢欺負俺,打架不怕他。”
我家姑娘小的時候,表姑每次見我,都皺眉搖頭地替我擔憂:“這可怎麼行啊,閨女不算人,以后嫁出去都是外人,你到老了指望誰?無論如何得有個兒子。國家不讓生,你們就不會偷偷生?要是不想生,我從山里給你們抱一個。”
因為超生,表姑家被罰得家徒四壁。喂的牛羊豬雞都被牽走不說,就連房頂上的瓦,都被揭掉好幾溜。

毛蛋該娶媳婦了,媒人來家看看直撇嘴,說誰家愿意把閨女往窮坑里送。表姑整天急得上火牙疼。
27歲那年,毛蛋終于娶上了媳婦,女孩叫小菊,住在比表姑家更偏遠的山里,因幼年生病沒能及時治療、落了個智力低下的后遺癥。
二蛋跑車時認識了外縣一位女孩子,給人家做了上門女婿,三兒到現在還沒成家。
毛蛋好不容易結了婚,卻在幾年后又成了光棍。
小菊剛進門,表姑指望她的肚子當奶奶,待她還不錯。
小菊做飯洗衣啥都不會干,每天就是傻呆呆坐屋里看電視,看看笑笑,嘴里自言自語念念叨叨。過了兩年,她生了個健康的男孩大乖。
表姑很疼大乖,除了叫小菊喂孩子吃奶,不讓她碰大乖一下,怕她不會照顧,把大乖給磕著碰著了。
小菊雖癡呆,天性里也有母愛,她很想抱自己的孩子,就趁表姑去做飯或忙別的事時,把大乖抱在懷里,使勁摟住,孩子感覺不舒服哇哇大哭,表姑聽見了跑過來,免不了把小菊打罵一通,說她只知道吃飯睡覺,啥活也不會,養她還不如養頭豬。
小菊挨了打罵,像個孩子一樣扯著嗓子咧著嘴大哭,毛蛋有時候在家,被她哭得心焦,不但不安慰她,也隨著表姑罵她。
大乖該上學了,毛蛋在縣城租了房,讓表姑帶著大乖、小菊住到城里,表姑父在家種地。
大乖上了學后,毛蛋繼續在建筑工地上打工,表姑拉個板車在學校門口賣水果,小菊在家閑著沒事,總往外面跑,每跑丟一次,毛蛋都得到處去找她,一找她就干不成活,干不成活就沒有錢掙。
所以每次找回來后,毛蛋都又氣又恨,把小菊給打一頓,越打越跑,有一次小菊挨打,邊跑邊扭頭看后邊追她的毛蛋,結果被路上的車給撞死了。
毛蛋拿車主賠的十幾萬塊錢,買了套房子,算是在縣城落住了戶。后來他在建筑工地上干了一年活,年底老板卻跑路了,工資一分沒拿到手,只好跟表姑一起賣水果,起早貪黑地干,掙了點錢又買了輛二手面包車,從三門峽批發進貨,拉回靈寶販賣。
毛蛋賣水果時,認識了經常買他東西的花朵,花朵家也是山里的,前幾年跟著老公出來打工,兩個小兒子和大乖在一個學校讀書,后來花朵老公跟著老板去南方工地了,家里就剩下她和孩子。
毛蛋對我們說的女朋友,就是花朵。
我問毛蛋:“她老公知道不?”
“聽花朵說他在南方和一個四川女的住在一起,也不往家里寄錢,我每月掙錢給花朵兩千。”
我開導毛蛋:“你咋真憨呢,花朵是別人的老婆,況且還帶著兩個孩子。”
“我不嫌她帶著孩子,我好好掙錢,能養活她們。再說,離開花朵,誰愿意跟我啊。”
“花朵要是愿意跟你,就催她去辦離婚手續,你們好名正言順在一起。不然等她老公回來了,會依你?別弄到最后,你竹籃打水一場空。”
“催過她。可花朵說她老公回來時,她一提離婚,老公就打她,死活不離。姐,你們在大城市,講究多,你到山里看看,這種事可多,有的男人好幾個媳婦,有的女人好幾個男的,現在俺和花朵過一天說一天,想不了恁多恁長遠。”
我剛想再說點啥,聽見毛蛋又說:“放心吧姐,俺媽前一段還找人給我算卦了,那算命仙兒說我這一回找的女朋友一準能成,他說我找的媳婦,家也在山里,從俺家出門,上個坡兒,下個坡兒,拐個彎兒,磨個角兒,大槐樹下第一家兒,姓李家有倆小哥兒。俺媽回來一說,花朵說算命說的就是她家。俺媽又跑去找那人,說花朵是有家的人,離不成婚咋辦,算命仙兒給俺媽說了個破法兒,讓俺媽扎一頭紙馬、一個紙人,和俺舅一起去后山上燒燒,過個半年一年,俺的婚事準成。”
我聽了不再吭聲。我既然幫不了毛蛋太多,也就覺得沒資格指手畫腳對他說教些什麼。
在這個充斥著喧嘩與騷動的世間,我早已經放棄對別人講些連我自己都難以被說服的道理。我只能如實記錄下,我所看到和聽見的那些不安和無序。倘若不是毛蛋就在我身邊,我真難以相信,城市里還有這樣一個八零后男人,面臨著如此困境和壓力。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6298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