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 孫周興
內容提要: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在他的哲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相關迷思可能是20世紀最艱深的一種。本文試圖從幾個方面探討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第一,海德格爾前期的世界和時間學說及其技術哲學含義;第二,圍繞“實驗”(experientia)概念探討海德格爾關于現代技術之起源的觀點,落實于形式科學與實驗的關系問題;第三,圍繞“集置”(Gestell)概念討論海德格爾關于現代技術之本質的基本看法;第四,圍繞“泰然任之”(Gelassenheit)概念討論在海德格爾那里啟示出來的關于現代技術的思想姿態。本文的主要意圖還不在于討論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本身,而毋寧說在于,從海德格爾的存在歷史觀和技術之思出發,反駁技術樂觀主義和技術悲觀主義,闡發一種所謂的“技術命運論”。
今天人類處于技術時代。關于技術有各種各樣的思考和態度,有技術決定論,有技術樂觀主義,有技術悲觀主義,有技術虛無主義,等等。技術決定論的前提實際上是技術樂觀主義,認為技術雖然還不夠,還有各種問題沒有解決,甚至還帶來了許多問題,但好在我們至少可以期待通過技術的進步把它們解決掉。由之引申出技術專家治國論和技術后果論之類的想法,它們大概是一條線上的。與之相對照,今天大部分人文學者多半抱持一種技術悲觀主義和技術虛無主義的態度,說技術再這樣發展下去我們人類就要完蛋了。技術本身的雙刃作用和意義,足以讓技術樂觀主義與技術悲觀主義各執一端,互不相讓。
于是,今天依然有一個問題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怎麼看待現代技術及其后果?技術如此深刻地規定了人類的生活,使得我們每個人還不得不采取一種看待技術的姿態。這就需要技術哲學的思考和討論。
我今天的報告主要討論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主題設為“海德格爾與技術命運論”。海德格爾的技術迷思可能是20世紀最難的一種,哲學界為之著迷者不少,但也有許多人對之不以為然,說他神神叨叨,胡說八道。我個人大概處于中間狀態,以為海德格爾的技術思想確有新義,但也未必神化之。下面我主要分四點來講:第一,討論海德格爾前期的世界學說和時間學說及其技術哲學含義;第二,圍繞“實驗”(experientia)概念探討海德格爾關于現代技術之起源的觀點,落實于形式科學與實驗的關系問題;第三,圍繞“集置”(Gestell)概念解說海德格爾對現代技術之本質的規定;第四,最后圍繞“泰然任之”(Gelassenheit)概念來討論海德格爾對現代技術的態度。我的重點還要放在第四點上,就是想努力一把,從海德格爾那里引申出一種超越技術樂觀主義和技術悲觀主義的技術觀點和姿態,我斗膽稱之為“技術命運論”。
一、重新理解世界與時間
我們知道海德格爾哲學大概以1930年為界,區分為前后兩個階段。①1930年之前的前期海德格爾給人感覺是不關注現代技術的,因為他討論的是“存在學/本體論”(ontologia)的問題,落實于此在的實存狀態和生活世界。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前期海德格爾對傳統哲學的解構和對生活世界(周圍世界)的重新理解(現象學式的理解),根本上仍然具有技術哲學的意義,因為這已經是一個被技術工業規定的世界。今天被現代技術改造的生活世界需要新的經驗。如果人們還是用老舊的經驗來衡量這個世界,總是沉湎于過去,甚至總是美化過去、蔑視現實,那就會出問題的,那就無法面對現實。海德格爾當然不會這樣。現在我們完全可以認為,以《存在與時間》為代表的前期海德格爾的思想目標和思想成果就在于重新理解這個新生活世界(技術人類文明),質言之,就是生活世界經驗的重建。
海德格爾的這項工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重新理解世界;二是重新理解時間。如果我們并沒有太大的純粹存在學/本體論方面的興趣,那麼,我們就不得不認為,關于“世界”(Welt)和“時間”(Zeit)兩大課題的新思考和新理解,無疑就是前期海德格爾最大的哲思成就。
在“世界”問題上,海德格爾受胡塞爾現象學的影響良多,并且進一步把現象學實存哲學化,拓展了現象學的“關聯性思維”,而后者對于傳統西方哲學來說具有革命性意義。西方傳統哲學根本上是一種“超越性思維”,古典哲學尋求一個存在學/本體論的先驗形式結構,認為事物的存在就在于它的自在結構(物是“自在之物”),近代哲學完成了一次轉換,即“自在”(an sich)向“為我”(für mich)的轉換,物是“為我之物”,存在被設定為“被表象性”或“對象性”,但在這兩種哲學中,“超越”(Transcendence)都是一個核心問題。受傳統線性時間觀的驅動,傳統哲學實施了“線性超越”策略,旨在構造一個純形式的、無時間性的先驗領域。
胡塞爾看得很清楚,認識論的基本問題就是“超越”問題:“認識如何能夠確定它與被認識的客體相一致,它如何能夠超越自身去準確地切中它的客體呢?”②胡塞爾試圖通過意向性學說來解決這個問題,其意向性概念的特征之一是所謂“先天相關性”思想:意識不是一片空海灘,不是一個有待充實的容器,而是由各種各樣的行為組成的,對象是在與之相適合的被給予方式中呈現給意識的,而這一點又是不依賴于有關對象是否實際存在而始終有效的。這就是說,對象(事物)是按我們所賦予的意義而顯現給我們的,并沒有與意識完全無關的實在對象和世界“現實性”。因此,意向意識本身包含著與對象的關聯,即“先天相關性”。胡塞爾寫道:“意向性概念原則上就解決了近代認識論的古典問題,即:一個起初無世界的意識如何能夠與一個位于它彼岸的‘外部世界’發生聯系。”③海德格爾對于認識論問題沒有興趣,但對胡塞爾所謂“先天相關性”卻是心有戚戚,因為他從中發現了一種新的事物規定和世界理解的可能性,事物的存在既非“自在”亦非“為我”,而在于“關聯”。海德格爾說這已經是一大進展或者轉折,但還不夠。不夠在哪里?海德格爾說“現象”有三義,即“內容意義”(什麼)、“關聯意義”(如何)和“實行意義”(如何),胡塞爾停留在關聯意義上了,所以還不夠,關鍵還要看“關聯意義”之“如何”的“如何”——意思就是,“關聯意義”是如何發動和實行的。這就有了《存在與時間》中以此在之“關照”(Sorge)為核心的此在在世分析,此在通過“照料”(Besorgen)營造了一個“周圍世界”,又通過“照顧”(Fürsorgen)構造了一個“共同世界”。這種此在在世分析的根本點還在于對作為“因緣聯系”的世界的理解,人生在世,是在一個物物互聯的環境里,也是在一個人人相關的關系中。這樣的想法當然是與西方哲學傳統大異其趣的。而正是技術工業才促成了這種萬物互聯和普遍交往的新生活世界。
那麼,這時候還有“超越性”問題嗎?當然還有,只是被轉換了,就“世界”論題而言,我認為海德格爾把“超越性”問題轉變為“指引性”問題了,就是每一個境域(世界)都超越自身,指引著更大的境域(世界)。而更為要緊的是,海德格爾進一步把“超越性”問題化解為此在的“時間性”問題了。這就涉及前期海德格爾的另一項工作:重新理解時間。
時間問題是前期海德格爾的基本課題,他的《存在與時間》原計劃分兩個部分:“第一部:依時間性詮釋此在,解說時間之為存在問題的先驗視域;第二部:依時間狀態問題為指導線索對存在學歷史進行現象學解析的綱要。”④但實際上最后只完成了第一部第一篇和第二篇。我們且不管這一點,我們要關心的是:海德格爾如何理解時間?海德格爾如何把“超越/超越性”問題歸化為“時間性”問題?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說,傳統的時間觀都是“現在時間”,此時此刻是現在,過去是已經消失的現在,未來是還沒到來的現在,所以時間就是一條“現在之河”,這就是“線性時間”。亞里士多德就已經開始了這種線性時間觀。亞里士多德說時間是“關于前后運動的數”⑤。時間就是我站起來走到門口這樣一種運動的計量。時間是直線的和均勻的運動。近代物理學也建立在這個線性的和均勻的時間觀念基礎之上。尼采在1884年左右形成“相同者的永恒輪回”學說,提出一種新的時間觀念,我把它叫做“圓性時間”。海德格爾繼承了尼采的思想,對之作了一種推進,把它轉化為一種以將來或未來為中心的曾在、當前與將來三維循環的時間性實存結構。
尼采和海德格爾都明顯意識到了一種人類生活世界以及世界經驗的根本性變化。他們直觀到今天的生活世界需要另一種時間經驗。當然我們大部分時候采納的是“時鐘時間”,比如拿出手機來看一下幾點了,哦已經四點鐘了,有點遲了,等等,這個“時鐘時間”或者“鐘表時間”就是均勻的“線性時間”。自然人類的日常生活采取這樣的尺度,這本身沒錯,但尼采和海德格爾會說,這是物理—技術的時間觀,還不是原初的時間經驗,或者說,還有非科學的時間觀,即我所謂的“圓性時間”,就是一種“實存論的”時間理解。“超越”問題被移置了,被坐落于個體此在的“實存”上。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導言中為自己的哲學給出一種總體定位:
存在絕對是transcendens[超越、超越性、超越者]。此在存在的超越/超越性(Transzendenz)是一種別具一格的超越/超越性,因為在其中包含著最徹底的個體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對作為transcendens[超越、超越性、超越者]的存在的每一種展開都是先驗的(transzendental)認識。現象學的真理(存在的展開狀態)乃是veritas transcendentalis[先驗的真理]。⑥
此在存在(實存)的“超越性”是什麼?海德格爾在上面這段話里沒有明說,但據我的理解顯然就是“時間性”。海德格爾在別處寫道:“時間性是源始的、自在自為的‘出離自身’本身。因而我們把上面描述的將來、曾在、當前等現象稱作時間性的綻出。”⑦所謂“時間性”就是此在面臨邊緣處境(死、無)而揭示出來的“超越性”的源始結構。此在實存(Existenz)即“綻出”(Ek-stase),即“超越”。傳統的“超越”問題在此被實存化了,成了三維圓性循環的時間性綻出。⑧
概而言之,前期海德格爾的“世界”觀和“時間/時間性”觀具有顛覆性的意義。世界被理解為關聯世界,時間性被理解為此在實存的超越性結構,或者說,傳統無時間的“超越”被時間化了。而海德格爾之所以能夠達成這樣一種新理解,根本原因在于在技術工業的改造下,生活世界變了,生活世界經驗也相應地變了。
海德格爾的思想轉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完成的。1933年他當了10個月的弗萊堡大學校長,但10個月后就辭職不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質上是技術工業之戰。眾所周知,當年我們國家在技術工業上十分落后,不會制造飛機大炮坦克,結果就被日本人打得狼狽不堪。海德格爾是在1933-1934年以后,在二戰的槍炮聲中,明顯地意識到技術工業正在脫離自然人類的控制,成為一種極端的異化力量,于是展開了關于現代技術的哲學思考,尤其在他的《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1936-1938年)中做了深入的探討。
現代技術已經全方位地統治了這個世界,其中有四大因素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一是核武核能,二是環境激素,三是基因工程,四是人工智能,它們分別與物理、化學、生物學和數學四門基礎科學相關。我們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礎科學的重要性。這四大因素都充分體現了現代技術的兩面性,即福祉與風險并存。這就是說,它們已經或者可能造福于人類,但同樣也可能給人類帶來滅頂之災。雖然核武器只在1945年夏天爆炸過,但其驚人威力使自然人類徹底發呆發懵了,終于使人意識到自然人類歷史的終結以及所謂“人類世”(Anthropocene)的開始。化學工業改善了人類的生活,而作為它的后果之一,環境激素構成自然人類的一個最隱蔽的技術風險。生物工程是今天人們最擔憂的,特別是基因工程,也是最近一些年里發展最迅猛的,其影響深不可測,也最讓人糾結。它可能使人類壽命大幅延長,但也帶來很大的風險,人們不知道后果到底會怎麼樣。⑩人工智能(AI)可能是今天最讓人興奮的,與之相關的互聯網、大數據技術今天已經掌控了人類,現在誰還能離開手機和電腦?雖然人工智能還在初級階段,但有人(比如已故的物理學家霍金)已經無比恐慌,斷言機器人消滅人類的時間已經不遠了,自然人類存在的時間不長了。(11)
現代技術四大因素本質上發端于近代自然科學,而后者又直接源自古希臘的形而上學哲學傳統。所以也可以說,古希臘形而上學通過近代自然科學和現代技術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實現。今天現代技術已經占領全球。但這里面有個難題,是我一直沒有想清楚的。海德格爾在《哲學論稿》中花了好大篇幅來討論這個難題,就是:源自古希臘的形式科學為什麼可以與實驗科學相結合,從而成就了技術工業?形式科學的定律和規律與個體、具體的東西沒有關系,與個別經驗也無關。典型的形式科學有邏輯學、幾何學、算術等,實際上語法和存在學/本體論(ontologia)也可歸于形式科學。為什麼在古希臘產生了形式科學而別處一概沒有?(12)這本身已經成了問題。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什麼形式科學到近代可以與實驗科學結合起來?或者說,為什麼形式科學可以被實驗化了?這事想來無比怪異。我認為這也是思想史(哲學史和科學史)上尚未完滿解決的兩大問題。
關于第一個問題即形式科學的產生,海德格爾在1935/1936年弗萊堡冬季學期講座《物的追問》(《全集》第41卷)中做了專題討論。我注意到這個講座的時間,恰好與海德格爾寫作《哲學論稿》的時間相合。在《物的追問》中,海德格爾從“學”(mathesis)與“數學的東西/數學因素”(mathemata)的關聯入手,認為在希臘已經產生了“數”意義上的“學”,希臘原本的“學”是“模仿”(mimesis),是“模仿之學”,但到希臘哲學和科學時代就已經有了“數之學”(mathesis),這兩種“學”有著根本的區別,海德格爾一言以蔽之:可“學”的不是具體的3只蘋果或3個人,而是3。但如果沒有3這種在先的認識,我們如何可能“數”3只蘋果、3個人呢?(13)
海德格爾更關心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形式科學如何可能與實驗科學結合起來。這個問題首先可以表達為現代科學與古代科學的區別問題。海德格爾正是由此入手來討論,他比較了亞里士多德的運動觀與牛頓和伽利略的運動觀。亞里士多德認為,物體是根據其“本性”而運動的,這是他基于古典的“自然”(physis)理解的運動觀。而牛頓的第一運動定律(慣性定律)則不然,認為任何物體若無外力影響,都將保持其靜止狀態或勻速直線運動。(14)在這兩者之間到底發生了何種變化呢?海德格爾居然看出了八大區別,舉其要者:首先牛頓慣性定律不再區分地上和天上的物,而是抽象地說“所有物”;其次是以直線運動取代了亞里士多德的圓周運動;再就是慣性定律把“位置”抽象掉了;運動與力的關系被顛倒了,力的本質是由運動定律來規定的;自然不再是物體運動的原則,而是成了物體在空間和時間中在場的形式,等等。(15)根本點還在于自然/存在理解變了,亞里士多德那里的具體的物—位置—空間關系被形式化和抽象化了。
那麼,形式科學到底如何可能被實驗化的?或者說,現代“實驗”到底是如何發生的?海德格爾討論了伽利略的自由落體定理和他做的比薩斜塔實驗。在亞里士多德的運動學說中,物體是按“本性/自然”運動的,重的物體向下運動,輕的物體向上運動;如果兩個物體一起下落,則重的必定快于輕的。伽利略的觀點則恰恰相反,他認為,一切物體下落速度相同,下落時間的差異只是由于空氣阻力,而不是因為不同的內在本性。伽利略試圖通過實驗來證明此點,這就是著名的比薩斜塔實驗。但實際上這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實驗,因為自由落體下落的兩個物體,一個輕的和一個重的,只有在真空狀態下才是同時落地的;要是不在真空狀態下,這是不可能的事,不同重力的物體從塔上下落時并不是絕對同時的,而是有細微的時間差異的,但伽利略仍舊堅持自己的觀點,實驗的目擊者便更懷疑他的觀點了。(16)伽利略當時卻宣告自由落體實驗成功了。自由落體定律是一個形式科學的規定,通過這個不成功的比薩斜塔實驗被“證實”了。但這個實驗的實際情況到底如何,其實是無關緊要的,其實也與他的“自由落體定理”無關,重要的是這個實驗表明:形式—數學的世界是可實驗的。現在看來,這一點顯得十分關鍵,因為它把形式科學與實驗科學結合起來了。有了這個結合,才有了近代科學和技術工業,這才有了今天這個最數學——普遍數學——的技術時代。海德格爾指出,伽利略做的實驗其實是一種“心靈設想”(menteconcipere):
所有物體都是相同的。沒有任何運動是優越的。任何位置對于任何物體都是相同的;每一時間點對于每個物體都是相同的時間點。任何力只是根據它在運動變化——這一運動變化被理解為位移——中引起的東西來加以規定。對物體的一切規定都有一個基本輪廓,據此輪廓,自然過程無非是質點運動的時空規定。這一關于自然的基本輪廓同時也限定著自然的普遍同一的領域。(17)
一句話,一個有別于古典時代的自然世界的形式的—數學的抽象物理世界形成了。我們當然可以說,伽利略的實驗無論是否成功,都表明當時知識的興趣已經轉移,從靜觀式的沉思轉向了務實的和行動的經驗和實驗,這樣的說法沒錯,但似乎還不夠。進一步,海德格爾在《哲學論稿》中試圖區分“經驗”與“實驗”。有不少學者認為中世紀后期就出現了經驗科學的興趣以及現代科學的苗頭,海德格爾卻持有不同的看法。海德格爾在德語字面上來了解“經驗”(experiri),認為“經驗”意味著“沖向某物,某物沖向某人”,這就是德語的動詞erfahren。這種“經驗”還不是“實驗”(experientia),而只是“實驗”的準備。海德格爾寫道:
作為考驗性的走向和觀察,經驗的目的從一開始就在于制訂出一種合規則性。……唯在有一種對本質性的、而且僅僅在量上規則性地被規定的對象領域的先行把握之處,實驗才是可能的;而且,先行把握因此規定著實驗及其本質。(18)
所謂“經驗”乃是“一種對被尋求者的先行把握,也就是對被追問者本身的先行把握。相應地,〈它乃是〉程式的設置和安排。然而,這一切experiri[經驗]都還不是現代的‘實驗’。現代‘實驗’(作為試驗的考驗)中決定性的因素并不是‘設備’本身,而在于問題提法,亦即自然概念。現代意義上的‘實驗’乃是精確科學意義上的experientia[實驗]。因為精確,所以才是實驗。”(19)這就是說,“實驗”的決定性要素是數學:“因為現代‘科學’(物理學)是數學的(而不是經驗的),因此它必然地是在測量實驗意義上實驗的。……恰恰數學意義上的自然籌劃乃是‘實驗’(作為測量實驗)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的前提。”(20)
因此,海德格爾得出結論,認為現代實驗之可能性的基本條件有兩項:其一,對自然、對象性、被表—象狀態的數學籌劃;其二,現實性之本質從本質性(普遍性)向個別性的轉變。“唯有在此前提下,一個個別結論才能要求證明和證實的力量。”(21)這個結論如何?用簡化的表達,現代實驗的基本條件是數學+個體化(個別化)。海德格爾的這個結論恐怕會讓人失望,但哲學家的討論大概只能到此為止。無論如何,我認為他的思考方向是對的。形式科學與實驗科學的結合才導致了今天的人類技術文明。要是沒有這個結合,今天的技術工業文明是不可設想的。所以這是一個特別重大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討論。
接著我來講第三個問題:現代技術的本質是什麼?我們說過,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被認為是20世紀最艱難的一種,難在哪里呢?主要是對海德格爾的Gestell一詞的理解。美國學者詹姆遜說這個Gestell是20世紀最神秘的一個詞語。這個德語詞語的意思就是“架子”,所以已故的熊偉先生把它譯成“座架”,但在海德格爾這里這個譯名不是太確當,或者說還不夠;我認為我們更應該從字面上來理解,前綴Ge就是“集/集中”,詞根stell就是“置/放置”,所以我把它翻譯成“集置”。到目前為止,學術界似乎還只有少數人采用了我建議的這個譯名,有人甚至也不用熊偉先生的“座架”,造出另一些奇奇怪怪的譯名。
海德格爾區分現代技術與古代技術,把現代技術的本質規定為“集置”(Gestell)。所謂“集置”包含著對現代技術以及作為現代技術之基礎的物觀念和存在觀念的規定和解釋。現代技術被海德格爾設想為在“存在歷史”(Seinsgeschichte)的第二個階段的現象,即近代以知識論哲學或主體性形而上學為基礎的現象。也就是說,海德格爾認為,如果沒有近代知識論,沒有主體性哲學,就沒有現代技術。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海德格爾是對現代技術做了一個存在歷史性的理解。
從存在歷史上看,海德格爾的“集置”實際上是一種對象化。什麼叫對象化?我們已經聽得太久太多了,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材料里總是講“主體、客體、對象化”,聽得學生們都麻木了,但“對象化”實際上是近代哲學的核心概念。(22)所謂“對象化”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在觀念和思維層面上,我們一般說哲學思維和科學思維,即在康德那里完成的“表象性思維”。眾所周知康德是一個誠實的哲人,他說物本身是什麼,我不知道,也是不可知的,我只知道物對我來說(for me)是什麼。歐洲古典哲學總是說:物的存在在于它本身,物本身有一個結構,構成了事物的存在。但到歐洲近代哲學就不一樣了,康德說:物的存在就是被表象,物的存在在于for me,物對我來說是什麼。什麼叫“對我來說”(for me)呢?就是說物有沒有進入到我的表象性思維范圍之內,物有沒有被我(主體)所表象,物有沒有成為我(主體)的對象?康德為這個事情花了不少腦筋,他有時候說“表象”,有時候說“設定”。康德為什麼是近代哲學的完成者?因為他完成了這一步,即把物的“存在=被表象性=對象性”這個等式建立起來了。這種觀念上的“對象化”是“集置”的第一個意義:“集置”就是“表象”(Vorstellen)——“表象”這個譯名不好,為了與“對象性”相對應,它更應該被譯為“置象”。
不過,海德格爾的作為“對象化”的“集置”還有第二層意思,就是在行動—操作—制造層面上,說的是對事物的擺置和置弄(stellen),比如說Herstellen就是把事物置造/制造出來,Verstellen就是偽置/偽造事物,Bestellen是把事物訂置/預訂了,好比人們發現南海海底有可燃冰,但憑借現在的技術手段還開采不了,不過我們遲早是要實施開采的,它就已經被預訂了,進入我們的“集置”范圍之內了,這叫“訂置”。在這種“對象化”意義上,“集置”就是“置造—偽置—訂置”等等行動的復合。
所以,我們要從這兩個層面上來理解作為“對象化”的“集置”。這樣說來,海德格爾所謂“集置”就并不多麼費解了。根本上這是一個“存在歷史”的規定,是從“主體性形而上學”批判意義上給出的關于現代技術之本質的界定。
除了把現代技術的本質規定為“集置”外,海德格爾還把技術與“解蔽”聯系起來,以他的說法:“集—置乃是那種擺置的聚集,這種擺置擺弄人,使人以訂置方式把現實事物作為存料而解蔽出來。”(23)現代技術是一種“解蔽”方式,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知道海德格爾重新理解和翻譯了希臘的aletheia(真理),把它改譯為“無蔽、解蔽”(Unverborgenheit)。這種改譯意義重大,因為我們習慣的“真理”是一個知識學概念,即“知”與“物”的符合。這已經是常識了,我下一個知識判斷,表達一個命題,若是與對象符合,那就是“真的”,若是不相符合,那就是“假的”。海德格爾會說,這事沒這麼簡單,所謂“解蔽”即“揭示”,不光認知和認知判斷是“揭示”,我們的許多行動都是“揭示”行為,我把你看作什麼,如此簡單的感知也是一種“揭示”。海德格爾進一步認為,知識/科學還不是原初的“揭示”,創作、犧牲、思想等可能是更原初的“揭示”即“真理”。關鍵還在于,“一切解蔽都歸于一種庇護和遮蔽”。(24)若是沒有遮蔽,何來解蔽?因為我把你看作什麼,已經構成一種對你的遮蔽——區分、掩蓋和否定等等,如果沒有后者,實際上我無法把你看作什麼。
現代技術當然也是一種“解蔽/揭示”。但這種“解蔽/揭示”并不是原初的和基本的,而是派生的或衍生的。它以上面描述的“集置”方式把事物當作“存料”(Bestand)而揭示出來。現在它已經成為一種統治性的力量,迫使人類“一味地去追逐、推動那種在訂置中被解蔽的東西,并且從那里采取一切尺度”,由此鎖閉了人的其他更原初地參與到“無蔽狀態”中的可能性。(25)這就把人帶入“危險”(Gefahr)之中了。海德格爾有一段話寫道:
對人類的威脅不只來自可能有致命作用的技術機械和裝置。真正的威脅已經在人類的本質處觸動了人類。集置(Gestell)之統治地位咄咄逼人,帶著一種可能性,即:人類或許已經不得逗留于一種更為原始的解蔽之中,從而去經驗一種更原初的真理的呼聲了。(26)
這里所謂“更原始的解蔽方式”是什麼呢?顯然是指techne意義上的,也即藝術和手工意義上的揭示和解蔽。但我們現代人已經離開這種意義上的真理了,我們已經進入另一個體系之中。由于現代技術的這種集置作用,自然人類的生活世界和文化世界已經衰敗,正在瓦解之中。大家注意我用的詞語,叫“自然人類的生活世界”,今天在座各位包括我自己,表面看來還是自然人類,但已經要大打折扣了,我們已經不是自然人了,我們已經被技術工業加工過了,身體和精神兩方面都被深度加工過了,而且還在不斷地被加工。此即海德格爾所說的現代技術“已經在本質深處觸動了人類”。
四、二重性:技術命運論
特別是在20世紀的進程中,技術哲學越來越成為一門熱門學科或研究領域。有人把海德格爾稱為技術哲學的先驅人物。這恐怕還是有失妥當的。實際上,技術是一個十分古老的哲學討論課題。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對技術問題就有過深入思考。往近處說,至少弗蘭西斯?培根可算最早的“技術哲學家”。正如一般哲學的發展狀況一樣,在技術哲學上同樣也有路線分歧,有人文主義的技術哲學與科學主義的技術哲學。國內有學者區分了所謂“技術哲學”的四個傳統,謂“社會—政治批判傳統”、“哲學—現象學批判傳統”、“工程—分析傳統”和“人類學—文化批判傳統”,自然把海德格爾放在“哲學—現象學批判傳統”里面了。(27)這個區分比較細致,但若簡明一些,仍不妨依照C.米切姆(Carl Mitcham)的劃分,分為“工程派技術哲學”(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和“人文派技術哲學”(Humaniti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兩大派。(28)從哲學史的角度來看,米切姆的劃分基本上仍舊與我們所熟悉的經驗—分析哲學傳統(科學主義)和人文哲學傳統(人文主義)之兩分相合。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無疑屬于以歐陸為主體的人文派。我愿意把海德格爾看作人文主義路線上對技術問題思考最深入的一位思想家。
但在對待現代技術的態度或姿態問題上,海德格爾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文主義者,而不如說,他既反對科學主義和技術樂觀主義,也不贊成具有技術悲觀主義傾向的人文主義。對此他是有充分自覺的,他明確地區分了兩種姿態,即“盲目地推動技術”與“無助地反抗技術,把技術當作惡魔來加以詛咒”(29)。這兩種姿態都不可取,實際上就是技術樂觀主義與技術悲觀主義。海德格爾試圖超越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而要走出一條中間道路,我稱之為“技術命運論”。這種姿態當然會左右不是、兩面不討好的。
關于現代技術世界,海德格爾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即“泰然任之”,德文的Gelassenheit,英文的let be,熊偉先生把它譯成“泰然任之”,蠻有意味的。let be是什麼意思呢?let be就是不要緊張、放松,你看我們現在都不會放松了,緊張得不得了,所以要放松再放松。所謂let be就是要對技術世界保持既開放又抵抗的姿態。海德格爾說什麼呢?我們對技術世界既要說“是”,又要說“不”,這種想法和態度可以說是采取了“中道”姿態。現在人文學界有許多“假人”,他們一方面反技術,另一方面又享受著技術。今天誰真的能回避和否定技術呢?
我們必須看到技術的普遍性。今天最可怕的情況是,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樣,今天一整天都沒碰到過手工的東西,全是機械制造的物品。但是,也就是三四十年前,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們的生活世界還是以手工物品為主的世界,放在我們桌子上的東西大部分是手工的,我們的椅子都是木頭椅子,人工做的,好多器具也都是手工做的。在工業化進程中,我們的生活世界已經巨變,有人間我這個變化主要體現在哪里?我的說法是,我們的生活世界變成抽象的世界了。我面前這個茶杯,如果是機械產品的話,在我面前放了幾千個,我就沒法把它與別的茶杯區分開來了,這時候我對它的感知就會落空,因為我們自然人類的感知經驗是靠事物的差異性來確認的。我今天進這個教室,各位都長得蠻好看的,都長得不一樣,感覺蠻好;如果我進來,各位長得一模一樣的,我肯定說完了,這個世界有問題了。但是今天的技術正在把我們往一樣的方向規整。我現在明顯有一種感覺,我們的學生長得越來越類似了。這是技術工業的后果之一,它有一種強大的同質化的敉平作用。技術工業無法抵抗,但不抵抗行麼?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海德格爾說let be,根本意思是說,要讓今天由技術工業制造出來的技術對象重新回到生活世界里。我想其中至少含有一個意思,要使技術對象變成有差異的個體。這個想法會不會讓人覺得很無聊?可能嗎?技術產品怎麼可能“降解”變成生活世界里面的事物呢?
還有一點,在技術—工業—商業時代里,人類正在變成一個奇怪的欲望動物。我為什麼要加上“奇怪的”這個形容詞,說“奇怪的欲望動物”?因為以前自然人類也有激情,也充滿著欲望,但今天人類的欲望無比怪異。為什麼這麼說?我們處身于這樣的一個狀況:我們的能力越來越差,但越來越想要。這才變得奇怪了。人類已經進入這樣一個狀態,一直是要要要,然后就不行了,開始發明各種藥和各種手段,讓他變得還能要。人要要要,要不了還要,人類就處于這樣一個艱難的悖謬的狀況中。結果是什麼?結果是我們失去了“不要”的能力,因為我們太要了,習慣于要而不會“不要”了。就今天這個欲望經濟而言,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用了“熵”的概念。斯蒂格勒說,人類世是“熵”不斷增長的時代,沒完沒了,絕路一條,所以要抵抗消費主義,營造一種以“負熵”為基礎的經濟——但這是可能的嗎?
斯蒂格勒的技術哲學是可以接通海德格爾有關“泰然任之”的思想的。而在我看來,圍繞“泰然任之”概念,海德格爾實際上闡發了一種“技術命運論”。所謂“技術命運論”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在此愿意指出如下三點:
其一,主張現代技術是一個存在歷史現象,是命運性的。正如我們前文所指出的,海德格爾是在存在歷史意義上、特別是從主體性形而上學批判的角度來規定現代技術的。在把現代技術的本質揭示為“集—置”以后,海德格爾明確地說到“命運”:“現代技術之本質居于集—置之中。集—置歸屬于解蔽之命運。”(30)海德格爾把現代技術理解為一個存在歷史現象,認為是在近代主體哲學的影響和規定下才會產生近代實驗化的科學,進而形成技術工業。在此意義上,海德格爾認為,現代技術已經成為一種自主的力量,我們人類已經無法控制它了。海德格爾還進一步認為,正是因為自近代以來,歐洲人變得自我感覺越來越好,人的主體性越來越強大,于是缺失了那種存在命運感,現代人作為規定者再也不愿承認自己是被規定的,所以才會有現代技術和技術工業,技術工業才會占據支配地位。
其二,承認技術統治已成定局,人類被技術所規定。人類進入新文明階段,自然人類文明向技術人類文明轉換,海德格爾稱之為存在歷史的“另一個開端”。現在我們完全有理由把這種轉換標識為“人類世”了。所謂“技術統治”是與傳統的“政治統治”相對而言的。以前自然人類文明實施的是政治統治,就是通過商討、討論來完成的權力運作。我們一屋子人誰當老大?不要以為坐在中間的就是老大了,那不對,我們投個票唄,哪怕裝樣子也要投一下。以前在自然人類文明狀態中,無論是封建時代,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制度,多多少少都是通過商討或協商來實現權力運作和政治治理的,但進入技術工業時代以后,情況就變了,統治方式就變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很牛,但大家也要注意,現在美國政治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卻是技術資本。我這樣講比較抽象,舉個例子,特斯拉的馬斯克是美國積極鼓吹要跟中國搞貿易戰的重要人物之一,但貿易戰剛開始,他就拖著拉桿箱,跑到上海浦東來拿地了,在浦東建了特斯拉工廠。這就叫技術資本的力量,這時候,政治恐怕只不過是技術資本的表現形式。這正是問題所在,技術統治的意義會變得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強烈。
如何來理解現代技術的統治地位?人們現在不愿意承認現代技術的統治地位,甚至理解不了這種狀況,主要原因在于多數學者和民眾還站在自然人類的立場上,還局限于傳統人文科學的知識范圍內。這是一個大問題。現代技術的統治地位意味著自然人類精神表達系統的崩潰,后者的主要成分是傳統哲學、宗教、藝術。尼采說“上帝死了”,真正的意思是自然人類精神表達系統崩潰了。對自然人類來說,哲學是制度構造的基礎,宗教是心性道德的基礎,所有的制度背后都有一種哲學,就像所有的道德背后都有宗教。尼采為什麼說自己是個“非道德論者”?因為他知道宗教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了,而沒有宗教的敬畏感,何來道德?所以我們已經進入到一個非道德主義的時代。20世紀出現那麼多有關“后哲學”和“后宗教”的討論,說哲學完了,宗教完了。不要以為這些哲學家在瞎掰,他們是在揭示一個文明的新現實,這個新現實就是:自然人類文明的退出,另一種文明開始了。
其三,貫徹是與不的二重性,既順命又抗命。如前所述,海德格爾的“泰然任之”主張對技術世界既說“不”又說“是”,這是“技術命運論”的基本策略,即堅持順命/聽命與抗命/抵抗的二重性,努力啟動文明中非技術性(非對象化、非主體性)的要素。我們確認現代技術的統治地位,但并不意味著要主張技術決定論或者技術樂觀主義。什麼叫技術樂觀主義?按尼采的說法只有兩點:自然可知,知識萬能。整個歐洲啟蒙運動的核心要素也就是這兩點。“技術命運論”承認技術統治,但并不主張技術樂觀主義。另一方面,所謂“技術命運論”也不主張技術悲觀主義,不是要對技術世界采取逃避的、甚至詛咒的態度。而不如說,我們要直面技術世界,采取積極的抵抗姿態。在這個技術統治的時代里,我們需要通過藝術人文科學進行抵抗,主要通過藝術與哲學的方式進行抵抗。因為如果沒有抵抗,自然人類文明將加速崩潰。
作為自然人類的我們心有不甘。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意在重新喚起近代以來已經消失掉的命運感。今天我們已經失去了這樣一種能力,無力于感受命運,不能承認我們是被規定的。但海德格爾卻想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自然人類還要有未來,就必須恢復這樣一種感覺:我們是被規定的。
①20世紀另一位大哲維特根斯坦差不多也以此為界分成前后兩期哲學,都構成一種轉折。兩位哲學家之間是可以作一番比較和對照的。兩者并不相互關注,但為何有此同步?這真的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這里且擱下不表。
②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倪梁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第22頁。
③胡塞爾:《現象學的方法》,黑爾德編,倪梁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第18頁。
④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商務印書館,2016,第56頁。
⑤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張竹明譯,商務印書館,1982,第125頁。
⑥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商務印書館,2016,第54頁(譯文有重要改動)。
⑦M.Heidegger,Sein und Zeit,Tübingen,1993,S.3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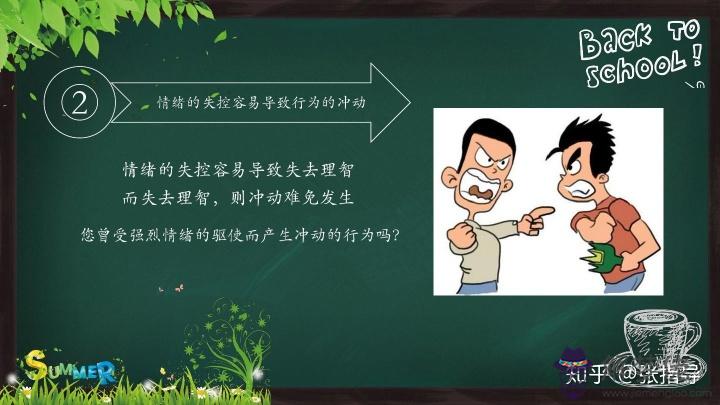
⑧參見孫周興:《語言存在論——海德格爾后期思想研究》第一章第四節,商務印書館,2011,第56頁以下。
⑨相關文獻可參見海德格爾:《存在的天命——海德格爾技術哲學文選》,孫周興編譯,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8。
⑩前不久媒體報道說日本政府批準了生物學家進行人類基因跟動物基因的雜交,后來說這是謠言,日本政府已經辟謠了,要禁止這個實驗!我們已經有雜交的植物,比如雜交稻,但是把人類基因與動物基因雜交一下,會出來一個什麼東西呢?后果是什麼?不知道。
(11)較詳細的討論可參見拙文《技術統治與類人文明》,《開放時代》2018年第6期。
(12)我們知道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就認為“希臘文明的突然興起”是人類歷史上“最使人感到驚異或難于解說的”的事,而希臘文明的核心要素,在羅素看來是他們首創了數學、科學和哲學。參見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6,第24頁。
(13)更詳細的討論可參見孫周興:《從模仿之學到未來之學》,《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

(14)(15)(17)Cf M.Heidegger,Die Frage nach dem Ding,Frankfurt am Main,1984,S.84; S.87—89; S.92.
(16)Ibid.,S.90.實際上只有在真空條件下,兩個不同重力的物體才可能同時落地,而在伽利略當時的實驗中是不可能的。
(18)(19)(20)(21)海德格爾:《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14,第189頁;第195頁;第192頁;第193頁。
(22)我曾經說過,如果我們通過“主體、客體、對象化”這套認識論說辭來解說馬克思哲學或馬克思主義哲學,那麼我們就面臨一個危險,就是把馬克思哲學又拉回到近代哲學里,我們就把馬克思哲學降低了。馬克思是一位現代主義哲學家,甚至是一位當代哲學家,已經超越了康德、黑格爾等的德國古典哲學,或者更應該說,已經超越了近代哲學。參見拙文《馬克思的技術批判與未來社會》,《學術月刊》2019年第6期。
(23)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18,第26頁。
(24)(25)(26)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18,第27頁;第28頁;第29頁。
(27)吳國盛編:《技術哲學經典讀本》,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第5頁。
(28)吳國盛編:《技術哲學經典讀本》,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第5頁。
(29)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18,第28頁。
(30)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18,第28頁。
來源: 《世界哲學》第20205期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6208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