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上方“社會科學報”關注我們哦!

“沒有人能逃脫命運的安排”

原文:《<命運的捉弄>:一部電影與它的時代》
作者:齊昕(上海外國語大學)
一代人的集體懷舊
1976年1月1日,對于鼎盛的蘇聯來說,應該是一個新的開始。這一天傍晚的5點45分,位于首都莫斯科的蘇聯國家廣播電視第一頻道播放了著名導演梁贊諾夫的影片《命運的捉弄》。近190分鐘的片長,交集著帕斯捷爾納克、茨維特耶娃、葉夫圖申科等詩人的名作改編的抒情小曲,組成一部干凈通透、舒展美好得像片頭莫斯科近郊的碧空一般的影片,轟動全國。

此后,不管政治巨變、物是人非,每年的12月31號,《命運的捉弄》的旋律必定在一套頻道響起,伴著這個巨大國家,從加里寧格勒販賣真假琥珀制品的小販一直到海參崴的漁民,迎接一個又一個新年,成了某種蘇聯式的人文頌歌。
除了俄羅斯本國,中國大概是最喜歡、最接受《命運的捉弄》一片的國家。作為中蘇關系破冰之后較早被譯介過來的蘇聯中后期代表影片,《命運的捉弄》的流傳引起1950年代留學龐大帝國的一代人的集體懷舊。他們懷念片中典型的蘇式人情與物質細節。

片中被梁贊諾夫暗自笑為“標準化”的蘇式生活點滴,曾讓學生時代的他們感受到了一種奇特的、整齊劃一的物質進步。不過,毫無疑問,此時蘇聯的文化面貌,與他們留學的那個時代已經非常不一樣。
比如,早個一二十年,很難想象帕斯捷爾納克或是茨維塔耶娃的詩歌能夠出現在文化產品中,并留名在片頭的字幕里。1970年代,兩位詩人還遠談不上徹底回歸,但均有了權威的單行本。詩集印數雖有限,卻在熱愛閱讀的蘇聯民眾中,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里迅速流傳。自然而然地,作為那個時期蘇聯電影大片的導演,梁贊諾夫所引導的大眾文化審美,也悄悄向真正的文化與文學經典轉向。

極為多產,且從《意大利人在俄羅斯的奇遇》開始便迷戀高耗資、大制作的梁贊諾夫其實花了特別的心血在《命運的捉弄》上。
在這之前,他在蘇聯電影界的成功,多少需要玩兒點迎合俄羅斯民族心理的鬧劇情節。于是,他在1974年末正式開拍《命運的捉弄》的時候,人們都以為,梁贊諾夫大約是要休息一下,搞一個類似于獨幕輕喜劇的東西。

《命運的捉弄》的導演:梁贊諾夫
然而正是這一年,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徹底定型。勃列日涅夫作為國家最高元首的象征意義遠高于實質;經歷了流放、病痛、回歸的索爾仁尼琴在官方的出版物中露了個頭,寫下憤懣無比的《致蘇聯最高領導人書》和《致大牧首書》,最終被迫離開蘇聯,開始了二十余年,跨越歐洲與北美的流亡;赫魯曉夫執政后期興起的地下和手抄出版物運動迎來真正的全國性高潮,《大師與瑪格麗特》《日瓦戈醫生》等長篇巨制,別爾嘉耶夫在歐洲發表的宗教哲學論文,阿赫瑪托娃、蒲寧的日記與詩歌,往往以天藍色的小體字打印、脆薄的紙張裝訂成冊,被無數人熬夜悄悄捧讀。

《命運的捉弄》拍了整整一年多。1975年初,劇組在莫斯科西南區拍外景,偏偏迎來暖冬,所以片中的雪景其實多為人造。仿佛二十年前作家愛倫堡命名的“解凍”,到了這個時候才在大眾文化中真正開始升溫。
梁贊諾夫的保守與激進
《命運的捉弄》的成功,從技術上來說,跟如今大眾文化產品制作的市場規則基本是一個道理。梁贊諾夫的保守與激進在此真正水乳交融。
片中的女主人公娜佳,毫無疑問是個新時期的高大全女性形象,延續了俄羅斯自民族文化經典真正形成以來對女性形象的男權式消費:純美不到一定地步的話,那麼就請徹底瘋魔,最好是美艷與瘋魔結合,如《白癡》里的納斯塔西亞·菲利波夫娜。

《命運的捉弄》的女主角:娜佳
娜佳的經世美麗、優雅教養,以及微妙的社會意義上的“自覺受難”(大齡未婚、被前男友玩弄、感情生活一團糟……),簡直就是某種必需。

而男主熱尼亞的塑造,則徹底相反。活潑俊美且人氣極高的男星們,他一一否定,最終選出了莫斯科“現代人”劇院名不見經傳的話劇演員安德烈·米亞赫科夫:路人甲的外貌,溫存的聲線,靦腆的笑容。

安德烈·米亞赫科夫
毫無疑問,梁贊諾夫顛覆了之前蘇聯主流社會的男性審美,毫不顧及傳統影視作品和民眾心理對強勢威武、高大勇猛,且幾乎永遠毛發濃重的男性形象的認同與追崇。他推出的熱尼亞,仕事平凡(普通診所的外科醫生)、其貌不揚、善良倔強。
對于蘇聯(俄羅斯)社會來說,熱尼亞的身上還有兩處“駭人”的地方:不勝酒力;大齡未婚還不說,仍與老母親同住。然而,這恐怕又是“解凍”以來的文藝作品中最具顛覆性的正面男性形象。

這個身形單薄的俄羅斯男人,看似庸庸碌碌,卻極有自己的原則:從事著收入低下、地位不高卻有益于社會的(他自己堅信此)工作;絕不濫情,不為結婚而結婚;日常生活自然清簡…… 動情的時候,他會拿起吉他自彈自唱。他所唱的,不是一般俄羅斯爺們兒酒醉時候喜歡亂哼的黑話滿篇、情色十足的下作調子,而是延續了中世紀自歐洲傳入的行吟彈唱傳統的詩化小曲。
這些譜上了曲的詩歌的作者,既有1930年代的紅色詩人基爾尚,也有在當時流傳活躍的帕斯捷爾納克,更包括了躥紅全蘇的“國民詩人”葉夫圖申科。

梁贊諾夫選出這些詩歌,并邀請以哲理抒情見長的作曲家麥克·塔里維爾季耶夫為它們譜上曲。他所關注的,是這些詩作里純粹而熱烈的情感表達。男女情愛的糾結也好,親疏無常的嘆息也罷,他要讓這些詩歌從這個不再那麼年輕的男主人公口中唱出來,讓世人知道,正是這個毫無典型蘇式英雄主義氣質的男人,默默經歷著國家奇特而曲折的歷史,敢愛敢恨,沉著安詳,無怨無悔。
這簡直神奇得令人驚嘆。梁贊諾夫所選的這些詩歌,都有復雜的創作背景,時代的變遷與個人的情感交織,甚至有些詩歌顯得隱晦沉郁,如茨維塔耶娃的詩作甚至驚世駭俗地涉及自己的同性情感經歷。他干脆利落地將這些詩歌做“簡單化”處理,襯著莫斯科藍得晃眼的冬季天空和彼得堡新年熱鬧的飛雪,讓它們在這部賀歲影片里集中涌出,仿佛就此撫平了之前的帝國歷史中的狂暴皺褶,在一個仍舊復雜曲折,但終歸平靜富裕了許多的時代,呼喚凡俗而實在的美好。

民族心理認同的范本
據梁贊諾夫后來回憶,片子內部試映時,受到的最大的意見無非是讓他在進行宣傳時把形容影片的“圣誕童話”之類的用語改為“新年童話”。對于在20世紀末期再次經歷巨變的俄羅斯來說,梁贊諾夫的保守與革新,為當代俄羅斯創造了一個忠于社會現實卻超脫于政治生態的民族心理認同的范本。

毫無疑問,1976是屬于《命運的捉弄》的一年。在梁贊諾夫個人的創作履歷上,這是他后來為人稱道的“抒情喜劇”(實際上應該是“抒情悲喜劇”)徹底成熟的一年。《命運的捉弄》捧出了蘇聯中后期文化史上至關重要的內心豐富、沉著動人的中等知識分子形象。在其后的三十年,這一形象都是蘇俄大眾文化的榜樣,像是某種文化意義上的穩固的“中產”標志。1977年,《命運的捉弄》的主創團隊(編劇、導演、主演)獲得國家獎。

德米特里·貝科夫,俄羅斯當今活躍的文化時評家和作家,曾經在多個場合反復稱,1970到1980年代初,不僅是蘇聯,也是整個俄羅斯20世紀史上最好的時期。他從社會保障的全面覆蓋、多民族的融合與共存、文化藝術的爆發性繁榮等多個方面給出了頗為雄辯的證據。整個翻滾沸騰的20世紀,對俄羅斯來說,最好最安穩的竟是社會經濟發展停滯的十來年。

支持他的俄羅斯人喜歡用流行多年的“歐亞觀點”來解釋,也就是說,俄羅斯民族文化里的亞洲(中亞、東亞)因素,使得他們在完成數百年激烈的擴張與征服之后,認同并維持住了充滿東方色彩的層次分明且穩定細密的社會結構與官僚體系。
據說與《命運的捉弄》差不多同時代的影片《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在美國上映時,資本主義陣營里的民眾們不禁驚奇,“原來蘇聯人也是七情六欲、多姿多彩地活著的”。轟動性地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1981),說明當時對于西方普通人了解蘇聯,《莫斯科不相信眼淚》是個啟蒙。

電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而《命運的捉弄》的啟蒙意義,就在于它以蘇聯大眾文化罕有的溫婉語氣告訴我們,只要時間與空間不再那麼追求整齊劃一的迅速拉伸,肯保留一點容納情感和欲望的紋理,那麼就會有簡單而倔強的人性,不多麼離經叛道,卻大而美好,在幾乎沒有市場也談不上什麼商業運作的空氣里,汩汩涌出。

文章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608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今日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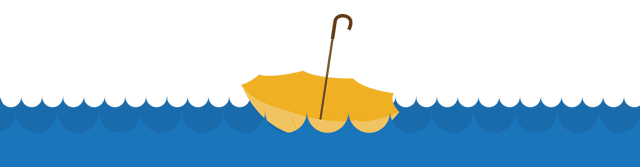
社會科學報
做優質的思想產品
官網
http://www.shekebao.com.cn/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6201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