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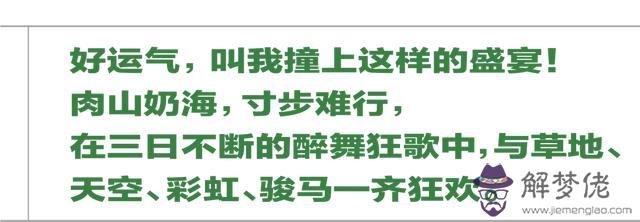
「你運氣好,今年的海拉爾是近二十年來最美的海拉爾。」一下飛機,遇到的司機、小賣部的老板、酒店服務員、牧牛的男孩、年輕的屠夫、燒鍋的阿姨、啃羊棒骨的老奶奶都這樣說,「雨水多,水都漫過橋面了,草長得又綠又長!」
草原上的人一定熱愛夏天,它的變化是陡然而至的急促。云朵像小孩兒捏的棉花,隨手扔向天空,河流是打開的水龍頭一股腦兒漫向了山坡,就連牛、馬、羊也沒準備好,那一日,干枯的草料就不再吃了,集體出動,向山頂進發去吃新抽出來的嫩綠。誰都不知夏來是幾時,藏在林區、草坡、卵石、野芍藥之下的綠意筆鋒一轉噴濺而出,男人女人迫不及待踏上草地去跳舞,用圓滾滾的面龐和鮮衣怒馬去迎接短暫的、繁忙的、聲勢浩大的夏天,盛宴開始,夏氣盎然。

陽光下,山坡頂端盛開的山丹花。
「彩虹!彩虹!」一聲稚嫩劃開帳篷,在里頭躲雨的人紛紛跑出來向南邊的天空望去,那是一道掛在遠處紅屋頂上淡得沒影的彩虹。一切都迫不及待,當風刮來,烏云飄來,雨噼啪噼啪打下來的時候,人們朝著帳篷一擁而入,三個孩童調皮地掀起紙殼趴進去,對著雨點嬉笑尖叫,草地上就這樣呼啦啦長出一頂遮雨的「蘑菇」。也有不怕雨的老人,戴著一頂尖尖的羊毛呢帽子,右手揣進胸前的衣襟里,抽著煙,緩慢踱步,如同那只黑色長發的草原獒一樣漫不經心,他知道,這雨下不了幾時。果然,十分鐘,雨停了。沒等烏云散去,剛才那道彩虹便在濃密又有棱角的云層中潦草地顯現,好似所有的氣象都在慌忙入席。

午后的一陣暴雨,調皮的孩童徑直躲在紙殼下。
人卻是懶洋洋的,外人全然看不出在這片草地上明天要舉辦一場布里亞特婚宴。中午時分,我們穿過那頂由鋼筋和藍色尼龍布臨時搭建的帳篷,桌凳拼湊成長條擺放在中間,桌上幾盤羊骨肉、一壺奶茶、兩三盤油果子和千層酥。來前,我詢問需要注意的禮節,當地牧民想了又想,最后支支吾吾說出一句:「餓了自己吃,沒人招呼你。」果然,那兩三個男人見我們走來,依舊坐在桌前悠閑地喝肉粥 —— 那是羊肉碎熬的大米湯粥,放了胡蘿卜、土豆和大白菜,羊肉的鮮全靠那一抹鹽帶出來。油果子用牛油炸制,溫暖扎實。千層酥是果醬蛋糕的質地,臭李子熬成一層紅艷艷的酸甜醬被雪白的蛋糕坯夾在中間,化在口中的時候剛好可以喝一口奶茶。旁邊那盤羊肉呢,羊脂凝結,讓人不想現在動它,卻在男人不經意的打量下,挑出一條剛好被我也相中的肋排,真叫人懊惱!他掏出刀,向內刮出一片肥瘦相間的肉條,泡在滾燙的肉粥里,雪白的羊脂化成了油花,語氣嘆詞抑不住地在熱氣中輸出,吸、溜、嘖、嗦,讓人好生嫉妒。

提前一天,部分牛羊肉就已經煮好擺在了庫房內。
穿過去,又是一頂帳篷,這里好看極了,滿目都是女人。她們穿著不同深淺藍色,不同深淺黃色,不同深淺粉色,不同深淺各種顏色的長裙,裙肩是泡泡袖,裙擺膨大得像是有裙撐;頭上綁著各式花紋的頭巾,有些是半透明黃紅碎花紗巾,有些是藍底玫瑰花的針織方巾,有些又是純色白花的棉布巾;每個人又根據衣服和頭巾的顏色搭配不同材質的耳飾、項鏈、戒指,她們崇拜銀,不屑于金,于是你能在白銀里找到鑲嵌著的藍寶石、紅寶石、粉珊瑚、綠松石,像是雪地里的奇遇,叫人眼花繚亂,嘖嘖稱奇。總之是各種顏色在你眼前穿來走去。我猜,她們隨時準備提著牛奶桶,端著果子盤在草地上跳舞。注意!還有那靴子,在草地上穿裙袍如果不穿靴子一定被人笑話,硬朗的馬靴、雕花的尖頭皮靴、漸變色彩復古短靴,她們撩起裙擺打一個結,翻身就能踏上馬背去追趕羊群。

女人們在草原廚房制作辮子腸。
顯然,這是一個草原廚房。女人們在桌前切菜,在地上擇菜,在鍋前煮菜。帳篷內擺了三排長桌,一排供人休息,其他兩排擺放著食材,在盡頭有四口紅磚砌成的直徑 1 米的爐火一直燒著。一口鍋里煮著羊肉碎蔬菜粥,一口煮著肉,一口煮著雜碎,另一口則是奶茶。煮奶茶的婦人朝格吉德瑪身穿寶藍色長裙,戴著細小的藍寶石耳墜,染著粉玫瑰和藍桔梗的頭巾下有兩道細長的眉毛,額頭上輕露幾道細紋來,這提醒著她已經有一個 16 歲大的兒子。但這些褶兒實在無關緊要,她沒有涂抹胭脂的面龐潔凈飽滿,因為鍋爐的熱,染出兩朵薔薇色的紅暈,像從雷諾阿油畫中走出的那些個豐滿的女人。
朝格吉德瑪朝沸水中倒入兩袋牛奶,噼啪作響的柴火下,牛奶飛濺起奶泡,她走出去,將木柵欄上那個小方枕頭模樣的磚茶包取下來,茶包足有 20 厘米見方。所有的茶包都是快樂肥美的跳水愛好者,干燥的茶包遇到牛奶溫泉,立即卸下包袱,反復朝著沸騰的中心翻滾游蕩,吃盡了水,躺平了身姿,愜意地流出暖棕色的汁水,發出一聲「啊」的嘆息,隨即一躍而起,又縱身躍下,棕紅色的茶液像瀑布一樣飛流直下,如此反復三四次,乳白色變成了赭石色。白色棉線的盡頭是朝格吉德瑪的手指,她提著茶包出去,繼續掛在木柵欄上,循環利用。

煮奶茶的朝格吉德瑪。
一柄長勺將奶茶舀進水壺里,又將剩下的舀進保溫瓶中。她沒有停下,在鍋中倒入水清洗,不一會兒,就煮上了一鍋羊雜。之前,她在海拉爾市的蒙餐廳做過五六年廚師,雖然來幫忙的親朋好友沒有規定誰是這場婚宴的總廚,但如今,面前這四口鍋的節奏,全在她的掌控之下。
真正的忙碌始于宰殺第一只羊。
年輕的屠夫趙日格圖高高瘦瘦,面相樂呵,不帶一絲殺氣,與印象中的屠夫完全是兩個模樣,卻無人能敵 —— 不像草原上的屠夫是自發的代代相傳,他 24 歲進入屠宰場,第一個月面對一天上千只牛羊的血腥場面,惡心難忍,打過退堂鼓。不過,在草原,屠宰是剛需,明白了這一點,不會沒飯吃。6 年下來,如今在城里開了一家肉鋪,幫人屠宰、做生加工、賣肉為生。他是位現代意義上的屠夫,無論是回族還是蒙族的屠宰方式他都會,就連草原上的老人都說,沒人能比得過他,他們所謂的比試是指干凈、迅速、利落。

內蒙人宰羊只需要在胸口開一個很小的口子。
趙日格圖還為自己起了一個漢族名字,趙強。他走進遠處的羊圈,10 只待宰羯羊關在里頭,迅速逮住一只羊的后腿往外扯,羊的勁不小,走了幾步,他索性像提行李那樣,抓住羊后背的皮毛整頭提起。兩只羊被捆住雙腿,肚皮朝天倒在吊車下的草地上。等趙日格圖一切準備妥當,俯身拔掉胸口處的一寸羊毛,露出一塊粉嫩的肉皮,接著一把尖刀稍微用力劃開兩寸的口子,那刀真不大,不過五寸長,直刃直柄,薄又窄。他將手縮起來,從小口探入,摳破胸肌肉,找到脊梁處的大動脈,向上一扯,斷了。
羊只是掙了一掙,肌肉的脈搏似乎還在跳躍,羊血全流進胸腔內,一滴血都沒有滲到外面,但已經悄無聲息地結束了,周圍的人靜穆無言。兩分鐘后,另一只羊也結束了,最后一眼的世界是一個倒立的苜蓿草天地。

牧民用噴槍炙烤羊頭和羊蹄子上的毛。
趙日格圖的手伸出來,手臂的汗毛與指縫里淌著溫熱的血。他戴上白手套,解開羊后腿的繩子,刷刷兩下,刀刃劃開羊膝蓋,像武俠小說中那些去人筋脈的高手一樣,幾乎沒看清他的手勢,手掌啪的一下,內力穿透筋骨,隨之而來兩聲清脆的「咔嚓」,后蹄松松垮垮地掛在那里搖擺。
接著,刀刃從尾端挑開羊皮,一點點往上走,如小刀開啟信封,到了胸口三角區,刀分兩路,挑開皮至前腿 —— 到這時都是小心翼翼的,像是畫家在打一個大的輪廓。接下來,是大寫意,趙日格圖的刀尖在羊身上飛舞,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刀刃走過的地方,皮不留肉,似乎它們天生就是臨時黏合上的。在柔軟的羊皮與韌勁的肌肉之間,說不清軟硬的一拳,近三分之一的羊皮嘩啦啦撕開,只聽十幾聲「嘩嘩」聲,半張羊皮便剝了下來。刀刃回到羊頸,來回兩刀,拉出食管,切開氣管,打一個結。繼續劃開前膝,「咔嚓」,繼續劃開右半身,「嘩嘩」,三五分鐘,羊皮與羊身基本分離。

宰牛羊的牧民滿手鮮血。
趙日格圖一人將整只羊舉起來,倒掛在鏟車上,刀隨手一插,豎在羊屁股上,順著一股勁兒,猛地一下撕拉開整張羊皮,至頭頸處,割開頭顱,劃開肚子,內臟流出來,剛好流在草地上那張潔白的羊皮上。一邊是男人們繼續瓜分車頭的羊身,另一邊是女人們紛紛出動,俯下身清理腸胃。蚊蟲、蒼蠅、蜜蜂、獒犬,飛鳥、老鷹,朝著內臟的方向胡沖猛撞,一切從草地上生長出來的又回歸草地。
下午一點,處理完兩只羊,像一個短暫的聚會,牧民們各自散去。趙日格圖坐在陰影處喝啤酒解渴,臉漲得通紅。大伙兒做做、停停、吃吃、喝喝,誰都不著急干活兒。
「牛什麼時候殺呢?」我問。「不知道呢。」他答。
下午三點,「牛什麼時候殺呀?」我問。「誰知道呢。」他回。
終于,四點半,被我問得不耐煩了,他們牽出了一頭黃白花紋的蘇白牛(不能生崽兒的母牛),起先是兩個人牽著,后來,一輛鏟車開過來,將繩子拴在鏟車后面,那牛顯然已經覺察到了什麼,半步也不挪。人不說話,牛不吭聲,一場僵局。

牧民們一鼓作氣將倒地的牛拉入草地中心。
沒有人敢靠近,都遠遠地觀看草地上牛、車、人的默片。只有司機踩油門的聲音,他一邊朝后看牛的勢態,一邊向前緩慢挪著。太犟了,牛勁在默默升溫,它知道自己要死了,腳踩緊了土地,仿佛嗅到了帳篷中那四口燃燒著大鍋正煮沸著肉身,頭鉆進車轱轆里,磕破了頭顱,鮮血從腦殼上流下來,也不愿去深處的草地赴死。
在車的動力下,一步一挪,半個小時后,連車帶牛還是挪到了 10 米之外的草地。車后的繩子松綁,整整八個草原漢子嚴陣以待,圍繞著它,趙日格圖當然是其中一員,在所有人都沒有準備之下,他舉起刀,狠狠插入牛角后的一個點 —— 致命處 —— 后腦勺的動脈神經。一具龐然大物轟然倒塌,深黑的眼睛下是兩道黑色的眼淚,它早就知道自己要死了,這是個在場所有生物都知道的秘密。
牧民像海底分食鯨落的小魚,聚在牛的身旁。隨著它倒塌,嚴肅的、冷峻的氣氛在太陽下融化了。牛的身下仿佛有一團融融的火燒了起來,暖烘烘地捂熱了草地 —— 孩童歡快地沖進沖出;老太太一邊嚼著口中的羊肉,一邊看著不知道是人生中第幾頭牛的倒下;男人們拿出自己的刀,圍站著,交替換下已經疲憊的人;婦人們系起裙擺拿出搪瓷盆和水桶……

掏心宰牛法會保留大量的牛血在肚子中,開膛后將血倒入桶中制作血腸,而后,牧民切斷脊椎,方便切分。
與宰羊幾乎是一樣的操作,只是放大了無數倍。趙日格圖伸進自己的半個胳膊切斷大動脈,早有人準備好不銹鋼盆對準了胸口接住紅彤彤的血,兩個牧民一左一右,腿半跪著壓住牛肚,有節奏地揉按,血汩汩流出,不一會兒就接了兩大桶。八九個人,五六把刀,沿著腹部中線一路劃開牛皮,這時拳頭派不上用場,不能靠撕,只能是割。右邊的皮毛從牛身上卸了下來,一根粗壯的松木樹干踢向牛皮之下,作為一個支點,好讓牛翻身。牛蹄不再是靠掌心的力拍斷,而是靠鋸,在草地上流傳著一個說法,四個牛蹄的重量乘以十,大約能估算出一頭牛的重量,而這牛蹄是連一只手都難以握住的。縱然它已死去,但是乳白色的脂肪之下,肌肉還在彈跳抽動著。
彩虹之后的太陽穿破云層,掀開整塊牛肚腩、露出內臟的那一刻突然變得又刺眼又溫柔。鼓脹、柔軟、乳白的瘤胃足有一個人的上半身那麼大,它在陽光下跳躍著瑩瑩的光,又是流淌的,是裝滿了水的氣囊,是動畫片中的史萊姆,但又是使不上勁兒的,拍動它,它不理,手按下去,它就兩邊鼓起來,只能半推半就讓它跟隨著心臟和迷宮一樣的牛腸通通滾向透明塑料布上。

牛的內臟從牛腹中流出。
牛肚空空,十三對肋骨如山脊盛著一汪谷底殷紅的血湖面朝藍天。開膛屠宰是游牧民族面對「親畜」的心理表現,古代蒙古人認為抹脖屠宰是非常殘忍的,牛羊的靈魂隨著它們的目光走動,它們自出生就兩眼面朝大地,終生尋覓芳草沒機會看往蒼天,靈魂也沒機會屬于蒼天。所以,屠宰時將它們翻過來面朝藍天,死時兩眼望天,靈魂可以盡早超脫升天。
女人們索性在草地上席地而坐,兩三人分得牛腸,五六人分了牛胃,翻出腸胃里沒來得及咀嚼完的草倒在草地上,用清水反復揉搓、拉扯、清洗。帳篷內響起砧板「剁剁剁」的聲音;面盆中攪拌著牛血、小蔥和生姜;年長的婦人坐在一旁編織血腸;洗凈的牛腸、牛網油掛在頭頂帳篷的骨架上,隨時要當心抬頭撞見它們;燃燒的爐火內,朝格吉德瑪用一根針戳破加熱后膨脹的牛腸,汁水直線噴射出來。

牧民們清洗牛肚。
后面那頂帳篷在黃昏中已經成為一片肉山肉林,不同部位的牛肉懸掛在頭頂,男人化身庖丁解牛的大師,落座、站立、蹲下,在任何一塊平坦處,都可成為砧板,蒙古刀在磨刀棍上發出「刷刷」聲響,落在肉身上便同落在豆腐身上那般柔滑。草地上響起「哄哄」聲,那是汽油噴燈對準十個羊頭,燒滅毛發,彌散出焚燒毛發的氣味。白熾燈下,中間的桌子上擺放著手扒肉和酒,地上的斧頭對準松木上的棒骨,「咔咔」直響,跟隨著牧民們每一次砍骨的吆喝,飛濺起肉末和碎骨,他們砍一會兒就坐下喝酒吃肉,酒精熏熱,每個人的臉都紅彤彤的。

入夜后的帳篷已然成了肉的海洋。
日落西斜,將肥胖的莢狀云染成了藍紫色,氣溫急轉直下,永不熄滅的爐火蒸騰起草地上的水珠,堆積成一片平流霧覆蓋住帳篷的上半部分。我們的腦袋藏在流動的水霧里,什麼也看不見,牛奶的香氣、脂肪的香氣、草地上百里香的香氣卻似乎能在眼前霧氣的每個空隙中伸手觸摸,以可明狀的形態出現在眼前 —— 牛群在草地上奔向天空中的云朵,在云里跳舞。

夜晚九點,帳篷內的爐灶仍在熬煮著牛羊肉。
跳舞,是布里亞特人婚宴的主題。
幾個世紀以來,為了逃避驅逐和戰亂,他們中的一小支由貝加爾湖畔一路南下定居錫尼河畔,保留了古蒙古最傳統的婚宴形式。比如說,婚禮這日,我們十點又回到東蘇木哈日嘎那嘎查(內蒙古地區村級行政單位)新郎達西高恩普拉的家,他的朋友們立刻將他帶走了。
帶去哪兒?帶去藏起來。在新娘到來的時候,新郎不能被新娘發現,這完全是與漢族相反的待遇呀!一輛輛遠道而來的車開進來,越來越多的尖頂毛氈帽出現在我們面前,男人系帶在前頭,女人系在后頭。每個人都鄭重其事,換上了華麗的袍子,或綠色或黃色的腰帶上用細鏈條懸掛著蒙古刀,我們被各色形態的配飾和服裝招呼得應接不暇。見面時,他們摘下小帽子,向前彎腰,攤開手臂以示禮節。最尊貴的遠方客人被請去后方的蒙古包內,前方的草地上已經搭建好一圈桌凳。昨日的帳篷里擠滿了人,喝奶茶、吃果子、吃西瓜、吃肉、喝酒,聚會已經開始!有人在乎新郎去哪兒了嗎?沒有人,新郎在哪兒都影響不了大家快活地喝酒吃肉!

頭戴羊毛氈帽的長者。
如果說漢族人可以將新娘藏在一扇扇門后頭,那麼在草原,藏新郎的地方可就深奧多了 —— 他正在家對面遙遠的草坡后,驅車半小時的距離,與兄弟們坐在草地上看風、看云、看牛兒吃草 —— 這片草原被布里亞特人擁有,蘊藏著無窮的浪漫。
直到下午一點,四位牧民騎著馬又牽著四匹馬去到五公里開外的路邊迎接新娘薩仁格日樂。她站在草地上,比前日晚上在酒店的舞會要精神百倍,姣好的面容笑出了褶兒,她是該笑,燦爛的笑容中不帶一絲猶豫和想象空間,那便是她全部的心情。她頭戴釘有貂皮的尖頂紅纓立檐帽,帽頂象征太陽,帽纓象征陽光;身著藏藍色開襟長袍,鑲有金色襟邊;帽檐下垂掛著一條鑲有珊瑚的銀環發飾,走起路來一擺一擺的,丁零當啷作響。那匹白底棕色斑點的珍珠馬便是她的坐騎,她與姐妹一起蹬上馬背,在草地上拍攝與家人的合影。而后,眾人策馬奔騰朝著盛會的方向駛去。

牧民騎著馬去公路旁的草原迎親。
下馬,新郎的一位新婚女性朋友出來迎接,牽著新娘與 8 位伴娘走向草地,手牽手,銀飾垂蕩,發出悅耳的鈴鐺聲。送親女子從她們的服裝就能看出不同 —— 不像未婚女子為溜肩長裙,已婚女子的袍子上,肩膀密褶聳起,配有坎肩和分割式長袍。布里亞特人有這樣一句諺語,「別讓天空看見你的頭頂,別讓大地瞧見你的后背」,穿坎肩和戴帽子融入了布里亞特人對天空和大地的尊重。
草地上,男女客人圍繞一個圈分邊而坐,由北向南按年齡從長至少向邊緣分散開去。中間的草地上,分放著一盤又一盤的手把肉,男人吃肋骨、頸椎、脖子、肩膀、前腿、腰以上的肉,女人吃胯骨、后腿及腰以下的部位。每一桌還有用臭李子、奶干、砂糖、磚茶茶水、紅棗、葡萄干混合黃油和面粉,加入米飯、列巴丁、油餅、藍莓汁制成的八寶飯,底下墊著炸果子和千層糕,四周搭配上糖果。涼菜還有涼拌拉皮和水果拼盤,奶茶要多少有多少,酒水卻是明文規定,不允許在白天的婚宴中出現的。

女性坐在場地左側,并由長至少向下分坐。
室內,薩仁格日樂與伴郎、伴娘圍坐新房客廳,桌上是新郎的嫂子準備了一上午的西式餐食,新郎的一雙新婚朋友為遠道而來的客人斟滿酒水,口中高喝著歡迎詞,眾人便將杯中酒一飲而盡。4 位伴郎跟著草地上的音樂唱起了布里亞特民歌,每干一杯酒,就唱一首歌,從《錫尼河布利亞特》唱到《出嫁歌》,一人的歌聲很快變成一屋子人的歌聲。薩仁格日樂在歌聲中前往臥室換上一套黑底暗花細絨的婦女服飾,雍容華貴。她坐在椅子上,開始行「分發儀式」,分發人是三位兒女雙全、婚姻幸福、健康長壽的新娘長輩,她們將一根辮子解開,從正中分開,編織成兩股辮子,在發梢處戴上傳統的布里亞特發飾 —— 托依卜(布里亞特語為 tʊiβ,發辮套飾,飾兩腮頰旁側,由黑、藍、紫、深綠、咖啡色等縫制),這代表著一位少女向已婚少婦的轉變。

提供給新娘與伴娘的食物更加豐盛精美,有布里亞特包子、雞肉卷、拌菜、牛羊肉、水果拼盤等等。
年輕的已婚女子再一次牽起新娘及伴娘的手,帶領她們走出新房,進入儀式主場地,按照太陽公轉方向轉一圈,主持人向來賓問「新娘漂不漂亮」,來賓大聲呼應「漂亮、漂亮」,轉完圈后她們在東北角的桌子邊坐下喝茶,接受新郎長輩饋贈禮物。收禮儀式完成后,她們再次手牽手進入新房。
發現沒有,直到這個時候,新郎都還沒有出現!

新娘與伴娘手拉手,繞場轉圈。
再一次見到他是在新房內,他突然地出現了,滿臉紅光,帶著微醺的酒氣。新娘在人群中一眼就瞧見了他,瞬間喜笑顏開,親昵地上去擁抱。他們牽著手,走入草地,今天第一次以夫妻的形態出現在大家面前。主持人從雙方的姓氏家族,再一次鄭重地介紹了兩位新人。接下來,就是祝福儀式,主婚人、雙方父母、各個年齡段的親戚長輩依次前去草地拿起話筒送上祝福,這個環節進行了 50 多分鐘。儀式結束,新郎與新娘繞著草地又轉了一圈,與此同時,主持人向來賓高呼「新郎帥不帥」,眾人呼應「帥、帥」。
等新人轉完一圈后回房,換下隆重的禮服,穿上一身尤為好看的青綠色長袍,恰好與草原悠遠的青色相呼應。新娘的耳飾發出銀鈴的聲響,新郎的腰上別著一枚來自深海的天王寶螺,上面用細鏈懸掛著一把雕花蒙古刀,低低垂著,走路時輕輕拍打著長衫。我問,能不能拔出刀來給我看看呀。兩人被我的要求難住了,都說,不好當人面輕易拔的。我好奇地追問,什麼時候能拔呢?夫妻倆誠懇地解釋,要吃肉的時候才拔呢。

新郎與新娘換上敬茶長袍。
夫婦二人整理完衣服,白凈的圓臉上笑出了幸福的細褶,他們雙手緊握走出新房,一左一右分別向來賓敬茶,每位落座的客人都要倒滿、敬上 —— 這是最后的儀式,走完整個場地,已經是下午四點。客人們陸續散席,騎馬的、步行的、騎摩托車的、開汽車的,他們駕駛著不同的交通工具駛離這片陽光普照的草地。
但,這還遠沒有結束。
我說過的,跳舞才是布里亞特人的主旋律。落日時,煙花噴射入天空,當音響、燈光發射出電子音樂迷幻的律動時,隨之而來的,是牧民將一罐油高高潑向高聳入云的松木篝火,火舌四射,眾人狂舞,跟隨電音蹦跳甩頭。當音樂緩和,換作布里亞特民歌時,他們一邊拿著酒瓶,一邊擁抱身邊的男男女女,眼神赤裸,姿態純真,盡情旋轉、扭動、跳躍,寬大的肩膀、健碩的大腿,配上豐滿的胸臀、傲人的腰肢,皮膚與皮膚相親,酒精與酒精碰撞,興致高起,放聲高唱 —— 這時候的求偶就真的是求偶,看羽毛、看歌喉,觀察舞姿,體察眼神,一切都與愛情有關,一切都有荷爾蒙的參與。

草地上跳舞的新婚夫婦。
音樂減緩,他們披上長至腳踝的防寒長袍,高大的身影在熾熱的篝火下走向蒙古包前的長桌,繼續喝酒吃肉。幾百箱啤酒堆砌在角落,女人的面龐印出一朵朵暈染的紅,像夕陽下草坡頂上的山丹花。有人前來桌前邀請每一位女性跳舞,是一位年長的牧人,他喝多了,不盡的舞蹈都解不了他的酒精,他蹦蹦跳跳、手舞足蹈,時而惆悵、時而歡笑,圍著篝火,邁著輕盈又寬大的步伐,仿佛腳下有云,一步步沿著篝火向上攀沿至頂尖,放聲高歌與狂舞。在這里,每個人都相信愛情 —— 即便是七八十歲的老奶奶,四五十歲的大叔也依然會醉倒在愛人的舞懷里,在暗夜,在飛蟲形成的一片雪花中,搖動起臂膀,旋轉起裙擺 —— 這便是「我愿拋棄了財產,跟她去放羊,每天看著她動人的眼睛,和那美麗金邊的衣裳」。

燃燒不滅的篝火。
凌晨四點,一層寒露覆蓋大地、長袍、氈帽與睫毛,躺在草地上的醉漢被抬入車內。迷瞪的目光里,對面山頭的一點點光和似有似無的牛鈴聲從遠方透了過來,一條狹長的玫瑰色薄霧像輕紗籠罩在村落與山巒之間,這是一場盛大的浪漫,夢醒后,一切都安然無恙又充滿喜悅。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6064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