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云新作名為《一日三秋》,聽書名不免想到他三十年前的作品《一地雞毛》,小林那個經典的夢:“夢見自己睡覺,上邊蓋著一堆雞毛,下邊鋪著許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軟舒服,度年如日。”雞毛飛過三十年,是當年度年如日的小劉變成了一日三秋的老劉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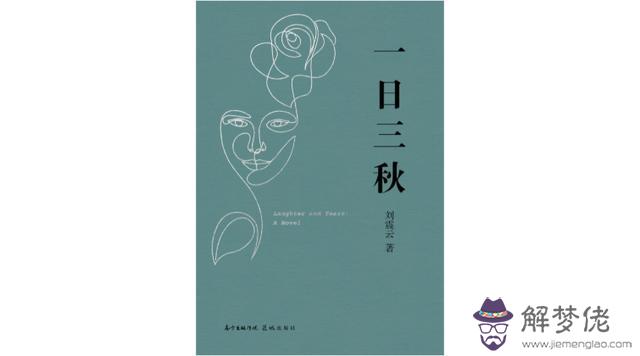
《一日三秋》,作者:劉震云,版本:花城出版社,2021年7月
一日讀完,我也頓生三秋之嘆。小說源于六叔的畫,六叔生前畫出延津的物態人情,可惜無人欣賞,只有寫小說的“我”能說的著。六叔死后,畫也灰飛煙滅,“我”就憑印象和想象用文字把六叔的畫勾連起來,構筑成這部小說。如果說六叔的畫如同《清明上河圖》,那“我”的故事就像超現實派畫家夏加爾的油畫,都是現實中人,沒有翅膀,卻可以飛升至半空,特別如夢之夢。
故事從花二娘的傳說起筆。花二娘是活了三千多年而不老、一直在延津人夢中找笑話的女子,延津人睡前都得備好笑話,以防花二娘入夢。笑話好笑,能得到二娘賞的紅柿子;不好笑,命就在夢里沒了。“我”把二娘從三千年前帶到現世人間,就在小說中隱身了。櫻桃、陳長杰、李延生、老董、陳明亮、馬小萌、孫二貨……半個世紀中、兩代延津人悉數登場。他們有唱戲的、算命的、開火車的、燉豬蹄的,他們中的一些人背井離鄉,在武漢、在西安安身立命,從離開的那一刻起,故鄉就已成為回不去的地方。
如果故事僅限于此,就是另一部扎根大地的《一句頂一萬句》。《一日三秋》宕開一筆,除了寫人間往事,還有神、鬼、畜的故事。花二娘是神,她盼著與花二郎團聚盼了三千多年,由“望郎”變成“忘郎”,日日飲笑話而活,卻也是為了附在自己身上三千多年的神秘人。櫻桃是人,因一把韭菜和老公陳長杰絆嘴之后上吊變成鬼,魂魄一度附于她曾在豫劇中扮演的白娘子劇照里,之后借李延生的身體找到背井離鄉的老公陳長杰和兒子陳明亮,最終穿越回到宋朝。小黃皮、孫二貨、中年猴子,還有那只被山神奶奶懲罰變成耕牛的貓,都是畜,卻極富人情味,它們不為索取笑話,似專為賺人一捧眼淚而至人間。算命的老董可以用“直播”讓人與鬼對話,他是瞎子,卻能摸骨而知人前世。老董幾十年來摸骨摸傷了心,摸過的幾千個延津人上輩子都是畜,唯有郭寶臣上輩子是個總理大臣,此生卻在人間掃大街;兒子有出息在英國定居,前世的總理大臣卻在現世到老年癡呆了也沒能去英國探一回親……
畫里畫外、戲里戲外、夢里夢外、神界鬼界、故鄉他鄉、歷史當下,這六重矛盾都在幽默這個大旋渦里撕扯捭闔,比夏加爾的油畫還超現實,小說成為一個六面體的魔方。
經典文學作品中的人鬼陰陽兩隔,夢中相見,多有情緣未了。如《牡丹亭》云:“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而在《一日三秋》中,人鬼殊途還在于“有趣”或“沒勁”這一念的起滅。延津人的幽默是因生命之虞,笑話沒勁,人就變鬼了。櫻桃上吊實因婚姻三載生活沒勁,夢遇二娘自然講不出有趣的笑話,不待二娘動手,自己先上了吊。而要轉世為人,難也不難,閻羅有新政,攢夠五十個一句話的笑話就可以了。真所謂沒有什麼是一句笑話解決不了的;如果有,就五十句。

劉震云。圖片來源:IC photo
難道,在劉震云看來一句頂一萬句的話,已經從“說的著”的話變成“笑話”了嗎?明亮的生父和養父都說過自己活得失敗,把自己活成了笑話。可見這笑話并不是老劉的一句之意。《一句頂一萬句》中,十八歲的楊百順在殺人與不殺之間感慨:“世上的事情都經不起推敲,一推敲,哪一件都藏著委屈。”《我不是潘金蓮》中,潘金蓮發現懲罰一個人,有比殺了他更好的辦法——大鬧一場,“不是為了顛倒這件事,是為了顛倒事里被顛倒的理。”到了《一日三秋》,老劉似在借著年近半百的明亮之口說:“活到這個年齡了,想起過去許多糟心事,當時樁樁件件,都覺得事情挺大,挺不過去了,現在想想,都是扯淡。”年齡變了,或者說,看世界的角度變了。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向外尋求不到“說的著”的人,于是向內反觀自己,好笑,不是幽默;笑話里要加了委屈、加了無奈、加了糟心、加了死去活來、加了上窮碧落下黃泉,還能笑出來的,才是有質感的幽默。真正能反求諸己的那一日,人生也到了天涼好個秋的季節吧。
在小說魔方中,作者借客人之口把“一日三秋”的時間魔法扭轉為空間魔法:“在這里生活一天,勝過在別處生活三年。”引申來說,即故鄉一日可抵他鄉三秋。然而魔方中的故鄉也并不可親。二十年前明亮離鄉是因為故鄉流言的可怕;二十年后再回故鄉,夢見了花二娘,因自己講的笑話又覺被故鄉逼得無恥,“什麼叫笑話,這才是笑話呢;什麼叫故鄉,這就叫故鄉了;不禁感嘆一聲,在心里說,延津,以后是不能來了。”故鄉一日逼人在他鄉度過三秋,幽默中含了羞恥。
小說中的三次空間的離鄉,是因為三場死亡:陳長杰離開延津去武漢是因為櫻桃上吊;陳明亮離開武漢回到延津是因為奶奶去世;再次離開延津去西安是因為妻子馬小萌上吊——萬幸的是馬小萌被明亮救下了,她的死卻是大型“社死”現場。面對親友之死,生者并不無辜。關于櫻桃輕生,陳長杰父子在多年后有場花園長談,明亮方知父親和自己一樣,認為是自己間接殺死了櫻桃;馬小萌的朋友香秀上吊,明亮也和馬小萌一樣,認為是自己拒絕她來家里成為壓倒香秀的最后一根稻草。死者死矣,生者流亡他鄉,從此鄉愁被覆蓋上原罪,幽默中含了淚水。
叔本華說過:“每一次離別都是經受死亡的痛苦。”錢德勒在《漫長的告別》中說:“告別就是死去一點點。”劉震云以笑話之名,給“社死”和流亡他鄉的人以新生;也以小說之名,給生者以再見死者的可能。雖然郭寶臣與兒子這對父子在現世無緣再見,但在奶奶的“噴空”里,奶奶終是見到了死去多年的爹的背影;老董去世前對兒子說,下輩子某一天,他會在一個火車站與兒子再見一面;馬道婆選定了少年明亮在四十年后拯救了已是孤魂野鬼的自己……三秋盡頭,成為初春。
這些超現實的設定,讓畫里在畫外新生、戲里在戲外重塑、夢里在夢外實現、神界在鬼界呼應、故鄉在他鄉消隱、歷史在當下復活。僅憑幽默之力是絕無可能把這六重矛盾的魔方復原的,一切皆因這幽默的背后,是等量的慈悲。
作者|張二嬸
編輯|張進
校對|陳荻雁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6043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