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靜(首都師范大學教授)
在《人間世》篇解釋“心齋”時,莊子有“三聽”之論:“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在此,莊子提出了認識世界的三種方式。“三聽”之中,若假以笛卡爾以來的主客二分或物質精神二元,將“聽之以耳”“聽之以心”作感性和理性之分,倒也是不難理解的。但問題在于,“聽之以氣”實非感性理性二分之所能范圍,又作何解呢?現當代以來,一些學者在百余年西學影響之下,普遍視感性理性二分為當然,對“聽之以氣”這一類悟性認識則頗為生疏,而這恰是中國固有傳統中極具民族文化特質的部分。
我們認為,莊子“聽之以氣”之所以值得重視,不僅僅在于這是莊子氣論思想的一個核心命題,反映了先秦諸子之學在認識論上達到的一個高度,同時,這也是上古政教一體傳統的遺存,是戰國以降以氣學為中心的感應思想興起的時代表征。
古人重“聽”。在目前所見的早期文獻中,“聽”與“圣”“聲”“氣”“樂”之間有著密切關聯。譬如馬王堆帛書有“聽者,圣之藏于耳也”“圣者,聲也”(《五行篇》《德圣篇》)的說法,參之漢人的相關論述,如《白虎通義》《風俗通義》等,亦可印證,皆強調圣人聞聲知情、條暢萬物、通于天地。所以郭沫若先生認為,古代的“聽”“聲”“圣”為同一字(《卜辭通纂·畋游》)。究其根源,“聽”之所以理解為“圣”“聲”,是建立在春秋以來氣化宇宙觀的基礎上,這是三代以來重要的思想傳統。
在上古樂官制度中,“聽風知政”的傳統一以貫之。從《國語》的相關記載可知,作為神人中介的盲瞽樂官,其重要職責就是省風、辨音、知氣,也即察節氣、協農事、成萬物。在古人“聽風知政”的政教邏輯中,“聽”之要義,在于測風聲、辨音律,察時節之和與不和,以此判斷是否適于農業耕種,所以韋昭釋為“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這是與民眾安居樂業、時運氣數乃至王朝興衰密切相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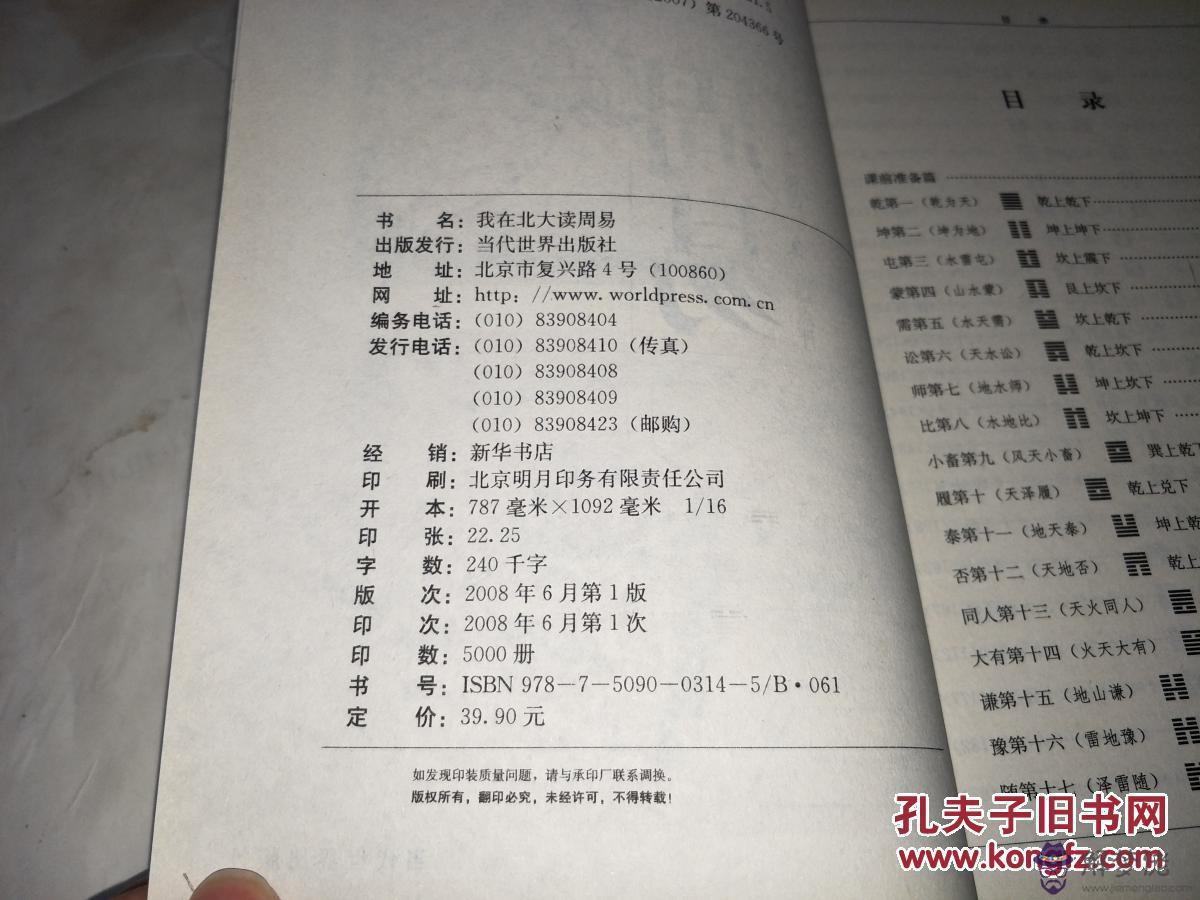
戰國以降,在天下一統思想的召喚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易·乾·文言》)一類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感應思想興起。我們從《周易》《禮記》《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等著述,以及孟子、莊子、荀子等人的談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這是當時思想界頗為流行的論調。這種發端于聲音感應和氣化感應的言說套路,不僅用以察人事、明天道,而且用以解釋天人關系、人人關系。作為時代公共話題的“感而后應”,孟子、荀子所針對的是人性、人欲問題,莊子所探究的是體道、達道問題,而稷下博士回應的是南面君術問題。譬如在闡釋樂教思想時,荀子以為樂之于人心的影響是以感應的方式表現出來。在比較了“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和“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荀子·樂論》)的不同結果后,他強調“制雅頌之聲”,如此“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方能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莊子將知識分為兩類:意會的、言傳的。對于兩種知識的不同,莊子在理論上有完整的表述和精謹的論證。《天道》篇:“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為了把這個道理說明白,莊子接著舉了“輪扁斫輪”的例子。在工匠做車輪時,榫眼松緊會導致松滑或滯澀,而松緊適當這種手藝,“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莊子·天道》),莊子稱之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不知之知”(《知北游》)。這種“不知之知”,不同于“無知”的狀態,也不同于“知”的狀態。對此,馮友蘭先生認為:“‘無知’與‘不知’不同。‘無知’狀態是原始的無知狀態;而‘不知’狀態則是先經過有知的階段之后才達到的,前者是自然的產物,后者是精神的創造。”(《中國哲學簡史》)這種“不知之知”,不可言傳,但可感可知,由低層次的“知”到高層次的“不知之知”,最終旨歸便是知道。莊子此論,不僅揭示出人類傳承的兩大類知識中,“意會知識”和“言傳知識”的根本不同,同時,也自根源處闡明了古人知識構成、思維模式、言說方式乃至審美心理形成的因由。
莊子舉的這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其實,不僅僅是“輪扁斫輪”,很多傳統技能、手藝以及一些技巧性運動,乃至于文學活動中的想象、靈感及鑒賞等,大都需要身臨其境、設身處地,憑經驗、直覺、技巧來把握,均呈現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特性,這構成了中國古代知識系統生成的一個重要特征。
那麼,如何解決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這一認識論難題呢?古代圣賢的解決之道各不相同。與儒家人文教化的法子不同,老子有“歸根”“復命”“知常”(《老子》第十六章)的路徑,而莊子開出的方子,則是“心齋”“坐忘”。
莊子以“心齋”為例,將認識分為三步:第一是“聽之以耳”的感性認識,第二是“聽之以心”的理性認識,第三是“聽之以氣”的悟性認識(龐樸《中國文化十一講》)。莊子所論的“心齋”,以虛為要,專一心志,拒絕感性刺激(“無聽之以耳”),排除心緒雜念(“無聽之以心”),凡感覺、思慮、意念均停止(“聽止于耳,心止于符”),在這種自然而然、聽之任之的狀態下,始能集氣于心,氣與道通(郭象“虛其心則至道集于懷也”),于不知不覺中進入虛無澄明的境界。由此觀之,“心齋”是悟出來的,既不是“聽之以耳”感覺到的,也不是“聽之以心”理解到的,而是“聽之以氣”體悟到的。莊子借助于耳、心,而達于氣、通于道。這種“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狀態,也就是道與人合一的境界。莊子此論,由靜而心、由心而氣、由氣而萬物一體。如此這般,獲得的認識才是最高的。
莊子認識論的精華,在于“聽之以氣”命題的提出。那麼,為什麼莊子要借助于氣論來詮釋認識論上的難題呢?這還涉及三代以來源遠流長的氣學傳統。
就現有研究成果而言,古人氣學思想的衍生發展,在春秋時期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知識斷層與思想斷裂(小野澤精一等《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和人的觀念的發展》)。由于關鍵性考古證據的缺乏,目前無法呈現出一條清晰完整的脈絡來。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戰國以后,產生于不同歷史時期的氣論,如物理之氣、天地之氣、生命之氣、生理之氣、心理之氣、精神之氣、倫理之氣、道德之氣等共時性地繁榮起來。在諸子各家的思想中,氣論不僅顯現為治氣養心之術的形態,而且成為自然哲學的基質概念以及理解精、神、形、質等問題的基礎,同時,還在宇宙生成論以及政治領域的“天人感應”思想中發揮作用,成為中國古代學術發生期一道獨具特色的風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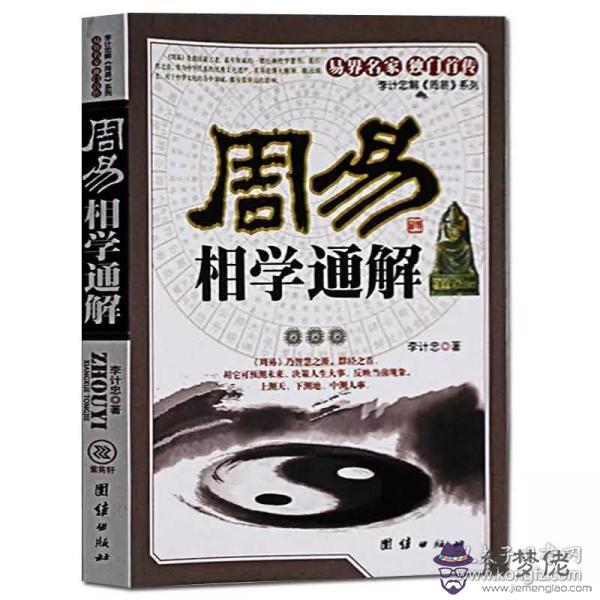
莊子氣論,面向有二:一是萬物本體及其達致途徑,一是審美境界及其超越意義。這涉及莊子對“道氣”“神氣”“虛靜”等概念的論述,以及圍繞“聽之以氣”“圣人貴精”“圣人貴一”等命題的闡釋。作為一個觀念性的語素,莊子之“氣”被賦予“陰陽”“一”“純”的含義,在思想建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從“通天地一氣”“道通為一”“萬物一也”等說法來看,莊子持“道氣同一”的觀點。更深一步看,作為一種“純氣”狀態,“虛靜”“心齋”“坐忘”“凝神”則是達道的唯一途徑。在這樣的理論預設下,莊子并不認同老子尊陰貶陽的觀點,而是主張氣之陰陽“相照相蓋相治”(《莊子·則陽》)。在他看來,只要秉持萬物一體之心境,順天而行、以天合天,方能與氣相合、道氣合一。人人如此,則天下大治。
莊子“聽之以氣”,影響深遠。限于篇幅,簡述三點:其一,這是中國式意會體悟認識方式的經典表述。中國式的意會體悟沒有本體與現象的差別,而是以天與地、陰與陽、兩與一、神與化、體與用的統一為基本特征,以整體的形式昭示其存在,并且與現實人生渾然一體,須臾不可分。這是中國古代知識生成的基本路徑之一。許多現代科學知識無法解釋的現象,如直覺、靈感、頓悟、冥想等,以及感覺、知覺、理智、聯想、情感、意志等觀念性、精神性的認識過程與審美體驗,均可以在意會體悟的框架下重新得以理解。其二,“聽之以氣”是一種氣化的悟性思維狀態,旨在忘卻現世之是非得失、功利欲求與意志努力,消除主客、物我之差異,“離形去知”“虛而待物”,以靜澈澄明之心體悟天地之道,以本元之氣(尚未進入人知行過程的存在)與天地自然之氣互動化生,使心靈活動達到極純粹的境地,這是對價值主體人格所能達致生命至境的深度認同,也是重返整體性意義世界的重要方法。其三,藝術價值的根源,在于虛靜澄明之心。純客觀的存在,本無境界高下,伴隨著價值主體此心的敞開,進入虛靜澄明之境,其價值理想與精神品格便自然投射于審美對象。莊子虛靜澄明之心,就是一個藝術的心靈(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我們不難發現,自魏晉起,中國偉大的藝術家都是在虛靜澄明之心下從事創造的。唐代畫家張璪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譯注》),便是一言概括了中國傳統藝術理論之精髓。就此而論,莊子功莫大焉。
《光明日報》( 2021年07月26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5712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