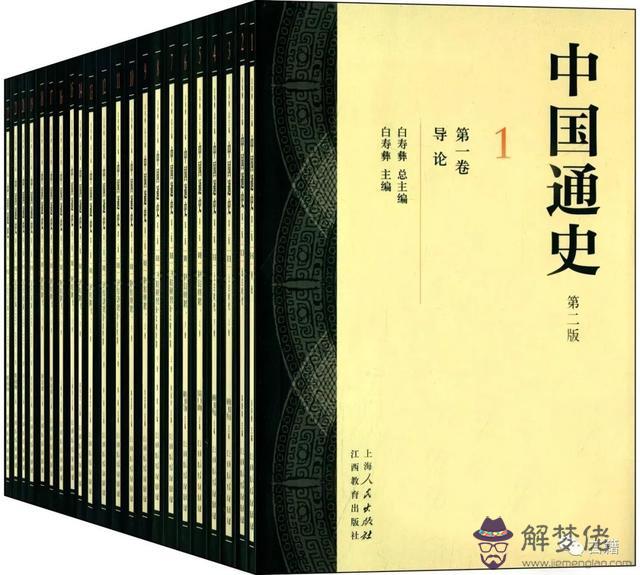
中國史籍,浩如淵海,初學入門,莫知所從,故通史之作尚焉。近年以來,應此需要以專纂著者,不乏其人,茲就最流行者數種,稍加撮述,著其梗概,以為介紹。庶于讀者需擇之際,不無裨助,是則述作此文之意也。
一、《中國古代史》(夏曾佑 著)本書原名《中國歷史教科書》,撰于清光緒季年,乃供中學教本之用。上冊止于隋代,是即本書,下冊未成,商務印書館列為大學叢書,改稱今名。清末西洋新史學觀念輸入我國,此為著者本此見地編纂之第一部通史。篳路藍縷,雖未臻于理想,然其觀點、取材及編制諸方面,迄今仍不失其為優長也。本書分我國從古至今為三大時代:自草昧以至周末為上古之世,自秦至隋為中古之世,自唐至清為近古之世。又細分為七小時代:由開辟至周初,為傳疑之期;由周中葉至戰國,為化成之期;由秦至三國,為極盛之期;由晉至隋,為中衰之期;唐室一代,為復盛之期;五代宋元明,為退化之期;清代為更化之期。每時代之中,于其特別之事加詳,而于普通之事從略,蓋欲“文簡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以供社會之需也。如言古代,即詳于神話,周則詳于學派,秦則詳于政術。此種分期及詳略方法,可謂開我國史界之先導。著者之述國史,極具時代眼光,如稱清代為更化期,其釋曰:“此期前半,學問政治,集秦以來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開秦以來所未有。此蓋處秦人成局之已窮,而將轉入他局者,故謂之更化期。”識見可謂銳敏!又本書不受前人成見之拘束,選擇史料頗為精審;而尤以能用綜合方法治史為最可貴。如辨桀紂之行事一一相同,必出于附會是也。著者又第二篇凡例中,言其所重:“總以發明今日社會之原為主。文字雖繁,其綱只三端:一,關乎皇室者,如宮廷之變,群雄之戰,凡為一代興亡之所系者,無不詳之;其一人一家之事,則無不從略。……一,關乎外國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類,事無大小,凡有交涉,皆舉其略,以為代表。一,關乎社會者,如宗教、風俗之類,每于大變化時詳述之,不隨朝而舉也。執此求之,則不覺其繁重矣。”二、《中華通史》(章嵚 著)本書作于民國三年,乃融會日本與我國史論之精神,而以新觀點撰成者。內容共分四編:甲編為上古,乙編為中古,丙編為近古,丁編為近世及現代。首列導言,于國史之地、族、系、時、政、民,皆加詮釋;凡一切術語之當先事說明及歷代總表之必須首為羅舉者,均為列入,以見眉宇。其于歷代之官幣,幣制、稅制、兵制、法制,以及文學、史學、天文、醫術、雕刻、音樂、宗教、風俗等,凡足瞻先民活動之梗概者,皆能條分縷析,予初學以明確之觀念。至其對于史料之采輯與征別,態度亦尚謹嚴。凡涉古代之難以確考者,則羅陳眾說而折中之;其于近時所難征實者,則搜稽信史而考訂之。參考中外新舊各籍,計達五萬余冊,可稱富贍;而于史類瑣記,子類小說之未易征信者,則一概不錄。尤有足稱者,著者自述其歷史觀念,乃欲由“君史”而進于“民史”,鑒于本書成于鼎革之后,固以契合時代新勢為其幟志也。三、《中華兩千年史》(鄧之誠 著)本書為著者在北平各大學多年講授之教本,原名《中國通史講義》;現列為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已出四冊,止于元界。據敘錄所言,本書在其體裁、取材及文字三方面,固皆具有特見。本書體裁,略依紀事本末之例,先之以世系,著明年代;稍及統系,以存通史之本義,兼使讀者得以與本書互相參校。次之以一代大事,尤重民族變遷,其無關得失,不必詳者則略之。次之以制度,制度為一代典則,不僅觀其因革損益,及政治良窳,實欲藉以測其影響于社會者安在。尤重地理官制者,讀史本以二者為基礎。次之以學術文學藝術,期以著學術之淵源,思想之變遷,亦以見時代遞變遞進之跡。終之以生計,以為讀史意義,根本在此。民族興亡,無不關乎生計之盈絀;今后經濟關系,或牽于外,或變于內,必更繁復,故欲參證史實,以一較其得失。至其所以造端于秦者,以秦以前六經即史。至說經偏于考據,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且遠古所謂三皇五帝之事,所得材料既渺,故遂毋寧付之闕如,亦竊比司馬光不作《通鑒前紀》之意。至秦以后,制度文化一貫,約而分之,則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夏元,明清,各為一時代,共厘為五卷。取材方面,首重正史,次及政書,次始及于雜史,再次始及于其他。著者以今人重視野史,而本書乃多取正史者,非謂正史以外無史,亦非輕信前人所信。誠以自來史職甚尊,斷代之書,所以累代不廢,即由無以相易。自唐修《晉書》,李延壽修《南北史》,多取瑣聞小記,宋人歐、宋之于《新唐》,司馬之于《通鑒》,采摭雜史,多至數百余種,此后私家撰述益富。然野史多尊所聞,沈括身在朝列,所紀宋事不實,遂為洪邁糾摘;明季野史,果一按其時地與人,則互相違忤,莫可究詰,故顧炎武以野史為謬悠之談,而萬斯同獨重實錄。正史為體例所限,往往不詳,且成于后人,自不能盡得當時真相;野史佳者,多足以補史闕;然正史據官書,其出入微;野史據所聞,其出入大;正史諱尊親,野史挾恩怨;諱尊親不過有書有不書,挾恩怨則無所不至矣。故取材野史,務須審慎。著者又謂今人治史多重金石,金石足貴,此亦誠然;然其所以足貴者,亦只官階、地理、姓名、世系、年月,或足以補證史闕,至于行實,恐其虛美。故以金石為旁證則可,若以金石為主,則著者以為稍過。他如實物及各種新發現,亦皆僅足為史證。蓋著者特重正史,以為果能細讀正史,亦可獲得新發現與新材料也。至于文字方面,著者以為紀古事而用今文,亦猶之乎紀今事而用古文,皆屬不當。史貴求真,茍文字改易,將必有所錯雜。追述古事,原文不當更易;若夫制度,更難以今文釋之。故其全書行文,均與近代文字距離較遠。總而觀之,本書對于民族消長,生計盈絀,紀之獨詳,是其最大特色。至于取材之必據正史,文字之必用古文,當待有所討論。然其所集正史之材料俱能提挈綱要,分類鈔集,凡政治、社會、文物之大端,無不條舉臚列,讀者茍加披覽,便可一目了然,實真本書之特長也。四、《國史大綱》(錢穆 著)本書為著者在北京大學教授通史之講義,屢經改訂而成。前有引論一文,洋洋萬言,述其認知國史之心得,極有價值,讀者不當忽略。著者謂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一曰傳統派(即記誦派),二曰革新派(即宣傳派),三曰科學派(即考訂派)。傳統派主于記誦,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為校勘輯補;革新派為有志功業急于革新之士所提倡;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三派各有其長短得失。而我國新通史之制作,則在利用積存之豐富歷史材料,以正確揭示今日時代所需要之歷史知識,亦如往代歷史不斷隨時代之遷變而有改寫之必要也。例如《尚書》為最初之史書;次有《春秋》為最初之編年史;又次有《左傳》,網羅尤詳,則為編年史之進步;又其次為《史記》,乃為以人物為中心之新史,顯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社會之團體性而嶄然露頭角也;又其次為《漢書》,為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后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繼而復生通史之要求。于是而有杜佑《通典》,此為政書之制作,為以制度作骨干之通史,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又繼而有《通鑒》,為編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以事件為中心的新史之再現;又次有鄭樵《通志》之《廿略》,其歷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譜,如學案,形形色色,乘一時代之新需要而創造體裁者,不勝枚舉。蓋自《尚書》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之敘述。觀其相互體裁之不同,與夫內容之差別,可知中國舊史,固不斷在改寫之中。惟自由南宋以后,乃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則因中經元清兩代異族不欲國人治史之束縛而衰息也。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為何?著者觀之,將為自《尚書》之下迄于《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且必須具備兩種條件:(1)須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2)須能于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復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癥候,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通史之制作,即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功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也。本書共分八編,總四十六章。一為上古三代,二為春秋戰國,三為秦漢,四為魏晉南北朝,五為隋唐五代,六為兩宋,七為元明,八為清代。至其內容所重,則為政治制度,學術思想與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中層之干柱。其于史上之輕重先后,著者稱其并,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只于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學術思想(例如先秦戰國),彼即著眼于當時之學術思想而察其如何演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漢),彼即著眼于當時之政治制度而察其如何演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社會經濟(例如三國兩晉),彼又即著眼于當時之社會經濟而察其如何演變。蓋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系也。本書積理甚富,創見特多,略去常談,指點扼要,足覘著者之好學深思,非只鈔纂陳文,泛泛言之作也。五、《中國通史簡編》(范文瀾 等著)中國史籍浩瀚,研習國史如由“廿五史”及《通鑒》等書入手,依本書著者之意,以為其事捍隔甚多,恐難獲得預期之效果。述其理由:“第一,這類包含千百萬字的大部書籍,學習者哪有這許多時間和精力去消費;第二,這類書籍連篇累牘,無非記載皇帝貴族豪強士大夫少數人的言語行動,關于人民大眾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記載非常簡略;第三,我們要探求中國社會循著怎樣的道路向前發展,而這類書籍卻竭力湮沒或歪曲發展的事實,盡量表揚倒退停滯阻礙社會發展的功業。一言蔽之說,這類書不適于學習歷史的需要。”據此,則本書之作,固錢穆所謂屬于革新派而以宣傳一種主張為其幟志者也。故著者言其著述之目的,乃在于“從廣泛史料中選擇真實材料,組成一部簡明扼要的,通俗生動的,揭露統治階級罪惡的,顯示社會發展法則的中國通史”。由于當前現實之思想斗爭,以至兵爭政爭,立場既有不同,故本書出版之后,贊否之詞亦大異其趣。然由純學術之觀點以從事于批判本書者,則以上海人文研究所所刊行之丁山先生批判一文,最為平正公允。丁氏以為本書確有后來居上之數種優點:(1)本書材料不是抄取雜志論文,或自坊間出版之通史,輾轉傳抄,偽以傳偽,雜湊成篇,而是后人所必讀之舊史料中,直接選錄。又本書取古代材料譯為現代語言,譯筆亦稱忠實。(2)近來編纂通史者,常犯考證學之弊,詳古略今,顯出頭重腳輕,本書則不如此。(3)本書分期,劃為三大階段:第一,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成立(遠古至秦);第二,中央集權封建國家成立后對外侵略到外族內侵(秦至隋);第三,封建經濟的發展到西洋資本主義的入侵(隋至清中葉)。此種政治經濟兼顧之分期,顯受蘇聯科學院歷史所編新歷史之影響,亦可謂中國新史之嘗試工作。(4)過去之史籍名著,茍非帝王家譜,即屬貴族教科書,甚少注意為人民生活寫照。即以時下通史專家而言,或注意政治人事之進退,或注意典章制度之沿革,當或空發其知今而不知古之策論,殊少能抓著古今人民生活而通觀其變化者。本書以人民生活為中心,由經濟基礎論到歷代的社會政治問題,斯實為吾人所應了解之中華人民史。然著者既持階級斗爭之觀念,而本書又適為一種宣傳之工具,故其甚深之主觀成見,往往亦造成偏激之理論,而于史實難以審合,斯則其顯然之失也。丁山并就本書擇舉數事,以為須待商榷。其一,就中國統治階級者之出身,用以檢討秦漢以來之歷史,隋唐以前,誠為封建社會,而宋元之后,吾人實當改稱為官僚集團時代。歷史之分期,應將秦漢至隋唐劃為中古,宋元明劃為近古;著者乃以隋唐為歷史時代之分界,似為沿襲夏氏歷史教科書史觀之誤。其二,本書于秦、漢、唐、元、明各代之末,莫不大書特書“農民大起義”,此則不能不謂為尋得中國問題之根本。蓋吾人由歷史上觀察及于現代社會,農工實為被壓迫階級,而士商則屬于統治階級。前者所謂“用力者役于人”,而后者則所謂“用心者役人”也。中國生產基礎,全在農業;農業基礎,則在土地與勞動時間。惟有所當知者:中國歷代領導人民以反抗統治苛政者,絕少屬于純粹農夫。秦漢以來,一般革命者,大抵俱為社會上游食之徒,輒于衰亂之世,利用官逼民反之機會,以冀圓其稱王稱帝之夢而已,其實心為人民謀福利者,蓋不數數睹也。吾人茍自人民立場言,此輩以暴易暴之野心家,豈值表彰?吾人所當贊誦者,實乃應為除暴安良之循吏,與夫舍身救世之豪俠也。農民本身,多如馴羊;孰執統治之鞭,彼則隨順其意而進,孰執屠刀,彼固向之乞命矣。中國農民由其千辛萬苦之儲蓄,以造就其微弱之私有財產觀念,并于中產生基本的生產動力;數千年來中華民族之生命實賴此支柱而不絕,統治者縱不欲加意保護,似亦不必以盡行摧毀為快也。故每代之興,先必重申“崇本抑末”之政策,雖間不免虛應故事,有名無實,然歷史之告訴:凡能使農民得其安居樂業者,未有不能把握百年以上之統治權也!是以對于統治階級似不必盡行仇恨而一律打倒,因時至今日,任何國家與民族皆尚未進步臻于不須統治者之可能也。本書對于歷代革命性的破壞描寫至為詳盡,而于積極的政治建設,消極的經濟建設,則敘述殊不著力。諸如西漢文景兩帝之儉約,唐初貞觀之治,皆能整飭吏治,藏富于民,由今視之,似應予以頌揚,不能以其為統治階級,便隱其善而揚其惡也。其三,關于民族對外問題,本書態度似亦失之偏畸。中國自來常受北來游牧蠻族之侵逼,如永嘉南渡,元魏飲馬長江,靖康之難,蒙古滅宋后之賤視“南人”,吾族所受外來馬蹄之蹂躪,其事豈鮮?而漢武帝之伐匈奴,唐太宗之滅突厥,明成祖之伐蒙古余裔,同為我族不勝塞外馬蹄之長期壓迫,乃取此攻勢的防御,本書不宜動輒加以“對外侵略”之罪名。試觀宋明兩代,以其國力衰弱,不能貫徹攻勢防御,即立刻遭受遼金之打擊,甚至演出土木堡皇帝被擄之丑劇,可以知其消息。民族自衛,不能采取攻勢,即不能良固封疆;是以唐太宗“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四夷”者,亦不過以吾族求取永久之安全保障而已,本書對之極多微詞;如此史觀,將不許吾族產生反侵略之英雄,寧不令人喪氣乎?反之,本書不以塞外馬隊之南牧為侵略;甚至對于帝俄在清初以來對我之侵略,亦略而不言,不免使人有回護過深之感矣。其四,本書對于孔學認識,既已輕淺,且又從而誣之。夫“仁民愛物”乃為孔子學說之中心(郭沫若著《孔墨之批判》,亦曾揭發孔子“人民本位”之理論),著者對此未有認識,乃于孔子思想行為,多予譏刺揶揄。如硬謂“孔子所謂天命就是君主專制,鬼神就是卿大夫”,厚誣前哲,誠屬非是。蓋孔子思想雖尚未能蟬蛻封建社會之軀殼,然其思想本體,乃以絕對整潔之精神,以建立其基于人民福利的政治主張,并無可以輕加非難之處。又黃宗羲“原君”之議論,明系導源于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民本思想。著者但稱孟子學說“頗有革命的意味”,而或贊“原君”為“透徹地發揮了民主主義”,持論未為公允。又理學二宗,陸王與程朱對立,前者屬唯心派,而后者屬唯物派。本書既充分發揮唯物史觀,獨于宋明理學,反對接近唯物論派的程朱學說,轉而表彰陸王派的唯心論,無可諱言,對其所守立場,實為一種矛盾。六、《中國通史綱要》《中國通史要略》(繆鳳林 著)前書為著者所用于南京中大之教本,幾經修改,網羅極富,舉凡王國維、羅振玉等之于古史方面之貢獻,以及近年來金文、甲骨、碑闕、封泥、簡牘等之發現與考定等類材料,均為其盡量吸收與應用,可謂詳博矣。著者于其《自序》中,嘗申論今日所需要之國史云:“高中與大學普通科之國史,以說明古今各方面之重要潮流,示國家民族社會文化政治演進構成之真相為主。可尋之國史遠其炎黃,近迄廿祺,紛紜繁復,不可殫論,而其犖犖大者,亦不過數十端:如唐虞三代為封建時代,視中央政府更易增損之國之多寡、王朝與諸侯天澤之譜及關系之疏密,諸侯叛服影響王朝地位之大小,即可窺見封建制度之實際,而五代之史,如網之有綱矣。東周為列國時代,強國代天子為政于天下,歷史之重心,不在王室而在列國,故諸侯制度,多模擬王朝,禮樂刑政自諸侯出,平戎御狄,興滅繼絕,聘問盟會,攻戰吞滅,開疆拓土,合縱連橫,皆列國事而非周室事。人才則諸侯盛于天子,學術則私學盛于官學,歷史則侯國詳于王朝,而馬遷、劉向、班固之所慨嘆者,皆可取之以解釋時代精神矣。秦漢隋唐為統一時代,故內則經濟富庶,物力充盛,國都之宏偉,宮殿之壯麗,交通之發展,帝王之靡費,皆反映社會之富力;外則國威遠揚,冠帶百蠻,疆土之開拓,夷狄之款貢,文化之傳播,商賈之懋遷,亦隨國勢而繁隆;余如方域之區處,官吏之分職,應統一之需要而規劃,帝王之權力,學者之思想,亦多與統一之國勢相應,而四朝之史,無不通矣。又如外戚之禍,與西京相終始,東京復益之宦官,詳戚宦之禍,則兩漢之史明矣,隋唐之政制顯矣。五代十國,多唐室節鎮之流裔,統論唐五代之方鎮,則蟬蛻之跡見矣。推之民生之休戚,風俗之變遷,典制文物之隆污,學術宗教盛衰,茍論其大而忽其細,亦皆可執簡馭繁,以表現其演進構成之總相。”繆氏本此見地,以成其書,分為四編:首編導論,略述史學之通義及國史之民族年代與地理;次編歷代史略,以說明各時代之潮流為主旨;三編政治制度;四編學術文化與宗教。每編分門論述,自太古以迄最近。說明今日各種現象之所由,及其蛻變之所以。凡所敘述,先通其大,標立節目。次就一己涉獵之正史、《通鑒》《通考》與百家傳記之書,旁及中東時彥論著,扼要匯錄。其所征引,多因仍舊文,而采錄最多者,則為顧氏《日知錄》,趙氏《廿二史札記》及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三書。著者立言態度,乃本傳統儒家明經通史之方法,以講微言大義。其言歷史功用,奉則知幾之說為圭臬曰:“古來言史之功用,未有如子玄之深切著明者。夫史之大源,本乎《春秋》,《春秋》據行事,仍人道,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居于新史學最為發達之今日,其議或失抱隘矣。又本書之被非難者亦有數事:是古觀念過甚,對于堯舜之禪讓,大禹之治水,信之太堅,曲為之說,致有過情失實之弊,又如以《周禮》為西周典籍,以《湯誓》《牧誓》代表當時之誓師詞,信《禮記》中之“子曰”真為孔子之言,信墨子之教果為夏道之傳衍等是之一也。本書雜引書文,繁若類史論,其書體乃于史料集與著作,兩皆非是,二也。又間有于所稱引之文,不以為然,而本身論斷亦欠明決,而失之含糊者,如引《日知錄》論共和事,三也。又本書以共和紀元,形同累辭,徒亂人意,四也(參《清華學報》八卷,一期,田義生評本書一文)。至著者主張我國種族定名,應表以切當之詞,謂“中華民國”宜改為“大黃中華夏民國”,即屬迂闊之一例也。本書共已刊行三冊,僅及第二編隋章五代章而止,約八十余萬言。抗戰后著者又有《中國通史要略》之作,分為三冊,計十二章。第一冊迄漢末,第二冊迄元末,第三冊迄民國。著者述其編纂《要略》一書之宗旨及用心所在曰:“史為人事之記錄,人事之演進,雖無前定之原則,就已陳之跡而察之,又若有端緒問尋,撰述歷史,首在尋得此端緒,一也。史文敘述,其事實皆有客觀的存在,言史者惟當以事實為依歸,實事求是,不宜先懷成見,尤忌向壁虛造,務求所言合乎人心之公,絕不能稍逞一人之私,二也。營阿房建章之宮者,張千門而立萬戶,若尋丈之基,止宜筑為環堵之產屋,大小殊則其制異也。十數萬言之課本,斷不能事事求備,要在別擇史跡之重輕,著其大而忽其細,必有所舍,乃能有所顯,三也。”以是《要略》《綱要》二書,宗旨雖同,而面目則異:《綱要》之史略政治學術,各自為篇,《要略》則每章成一完全之單位,義取縱貫,此不同者一;《綱要》體如讀史要錄,征引頗詳,《要略》則文多鑄,僅著大凡,此不同者二;《綱要》多考訂史實,辨析異說,《要略》則惟直敘正義,凡鉤索困難者,概付缺如,此不同者三。蓋《要略》篇幅之大事刪削,著者本在求其適于教課之用,此體例自不(得)不變矣。七、《中國史綱》(張蔭麟 著)張氏之為此書,乃不嫌于舊史之冗雜,對于讀者浪費精力,不足啟其愛慕興感;思欲以極簡潔的筆調,采熔鑄之方式,集合多人之力,以完成此一通俗之通史。其書不加腳注,不引原文,使人人習之,皆得易熟于史事。其計劃,漢以前由張氏自撰;唐以后則屬之吳晗;鴉片戰后的社會變化,則屬于千家駒;中日戰爭則屬于王蕓生,以其史事乃為諸人素習,容易貢獻其心得也。惟張氏英年早逝,厥志未成;僅其自撰《東漢前中國史綱》一冊刊布于世。八、《中國通史》《白話本國史》(呂思勉 著)呂著《中國通史》一書,分為上下兩冊:上冊以文化現象為題目,除緒論外,計十八章,為婚姻、族制、政體、階級、財產、官制、選舉、賦稅、兵制、刑法、實業、貨幣,衣食、住行、教育、語文、學術、宗教等。下冊仍依時代,述其大事,以便兩方兼顧。從十九章至五十四章,下冊計共三十六章。著者于上冊就我國文化之各方面加以探討,明其變遷之故,乃進而推求現狀之所來。敘述扼要,行文淺顯,多引各社會科學之成就,頗能裨補史識,而收文化史教科所要求之效用。呂氏早年有白話本國史之作,亦殊具特色:一為用語體文撰成,議論發抒,靈活自由,極便初學瀏覽。二為書中摘錄重要史料甚多,此種以原料示人之辦法,使讀者對于當時史事易得明確之認識。三為善用考據方法,往往可以發生新見解,增加讀者之興趣。惟騖新好奇,正亦著者之病,實證未充,貿然強說,向之所謂新奇者,且不免齊東野語之誚耳。例如漢族西顯發見西半球之說,皆無可成立也。三六,四,一六本文選自《吳天墀文史存稿(增補本)》(吳天墀 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原載《新中國日報》1948年4月18、19日。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5582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