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潭往事:原本山川,極命草木
本刊記者/宋春丹
發于2021.10.4總第1015期《中國新聞周刊》
20世紀30年代初期,云南邊陲瘴氣彌漫、人跡罕至的山地林間零零星星出現了一些形跡奇特的人。他們穿膠鞋,打綁腿,戴草帽,握著木棍撥打草叢,手持放大鏡仔細查探,剪下枝葉花果小心翼翼地放置在標本夾里。
這些當地人口中的“采花人”,就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中國植物學開路先鋒,一群試圖揭開“植物王國”面紗的人。
“游動的魯濱遜”
1932年,在位于北平西安門內文津街3號的私立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里,21歲的蔡希陶接到任務:率隊赴云南采集標本。
彼時靜生所雖然剛剛成立四年,但已是近代中國生物學研究的龍頭機構之一,全所分為動、植物兩部,動物部由秉志主持,植物部由胡先骕主持。受經費限制,靜生所羅致的人才名望不高,但都年輕有為。蔡希陶并非科班出身,大學輟學后通過其姐夫、中共早期黨員陳望道介紹進入靜生所。

(1932年,在云南怒江考察的蔡希陶(左)。本文圖/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約在1930年,胡先骕即籌劃與美國哈佛大學阿諾德植物園合作,開展對云南省的大規模植物調查采集活動,1932年正式啟動這一長達14年的基礎工程。采集的標本每號10份,有半數要歸入阿諾德植物園標本室,而該園未派一人來滇工作。
那時云南是個閉關自守的獨立王國,惡性瘧疾猖獗,民間有“要過潞江壩,先把老婆嫁”的說法(意即去了就回不來),因此內地人很多都視云南為畏途,更不要說去少數民族聚居區。蔡希陶登報招聘,錄取了四名成績優異者,但他們得知要到云南工作就全部告退。他只好另約了兩三個年輕學生一起出發,結果一人不辭而別,另一人也借故折回。
蔡希陶在四川宜賓碼頭遇到挑夫邱炳云,對方開始也不愿意,但幾天沒找到活兒,總算在蔡希陶的一再勸說和優厚的待遇下接受了。邱炳云后來一直在蔡希陶指導下學文化,也成了一名植物采集員,新中國成立后成為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元老之一,全所人都稱其“邱大爹”。這是后話了。
當時云南尚無一條通省外的公路,蔡希陶和邱炳云自宜賓徒步經鹽津到昭通,沿金沙江徒步到達云南,又向西折到大涼山,再從大涼山南下云南,直至中越邊境的河口、屏邊。
采集路上危險不斷,熊豹足跡比比皆是。蔡希陶淋雨后發高燒,被捆在簡易擔架上背下山。行至昭通,在地質學家趙亞曾被土匪殺害處,蔡希陶頓覺人類生命之渺小脆弱。
那時涼山地區是農奴制社會,有人專門販賣漢人“娃子”,抓住在逃的就釘上腳板防止再逃,令漢族人談虎色變。蔡希陶和邱炳云冒著生命危險在天雞街與黑彝奴隸主交結,大碗賭酒,喝牛血結盟拜把,才渡過這一關。
蔡希陶到云南后,做了三年“游動的魯濱遜”和“采花委員”,每天游走在深山密林之中,足跡遍及三迤大地。
為安全起見,他一般會隨馬幫而行。那時從下關到昆明山路崎嶇,關隘重重,經常發生搶劫,但可觀的腳價常常誘使貧困的趕馬人鋌而走險。
從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縣的官廳鎮到90里外的凹子,只有極其難走的“江坡單邊路”(即山坡懸崖上開辟的羊腸小道),騎馬也要十二分注意,一不小心撞到樹枝巖石就有可能掉到萬仞深壑里去。蔡希陶一行不敢騎馬,自清晨六時啟程,下午七時才到。
蔡希陶早已聽說“車佛南”(“車”指車里,今之景洪,“佛”指佛海,今之勐海,“南”指南橋,屬勐海縣,“車佛南”泛指西雙版納)物產富饒,地廣人稀,是個種一年吃三年的大糧倉,行至此發現名副其實,可稱植物王國之冠。
1933年5月他致函胡先骕:“山谷中木本植物叢生,竟著美麗之花果,生每日采集時,回顧四周,美不勝收,手忙足亂,大有小兒入糖果鋪時之神情。預計今歲總可獲六千號左右也。”
蔡希陶對少數民族的人情風俗、云南的虎豹野獸、當地體型矮小但擅長走江邊羊腸小道的毛驢以及這里特有的馬幫生活都很感興趣。霧蒙蒙的雨、鉛色的云、綠色的秧苗、人們栽秧時的唱調子對歌、在泥濘中跋涉、馬幫出發時龐大而井然的場面,都被愛好文學的他寫入小說里。
從1933年到1937年,他風餐露宿,跑遍了云南,北自巧家、昭通,南至西雙版納,東自文山、屏邊,西達保山、騰沖,先后在烏蒙山、碧羅雪山、高黎貢山、大圍山、老君山、金平分水老嶺、芒市、龍陵等地做了大規模采集調查,共采集標本12000余號(每號采10份),成果斐然。
1935年至1937年,王啟無率領靜生所第二支考察隊伍來滇采集。他的采集范圍廣泛,除高等植物外,地衣、真菌、蕨類無一不采,還采集木材標本。他曾在途中感染惡性瘧疾,每天服用金雞納霜,才幸免于難。
1937年1月,靜生所接受英國皇家園藝學會委托,代為采集云南高山植物種子。領隊俞德浚一行五人到麗江后分成三組,分別前往木里、中甸、阿墩子進行植物采集。
第二年,英國皇家園藝學會又出資400英鎊,與靜生所繼續合作,美國哈佛大學阿諾德植物園也出資600美元加入,仍由俞德浚率隊,規模更大。
俞德浚一行雇請了26名背夫運輸糧食,計劃六七日翻越高黎貢山抵達獨龍江,但途中遇雨,凍死了五位背夫。兩位向導中的一人不辭而別,所幸另一位向導、鄉長之子孔志清不離不棄。
孔志清是獨龍族里第一位小學畢業生,品性堅毅,白天帶領先遣隊翻雪山、過峭壁,晚上幫忙烘干標本紙,并積極學習漢語。采集工作結束后,俞德浚安排他到大理政治學校學習,還給予經濟資助。新中國成立后,孔志清成為貢山縣首位獨龍族縣長,1960年代他作為獨龍族代表赴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俞德浚不期而遇。他們的友誼保持了一生。
這期間,中國各植物學研究所幾乎都派員來云南采集,如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的吳中倫與中央大學的陳謀、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蔣英、廬山森林植物園的馮國楣、北平研究院植物學研究所的劉慎諤等。其中,陳謀是首位在采集途中犧牲的植物學家。年輕的植物學家們在云南共采得新植物1800多種,來自靜生所、有“四大采集家”之稱的蔡希陶、王啟無、俞德浚、馮國楣貢獻了其中的1400多種。
“桃源仙境”
1937年7月,北平淪陷,胡先骕計劃在昆明成立靜生生物調查所的分支機構。他與云南省教育廳廳長龔自知一拍即合,雙方決定合作建立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
胡先骕派蔡希陶入滇,負責籌備工作。蔡希陶經多番考察,認為黑龍潭是最適宜建所的地方。
黑龍潭位于昆明北郊龍泉山下,源出兩泉而分南北兩潭,南潭深邃清碧,北潭淺而渾濁,兩水相連卻不相混,清濁分明,蔚為奇觀。潭邊建有黑龍宮。民國年間,黑龍潭改為龍泉公園,以深潭碧水、唐梅宋柏、元茶明杉、舊觀古墓和楹聯碑刻聞名于世。
1938年7月,黑龍宮門口正式掛出了“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的招牌。所長由靜生所所長胡先骕兼任,從英國進修回國的汪發纘擔任副所長。

(1938年,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的辦公地點黑龍宮)
汪發纘來所主持后,請求云南省教育廳撥款兩萬元,又向其他機構請款一萬多元,在黑龍潭附近購置了苗圃及庭園用地,新建起了辦公室和陳列室。新建筑只有200多平方米,黑龍宮也仍舊使用。
新所址落成,汪發纘在《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叢刊》1941年第一卷第一期上撰文《本所之回顧與前瞻》,文中寫道:“黑龍潭外,溪流一碧,短垣半規,芊草綠褥,翠柏翁翳,廣廈翼然其間,景物幽然,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所址也。”
蔡希陶本擬在籌辦后即回北平,因戰爭期間“道阻未能北返”,就留在農林所擔任標本管理員,兼任龍泉公園經理。在云南采集的俞德浚等結束考察后也加入了農林所。
張英伯、王啟無等從北平靜生所來到昆明。剛來時農林所還在籌備階段,大家都住在黑龍潭的廟里。張英伯和王啟無兩個單身漢同住在大神殿中,每人行軍床一張,共用馬燈一盞。白天老道念經,他們打字,伙食自辦,粗茶淡飯,但那樣的歲月還能進行科研,大家都很滿足。
不久,張英伯的未婚妻鐘舒文從北平輾轉來到昆明。農林所為這對新婚夫婦準備了山半坡廟里一間廂房,非常幽靜。房前一叢松林,山坡一片野生秋海棠,坡下一潭泉水,院內有大樹茶花,紫薇盛開,如同天上人間。
靜生所所屬的江西廬山森林植物園人員也西遷來昆明,加入農林所。副主任陳封懷是陳寅恪的侄子,在英國留學時所學專業是報春分類,俞德浚的采集中僅報春一屬就有植物標本400號、種子標本130號。陳封懷經過研究,寫出了《云南西北部及其臨近之報春研究》和《報春種子之研究》,稱俞德浚的采集為“吾國報春采集中之最卓著者”。他在這批標本中發現了新種三種、新變種三種,并將其中一新種命名為“俞氏報春”。
王啟無與陳封懷的妻子張夢莊是清華同學,那時陳家住黑龍潭上觀,他住下觀,日日相見。王啟無1945年去美國深造,后定居美國,1973年曾撰文紀念張夢莊,并回憶起黑龍潭的生活。他寫道,上觀為漢之黑水祠,古木森森,正庭花木亦盛。張夢莊畫有一幅唐梅圖,胡先骕還為之題詩。那時陳家有一個極活潑的小男孩,常常嬉戲于泉林深處。“現在想來,在戰亂擾攘之中,實是桃源仙境也。”
1939年,王啟無發表了重要論文《云南植物組合之研究》。云南海拔高度懸殊,氣候各異,植物分布因之有較大差異。他根據在云南實地考察的結果,把云南植物群落分為14種類型,即極地植物、高山草原、高山灌叢、杜鵑林、柏樹林、冷杉林、樺槭混交林、苔蘚沼澤、松林、橡樹林、湖澤植物、河谷植物、熱帶雨林等。
王啟無還進行了云南松地理種源實驗,以驗證地緣因子和立地條件對其生長的作用。他從小哨移來10株地盤松,植于黑龍潭植物園內。1979年他從美國來昆明訪問,查看其手植松,有6株已長成參天大樹了。
所長胡先骕和第二任副所長鄭萬均是云南植物分類研究權威。他們合作研究云南的木本植物,新發現了很多植物新種,如云南七葉樹、云南紫荊、王氏短葉松、俞氏冷杉、求江枳椇。
經過幾年的積累,僅十幾人的農林所儼然已發展成名副其實的研究所,不但接納了一批又一批疏散而來的科學家,還建立了一個幾十平方米的展覽室和圖書館,陳列著他們出生入死采集來的幾萬號標本。那時農林所財政困難,但仍派出王啟無、劉瑛、馮國楣、張英伯等人到滇東南、景東、滇西北、烏蒙山等地采集標本。
一時間,黑龍潭成為中國植物分類學活動中心。時任西南聯大生物學系助教的吳征鎰回憶,每當帶學生野外實習時,黑龍潭農林植物所是必到之處,有時又是天然歇腳地和歸宿。
大普吉
除黑龍潭外,西南聯大也是植物學研究重鎮。
1938年時西南聯大生物學系經費較多,且助教充足,著名教授李繼侗、吳蘊珍、張景鉞等幾乎每周都帶學生去采集標本。
8月初,張景鉞和吳韞珍教授帶領一個六人的“綜合考察隊”,赴大理蒼山和賓川雞足山采集。盡管路途艱苦,整個小團隊卻甘之如飴。
吳征鎰回憶,蒼山中和峰上的洗馬塘是一個冰川湖,寒澈見底,杜鵑灌叢繁花似錦,冷杉林蒼翠欲滴,令人心曠神怡。
在雞足山,他們在金頂下的寶塔底層住了一星期,那里即使在盛夏也寒氣逼人。一星期中,吳韞珍不斷解剖觀察他每天采來的新鮮花草。周家熾和姚荷生一面畫水彩圖,一面烤蘑菇,香氣撲鼻。楊承元張羅伙食,照相,整理記錄他采集的各種苔蘚。吳征鎰采來各種野鳳仙花,畫解剖圖。

(吳征鎰(左七)率隊赴哀牢山選址。)
讓吳征鎰終身難忘的是親身領會了張景鉞老師的治學態度和為人風度。張景鉞不管在什麼境況下總是和顏悅色,說話輕言細語,制作一小瓶一小瓶的固定材料時一絲不茍,在野外用顯微鏡做預備觀察時細致安詳。觀察到入微入神時,平時寡言少語的他滿臉動情。
吳征鎰三年助教期滿,考入北大研究院,成為了張景鉞的碩士研究生。
1939年,西南聯大生物系也不再有經費支持野外考察。到1941年初,物價飛漲,生活艱難。吳韞珍患有嚴重胃病,手術后傷口崩裂,轉成腹膜炎。吳征鎰一直侍奉在旁,但戰爭期間抗菌素短缺,吳韞珍的生命還是沒能挽救過來,去世時年僅44歲。吳韞珍之死對吳征鎰打擊很大,動搖了他科學救國的信念,他開始真正轉向革命陣營。
西南聯大期間,清華大學因有一筆庚款基金,還另設了一套清華大學研究所,其中金屬研究所、無線電研究所以及農業研究所的植物病理組和植物生理組設在大普吉。
大普吉距昆明七八公里,彝語意為“岔路口有廟的地方”。植物生理研究組主任湯佩松與殷宏章、婁成后同住在研究室的四合院內,北面是實驗室,實驗室中間是一個陳設雅致、裝有壁爐的圖書室。每周幾乎固定有一個下午,要在圖書室中召開全室參加的學術討論會或工作進展報告會,有時也請附近學者一起參加。
同時,圖書室也是大普吉三個研究所工作人員的社交場所。有時在這里開唱片音樂會,有時在塵土飛揚的四合院中開舞會。研究所外的籃球場每天下午必有喊聲震天的比賽,每周六晚還有雷打不動的橋牌聚會。
那期間,中國植物學形成了兩個中心:黑龍潭和大普吉。因為經費充足、人才濟濟,大普吉一度比黑龍潭更為興旺,但大普吉一開始就是臨時性質,而黑龍潭則堅持了下來。
抗戰后期,農林植物所財政每況愈下,日益失去資金來源。一部分職工去學校教書,一部分在蔡希陶帶動下種植煙草、繁育良種,開辦農場,種花、種菜出售。
抗戰勝利后,眾多機構均在整備復員,農林所則繼續留守。那時農林所僅有土地10畝,平房252平方米,職工20多人,沒有固定經費。
內戰爆發后,來自靜生所的經費徹底中斷。1947年秋俞德浚前往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進修,僅副所長蔡希陶主持所務,獨撐局面。
蔡希陶將農林所西邊的一塊荒地辟為農場,栽培土豆、蔬菜等維持生活,還親手砌起烤煙房,第一次成功引種栽培了美國著名的“大金元”草煙品種。由于生活拮據,他在昆明開了一家鸚鵡店,賣鮮花、盆景、種籽、鸚鵡、云雀、鴿子、兔子、暹羅貓、小狼狗,營業收入可資助研究所少數員工。到最后,研究所只剩下八人,勉強度日。
云南大學農學院老師、樹木學家徐永椿去黑龍潭看蔡希陶,見他在茶花園種滿了紅薯和煙草,問他生活如何,他說:“雖然不算好,也還過得去,同事們上下一心,同甘共苦,這就很愉快。”
一年過年前夕,全所職工還在等米下鍋。大年二十九,蔡希陶卷起褲腳,和幾個工人一起挑著自己種的白蘿卜和青菜到小西門叫賣,直到天黑才回來,勉強過了年關。
1949年底,云南和平解放,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被軍管會接管。1950年4月,農林所易名為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昆明工作站,蔡希陶被任命為工作站主任、研究員。
“原本山川,極命草木”
禹平華1948年8月從蔡希陶擔任實習總指導的煙草技術訓練班結業,進入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蔡希陶看他對認識植物上心,就讓他到標本館工作,任務是每天翻標本,從第一個柜子一直翻到最后,生蟲的要拿掉,受潮的要晾曬。
工作站成立后,禹平華頻繁跟隨蔡希陶去野外考察。蔡希陶告訴他,植物死標本要記,活植物也要記,不僅要知道植物是什麼,還要記得這種植物分布在什麼海拔范圍,弄清楚它的生長環境、在當地有什麼用途。另外到了兄弟民族地區一定要尊重民族風俗,所謂入鄉隨俗。
1955年秋,馮耀宗和張育英從西南農學院畢業,與其他幾個大學畢業生一起分配到昆明工作站。當時工作站只有幾間房子,將近40人,管理著溫室里的兩三百種植物。
新中國成立后,吳征鎰擔任了中科院植物分類研究所(1953年更名為植物研究所)副所長。1955年,39歲的他當選為中科院學部委員。為尋一安身立命之所,有所建樹,他于1959年自請舉家遷往昆明,出任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長。他到任后,與副所長蔡希陶合作,使得昆明植物所有了大發展。
那時,吳征鎰坐鎮所里,蔡希陶則大部分時間都在外考察。張育英跟著蔡希陶基本跑遍了云南海拔一千米以下的熱帶地區,一次考察歷時兩三個月到半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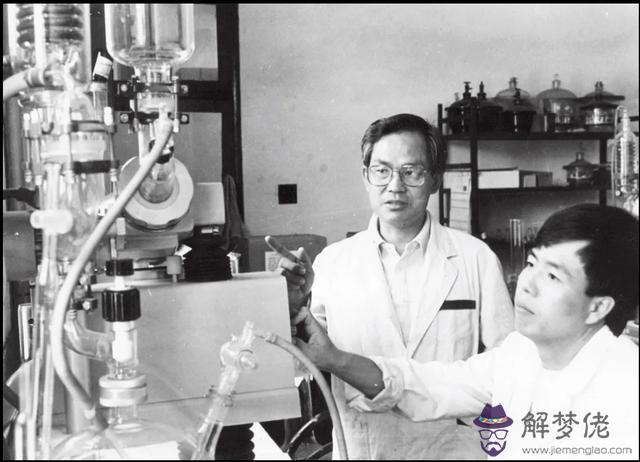
(昆明植物所專家的部分科研工作場景。)
張育英回憶,那時走的山路多是過去的茶馬古道,極為陡峭,前面的馬糞能落到后面的馬頭上。毒蚊子咬一口能腫半個月,有時肌膚還會潰爛,螞蝗咬了嚴重時需要開刀。蔡希陶規定,生病要及時報告,抬也要抬到縣上,如果隱瞞要受處罰。
張育英說,蔡希陶高興起來或者見到新奇事物就會手舞足蹈。他經常對年輕人說,熱帶資源非常豐富,有無窮的開發潛力,一說什麼東西很好就是“國家很需要”。
蔡希陶喜歡向年輕人講自己剛來云南時的故事。他在采集途中摔傷過,被毒蛇咬過,還有一次食物中毒昏迷了兩天。他說對于植物學他本是外行,那時以為來云南是出差,沒想到就是一輩子。
1958年8月,一批應屆大學生和高中畢業生來到昆明工作站,為昆明工作站改建成昆明植物研究所補充“新鮮血液”。10月,艾友蘭、呂春朝等被派到西雙版納,跟隨蔡希陶創建熱帶植物園。
呂春朝說,蔡希陶的領導風格與低調內斂的吳征鎰非常不同,別人不敢想的,蔡希陶敢想;別人不敢干的,蔡希陶敢干。吳征鎰曾評價他:“希陶同志真奇人也,始以率真見奇,因行奇事、見奇跡而愈現其率真。”

(1982年,昆明植物園的辦公樓(左)和學術報告廳(右)等建筑。)
1958年12月,蔡希陶進駐葫蘆島,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熱帶植物園。他在人才動員大會上說,西雙版納是云南最有前途的地方,很多與國計民生有關的資源都在那。他說:“同志們,西雙版納是塊美麗富饒的寶地,那里有很多珍奇植物,蘇聯專家們見著都眼饞,一屁股坐下去就是三個研究課題!”全場哄笑。
1959年,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宣告成立,蔡希陶為第一任園主任。馮耀宗、張育英都隨蔡希陶遷往植物園。

(如今的“扶荔宮”溫室群。)
那時西雙版納蔬菜缺乏,附近的傣族居民經常來植物園偷菜。張育英很有情緒,蔡希陶開導他:“你專門去推廣,人家還不一定愿意接受呢!他們吃了覺得好,就會回來主動學習。好的東西不要等著人家來要,要宣傳,教他們種,教他們吃。”那時,蔡希陶每隔一段時間就下到寨子里,吃住在那兒,推廣新的果蔬品種。
從1959年開始,裴盛基、許再福等一直跟著蔡希陶做云南藥用植物資源研究,如具有健胃和鎮痛功效的國產蓽撥、活血止血的血竭、抗癌藥物美登木、重要中藥材砂仁、含有秋水仙堿成分能治療急性痛風的嘉蘭等。
蔡希陶1978年住進昆明昆華醫院后,裴盛基去看他,他向裴盛基講起30年代初他第一次進西雙版納熱帶雨林時的場景。“西雙版納是名副其實的‘種一年吃三年’的大糧倉,有天傍晚我在羅梭江里劃舟,突然一條5公斤的大魚憑空跳進了我們的小船。又一次我們在河邊玩,腳下一塊大鵝卵石晃動起來,原來是一只5公斤的老鱉。”
周恩來和陳毅1955年視察昆明工作站時指出:“云南是植物王國,連一個像樣的王宮都沒有,應將工作站建成一個高水平的植物研究所。”此后,工作站開始大規模建設。今天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已成中國植物學研究重鎮。走進研究所大門,迎面的石墻上醒目地鐫刻著所訓:原本山川,極命草木。
“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出自西漢著名詞賦家枚乘的《七發》,意為“探究山川的本原,窮盡草木的命名”。1940年4月農林植物所辦公用房開工建設,這句話由胡先骕命意,由云南省教育廳題寫,被刻在奠基石上。吳征鎰說,此八字可以理解為以大自然為基礎,充分合理利用生物資源,是“其中有深意”的古訓。
如今在農林所原址上,建起了占地44公頃的昆明植物園。植物園分東園和西園,蔡希陶的墓碑就立于東園的山茶花園中。每到春天,這里山茶盛開,草木葳蕤,游人絡繹不絕。
(本文參考了胡宗剛所著《云南植物研究史略》)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5307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