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店里往來的人形形色色,在老板眼中,他們既是讀者,也是照顧生意的“衣食父母”。去年疫情期間,蘇格蘭最大二手書店的老板肖恩·白塞爾因過于想念曾經遇到過的顧客,而將他們寫進了書中。
在這本《書店的七種人》中,肖恩戲稱借用生物分類法上的林奈系統,將這些讀者分成七類,有喋喋不休的文學教授、高調凡爾賽的行業專家、拖家帶口的年輕夫婦,還有無所事事的退休老人等。他既吐槽一些讀者的可惡可恨之處,更懷念書與人、人與人相逢此處的奇遇故事。
這些故事匯集起來,為我們勾勒了書店的生活百態,就像肖恩自己說的那樣,他雖極盡吐槽之力,無非是想“像想念杳無音信的舊友一樣想念他們。無論是迷人而有趣的人,還是粗魯或無禮之徒,每個人我都無比想念”。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書店里的七種人》的第一章“屬:Peritus(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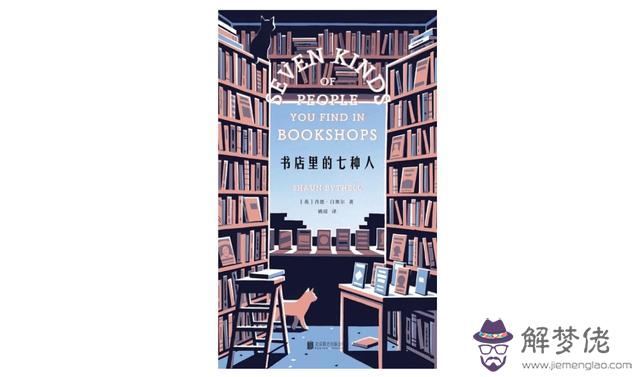
《書店里的七種人》,[英]肖恩·白塞爾著,姚瑤譯,明室Lucida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年9月。
Peritus,如果你的拉丁語和我一樣糟糕,那麼你猜測這個詞是指陰間某個討人厭的地方完全情有可原。但它并非此意。它的意思是“專家”。
總的來說,這類顧客自詡專家,他們往往沒有固定的聽眾來展現他或她的聰明才智。他們與大多數大學教師或公認的行業評論員不同,后者給出的觀點通常都基于事實,且博學多聞,有學生和讀者等著聆聽他們的講話內容。而接下來要講的專家呢,絕大多數自學成才,他們可沒有那樣如饑似渴的聽眾。但一如往常,萬事必有例外,在這類人里可以數出一些最最體貼的顧客,我能遇到他們真是三生有幸。而剩下的,真是讓人討厭得淚流滿面。
專家們最熱衷的莫過于使用超級復雜的詞匯,明明短小精干的語言就已足夠。集郵變成了“郵票研究”(philately),觀鳥變成了“鳥類學”(ornithology),對昆蟲的病態癡迷變成了“昆蟲學”(entomology)。這就像是他們外出就餐,吃下威爾·塞爾夫作為主菜,然后咽下喬納森·米德斯和斯蒂芬·弗萊作為甜品。不同之處是,塞爾夫、米德斯和弗萊全都已經吞下、消化并搞懂了整本《牛津詞典》,并準確地知道如何在恰當場合使用正確詞匯,讓自己的散文文辭清晰。而專家們呢,則痛不欲生地讓不情不愿的聽眾陷入混亂,別無任何驚艷之處。他們所知甚少,頂多五個高深詞匯,卻大用特用,說什麼都用。結果呢,唯一的作用就是一舉刮破他們智力優越感的浮面虛飾。但是我的藥劑師朋友克羅達會這樣說長單詞迷戀癥并非是嘲笑他人的理由,你有些人不知道化學品聚乙烯吡咯烷酮是大多數處方藥片中所含有的一種結合劑就去嘲笑他們。
威廉·福克納和歐內斯特·海明威就語言的使用有過赫赫有名的爭論,福克納譏諷說“誰也沒聽說過海明威用過一個需要讓讀者去詞典里查一查的詞”。對此,海明威的回應則是“平庸的福克納。他真的以為崇高的感情來自復雜詞匯嗎?我和他一樣了解那些艱深詞匯,但我更喜歡那些古老、樸素的單詞們”。就海明威對“們”的用法,我在學校里的英文老師恐怕會高度贊同福克納,他肯定會爭執說,“單詞”后面不應該加“們”,只能說“幾個單詞”,或者“很多單詞”。同樣,在對待“alternative”這個單詞時,他也相當迂腐。他堅持這個單詞的詞根來源于拉丁語“alter”,指的是兩者之一,所以不能有復數形式。因此在課堂上提出有兩個甚至更多的“alternative”時,總是我們巨大的快樂源泉。
類型一種:doctus(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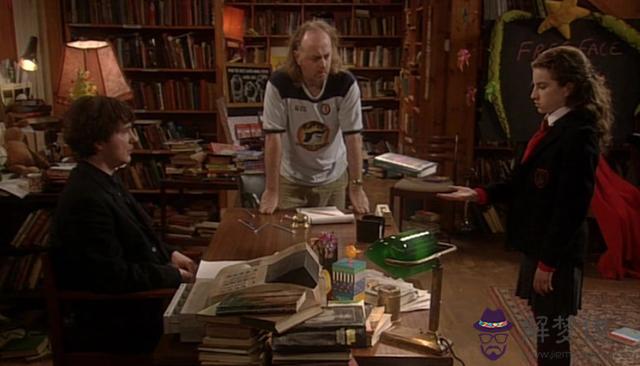
英劇《布萊克書店》(第三季)劇照。
這類人踏進書店沒有別的理由,只是為了長篇大論地給你上課,告訴你他們的專業興趣是什麼。若你對這一領域一無所知,那麼他們就能得到獨特的快感—因為你幾乎肯定是不了解的。大部分經營專業類書籍的書商都通過多年的積累,獲得了豐富的知識,這悉數反映在了他們的藏書上。可是,若你經營一家大眾書店(像我這樣),就不可能無所不知。盡管如此,對那些將自己成年后的人生都奉獻給了研究西伯利亞樹棲蝸牛繁殖習慣的人,你坦白這點試試。當你透露出,不,你不曾聽說過米哈爾·霍薩克在這一課題上影響深遠的研究《古生態重建中的軟體動物群落:利用傳遞函數模型對其預測能力進行研究》時,他們定會以一副傲慢的神情譏諷你,流露出不加掩飾的喜悅與輕蔑(兩者程度相當)。雖然這些人會從你對其專業領域的無知中獲得快樂,但他們無法真正理解為什麼你或者其他人不想花二十年時間蝸居在鄂木斯克五十英里外樹林的帳篷里,帶著一本筆記本和一架檢測蝸牛糞便的顯微鏡,除了與這一科目相關的晦澀學術論文以外,什麼都不讀。
在這類人中,極少數更擅長社交的成員則意識到,其他人或許無法分享他們難以理解的興趣。于是,這一小撮人從另一件事情上獲得了替代的快感,那就是他們對生態位的迷戀。這項愛好多少有些與眾不同,而這讓他們誤以為自己看上去更有趣了。我們曾經有位常客,總能成功地嚇人一跳。他悄無聲息地進到店里來,突然出現在柜臺旁,爽朗地同我們打招呼以宣布自己的存在,“你好啊!我這人有點古怪,我,我超愛閱讀有關不同結石之間區別的書。”但叫人痛苦的赤裸真相是,事實上,他對不同結石之間的任何區別都沒興趣,只是因為自己太過乏善可陳,因此覺得告訴別人有這樣的興趣愛好就能夠拓寬自己的人設。然而并沒有。不言而喻,任何自稱“有點古怪”的人,顯然都不怎麼古怪。
類型二種:homo odiosus(討厭的人)

電影《書店》劇照。
這類人總覺得自己是個博學家,一旦你注意到他們的癖好,就會發現,在任何你選擇提及或偶然提及的話題上,他們都要積極同你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們在場時你最好保持絕對沉默,因為就連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觸發其慷慨激昂的長篇大論,講的還是你最反感的話題。不過,你往往很難發現客人們竟然屬于這一分類范疇,直到一切為時晚矣。他們毫不避諱地去聽別的客人談話,然后用自己的觀點橫加打斷(通常充滿攻擊性)。在諸多場合,我都不得不同無辜的旁觀者道歉。他們原本只是在小聲交流,結果卻遭到陌生人的一通咆哮,這個陌生人恰好能聽到他們說話,未經允許便擅自開口(很有可能還是個種族主義者)。
在這類人中我們有一位杰出的代表,接下來的幾段記述了我朋友某天來店幫忙的經歷,這些經歷可以充分說明不知如何與這類人打交道的危險。
一個夏天的星期六早上,天氣溫暖,我的朋友羅賓十一點鐘出現在店里,在書店靠前的柜臺后面駐扎了下來。我當時正在店里四處轉悠,假裝工作。一如往常,書店的日常生活就是你來我往,數小時之后,附近著名的討厭鬼阿爾弗雷德拿著三本書去了柜臺。他帶著一種平靜的、沾沾自喜的神情,將書重重地放在了木質臺面上,眼睛則死死盯著羅賓,仿佛是在提前宣布這些書“很重要,因為正是它們造成了目前這種情況”。
在被阿爾弗雷德折磨了二十多年后,我深知,面對他可能拋出的一切引導性言論,唯一安全的回應就是沉默。不幸的是,我還沒有機會教導羅賓如何應對這類情況。除了在阿爾弗雷德背后手忙腳亂地朝他打信號、讓他別吭聲外,我什麼也做不了。好在老天保佑,阿爾弗雷德問能否把書先放在柜臺上,他要去銀行的ATM機上取點現金。
等他走遠到聽不見我們說話時,我馬上提醒羅賓,阿爾弗雷德明顯就是等著我們當中有人開口向他提問,所以千萬別問問題,以免承受那沒完沒了又自以為是的演講。他要說的就那點東西。“等他回來付錢的時候,千萬別說任何可能被他誤解的話,讓他以為你對他不吐不快的那些事兒感興趣。”這是跟羅賓分開前我叮囑他的話,隨后我就上樓去煮茶了。坦白說,我的話毫無說服力,我也不幻想自己做的這些事真能產生什麼作用。
二十分鐘后,我人在廚房里,此時疲于應戰的羅賓出現了。他解釋說,我剛離開,阿爾弗雷德就回來了,但是沒能從ATM機取到現金,因此避免提及任何可能讓其誤會羅賓對他或他的書感興趣的話羅賓建議他使用免接觸式銀行卡付款。“結果這打開了他的話匣子。接下來的十五分鐘內,我不得不聽上一段有關網絡安全的長篇大論,內容偏執多疑。我真心覺得他永遠也說不完。”
我尚未發現阿爾弗雷德對哪個話題沒有令人不快的深刻見解,也沒發現阿爾弗雷德對哪個外國人不曾懷有毫無道理的恐懼。而意料之中的是,對自己這種毫無理由的仇外情緒,他的解決方式是希望國家重拳出擊,其手段通常包括驅逐出境或監禁。而所謂的罪行呢,不過就是他們無法共享他的觀點。
類型三種:homo utilis(有用之人)

電影《書店》劇照。
并非所有專家都惹人厭煩,當然了,除非你是邁克爾·戈夫。有時候,專家能夠派上大用場。一月的時候,我接到了一位住在鄧弗里斯的女士的電話,她一直在清理自己的藏書,急需賣掉一些。那是個寒冷陰沉的下午,當我來到她位于足球場附近的獨棟平房時,發現一箱箱的書堆得到處都是。這些藏書趣味十足且種類繁多,其中包括了上百本她丈夫收集的板球類的書;而她自己則收集畢翠克絲·波特、“觀察者書系”和“瓢蟲書系”之類的書籍。這些對我來說都是書店里的優質庫存。在翻檢這些藏書的過程中,我拿起一本不太吸引人的平裝書,是帕特麗夏·溫沃斯的《荒涼之路》,就在此時她評論道:“哦,那真是本有意思的書,特別罕見,而且價值連城。”我看著這本書,封面是一張照片,拍的是一盒巧克力上放著一根針管。我是絕不會說這本書罕見或者價值連城的,然而她解釋道:“桑頓的人,也就是巧克力公司的人,反對這一封面,因為他們認為,將他們的產品與注滿毒藥的針管聯系在一起可能會損害其品牌形象。所以這個封面就撤回了,化成了紙漿,然后他們又設計了另一版封面。”這類信息對一個(偶爾)需要說服人們相信自己不是在胡扯的書商來說,珍貴無比。
我有或者說直到不久前還有一位常客,名叫哈米什。在我還差幾周寫完這本書的時候,他去世了。他是個息影的演員,非常癡迷于軍事歷史。同他聊天是件賞心樂事,他肚子里從來都不缺好故事。他對二戰課題很感興趣,對這一領域的了解程度絲毫不亞于任何專業科研人員,卻從不厭倦,也從不自以為是地高談闊論。
在我們短暫的談話當中,他會簡明扼要地摻入一些極其迷人的內容,都是精心打磨過的,并且總是讓我意猶未盡、想去了解更多。我會格外想念他。
類型四種:homo qui libros antiquos colligit
(古書收集者)

電影《書店》劇照。
古書收集者是一類截然不同的人群,他們對書的興趣往往在于將書作為一個物件,而不是其中承載的內容,盡管情況也并非完全如此;許多對古書感興趣的人都是用它們來進行學術或者家族史的研究。如何從自己的專攻領域之中甄別出特殊版本,對此古書收集者始終擁有百科全書般豐富的知識,深諳其道。比方說,羅伯特·彭斯著作的早期版本,尤其是《蘇格蘭方言詩集》。搜集這本書的人會翻遍書店的書架,尋覓極難找到的基爾馬諾克版,那是由基爾馬諾克人約翰·威爾森于1786年出版的版本。他們知道在六百一十二本的預訂版中,只有八十四本留存了下來。而且這一版本很好辨認,因為彭斯將這本詩集獻給了加文·漢密爾頓。他們也完全了解本書的二版二刷(1787年的愛丁堡版,獻給“蘇格蘭皇家狩獵部的貴族與紳士”彭斯是個收稅人員,很清楚怎麼做才對自己有利)中多收錄了十七首詩歌,《頌獻哈吉斯》里還有一處印刷錯誤。這首詩里的蘇格蘭語單詞“skinking”(意思是“水汪汪”)被錯誤地排成了“stinking”。這一錯誤在倫敦版里延續了下來(也是1787年出版),這些版本成了后來著名的“stinking版”。這種神秘的知識似乎有些強迫癥意味,但那是因為對某個課題相當狂熱的人往往都會有強迫癥的特質。
專家屬中的古書收集亞群的另一個特質便是不可避免地對價格報以不滿的嘖嘖聲。沒錯,那可能是十二卷一套的限量簽名版《尼伯龍根的指環》,由亞瑟·拉克姆繪制插圖,標價六百英鎊。我可以向你打包票,那些羨慕地摩挲它的顧客絕對會不滿地搖搖頭,告訴你說他們在別處看到過這套書,要價要便宜得多。但若果真如此,那他們還如此貪婪地盯著你的書未免也太奇葩了。嘖嘖地告訴書商你見過更便宜的版本,這樣是不太可能獲得折扣的。我們都很清楚有時買書會多花冤枉錢,或者某些書的價格會有所下降,但是絕大多數人都不太可能因為一個陌生人抱怨說看到其他書店賣得更便宜,就給一本書降價而自己承擔損失。
我有位買古書的常客,盡管他到柜臺來的時候,賬單常常達到三位數,但他總是能做到在離開書店的那一刻,讓你感覺仿佛被打劫了一般。他已經退休,顯然家境富裕,對稀有圖書抱有兼容并蓄的興趣。上一次他來店里的那天早上,我剛從一位極其有趣的老人那里買來一堆藏書。老人一家顯然已經兩只腳都踩在了更高的社會階層上。這些書曾舒舒服服地躺在一個豪門的書架上書上有你在收藏古書時總盼望見到的圖書館館戳;紋章歷史悠久,紙張間彌留著用人添火時的木頭味兒。但是,顯而易見,這個家庭后來家道中落,房子也沒有了。我懷疑這是藏書室里最后的零頭了,它們被裝在超市的面包箱里帶過來。我無法確切記清付了他多少錢,不過我留下了他的聯系方式,因為還有些書我當時沒空進行檢查和評估,如果最終定價過低,我希望能補償他。我估摸著其中應該有一套馬洛禮兩卷本的《亞瑟王之死》,由奧布里·比亞茲萊插圖并題刻。那個古書收藏家來到店里,仔細翻檢了我剛收來的貨物,最終,一不小心發現了比亞茲萊的那套書。他問我要價多少,在根本還沒機會做詳細研究的情況下,我告訴他八百英鎊,結果他(出乎意料地)開心地付了錢。幾個月后,在卡萊爾圖書節上我偶然遇見了他,他得意揚揚地告訴我,在倫敦拍賣會上,他將那套書賣出了一萬九千英鎊的高價。
作為一個書商,我感到,要公平公正地對待賣書給我的人是自己的職責所在。我覺得被騙,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賣書給我的那位老先生。如果同樣是由我來銷售這些書,并且也賣了一萬九千英鎊,為了讓自己心安,我一定會給他寫張支票,把大部分收入都歸他所有。沒錯,;我們都愛便宜貨,但在這類事情上,錢并非全部。沒人會樂意覺得自己上當了。這位古書收藏家很清楚我沒有機會發現這套書的更高價值。如果他愿意同賣書給我的那個人分享這一萬九千英鎊,但把我踢出局,那我簡直能高興死。
盡管有這樣的遭遇,但古書收藏家似乎是個瀕危物種,這一現實還是令我感到難過。“瀕危物種”這個詞可以用來形容絕大多數藏書人。他們出現在我面前的數量一年少似一年。知識不再僅是書籍貯藏的內容,嚴格說來,書籍或許不再像曾經那樣作為知識的源頭而那麼珍貴了。我父母的朋友布賴恩收集杰弗里·法諾爾的書,由于這個作家實在是太過時了,所以幾年前我就不再收購他的書。我已經在諸多場合告訴過布賴恩這件事,可他完全不放在心上。只要他人在蘇格蘭,就一定會到店里來,問我有沒有新收來的法諾爾的書。他有張清單,寫在一個破破爛爛的筆記本里,并且他總是帶著一股我始終無法擁有的樂觀激情破門而入。我這兒從來沒有他在找的東西,主要原因是我已經將所有法諾爾的書都送去廢品回收了。想到這會導致將來的某一天布賴恩最終不再到店里來,我感到有些心痛。我懷疑,直到我最后一次關上書店的門,是否還會有人再向我問起杰弗里·法諾爾的作品,除非他能享受到始料未及的翻紅,就像溫斯頓·格雷漢姆的《波達克》系列小說那樣。在BBC拍攝了這個系列之后,演員艾丹·特納在每一集里都要脫好幾次上衣,也因此讓這個系列出了名。
類型五種:mechanicus in domo sua
(家庭機械師)

電影《書店》劇照。
這些顧客是絕對的快樂源泉。通常,他們都是為路虎尋找《海恩斯手冊》。如果你沒有的話,他們也從不失望;但若你恰好有一本,那他們則會喜出望外。除了與汽車相關的書籍外,他們什麼書也不看。可是,誰又在乎呢?他們就讀他們想讀的東西,像每個人一樣,沒有一丁點兒在文學上的自命不凡。我喜歡并且尊敬他們。他們激情滿滿、令人愉快,值得最高的贊賞。他們會津津有味地吞下自己的文學獵物,比在牛津大學研究喬叟早期手稿的教授找到一本早期的卡克斯頓版古書還要熱忱。這種快樂是他們應得的。他們渴望信息,無論這信息是1947年的薩福克矮腳馬牌割草機的火花塞直徑大小,還是1976年的福特科蒂納齒輪箱規格,都無所謂。活字印刷本該為這樣的人發明出來才對為這些使用書面文字真真正正做實事的人,而非那些裝模做樣的人。那些人搞得好像活字印刷之所以存在,要麼是為了推動他們特定的宗教偏見,要麼是為了印證他們對水占卜或夢境解析這類偽智慧的信仰;抑或是為了使其自我催眠自己在斯勞的小屋位于六條地脈的交匯處,因此應當具有國家級名勝的地位。但事實上,它真正的歸屬,應該是在一群推土機的輪下。
家庭機械師總是緊張兮兮地走進書店,常常穿著油膩膩的工裝褲。當你告訴他們,你確實收有老舊的《海恩斯手冊》時,他們便滿心歡喜。即便你沒有他們要找的東西,他們自己也總能找出一本來,而且還恰好與他某個朋友正在修理的車子相關。我住在布里斯托爾的時候,有個朋友一直在購買老舊汽車進行維修。他就曾提到《海恩斯手冊》,說是“海恩斯的謊言之書”,因為總有一些線路,或者制動液儲液罐,與他當時在修理的汽車的真實狀況不相匹配。
*
就Peritus或者說專家屬而言,總的來講,類型一和類型二是你絕對想從書店里一腳踢出去的那種人。通常情況下,類型一就知道在那兒自吹自擂。這些人的丈夫或妻子終將非常膩煩他們多年來的相伴,可以做到完全無視他們。而書店則給這些人提供了一個完美場所,讓他們能夠夸夸其談。對類型二而言,政治是其相當熱衷的主題。他們通常毫不在乎“受害者們”可能不同意其觀點這回事兒,無論這觀點有多麼極端。氣候變化(他們通常否認)、同性婚姻(他們通常反對),還有歐盟(我們就別討論了)都是他們的慣常話題。別人對他們的看法越是無動于衷,他們就越是覺得有必要更大聲地叫喊出來。類型三和類型五成為了越來越稀缺的類型,這樣的人你會想同他們共進晚餐。而類型四則成了欠你好幾頓晚餐和一瓶昂貴葡萄酒的家伙,但無論是美食還是美酒,你哪個都別想看見。
本文內容經出版社授權節選自《書店的七種人》一書,內容有刪節,標題為摘編者所取。
原文作者 | [英]肖恩·白塞爾;
摘編|青青子;
編輯|張婷;
導語校對|柳寶慶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519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