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半仙是我的一個遠房親戚,是個結巴,但這并不影響他算命。他算命在我們這一帶小有名氣。
我出生在一個非常貧窮的小山村,丁小琴與我同村,是我的同學,從小學到初中都是。丁小琴的大哥丁大剛在一歲的時候找劉半仙給他算命,我們那里稱為定根八字。那時的劉半仙還沒有現在的名氣,算命的報酬也就是五毛錢,劉半仙仔細排了大剛的生辰八字,右手大拇指在其余四個手指的關節上來回游走一番,口里模模糊糊地念著子午卯酉之類的話語,睜開微閉眼睛對等候多時的大剛父母說:“這孩子長大后要瘋……瘋……”剛父母很是生氣,沒等劉半仙說完,大剛的父親氣沖沖地背著兒子走了,連五毛錢的報酬也沒有給。
大剛的父親對我父親說:“我就讓我兒子生活在我的身邊,我看他怎麼瘋?”所以,在我印象中,大剛很少出門,別人家的紅白喜事是小孩子們最高興的事,但從未見過他的身影,而我們經常徒步到小鎮上僅是為了一本小人書的樂趣,他也未曾嘗試過。他都在家里讀書,讀老師發的課本,讀我買的小人書。他的用功,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母親就經常讓我向大剛學習。
大剛是在我們鄉中學念的初中和高中,那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剛成績在我們這里是拔尖的,那時高校還沒有擴招,從建國后起,咱們村沒有一個大學生,所以,在大剛身上寄托著我們全村人的希望。高考后,咱們村的人都已經準備好了慶祝大剛升學的禮金,就等錄取通知書來了。大剛的父親也對大剛充滿了希望,但第一年參加高考時,大剛以兩分之差落榜了。大家都到大剛家去安慰大剛,去安慰的人很多,往往是張大嬸剛出來,李大媽又來了,幾乎知道這個消息的人都來了,用傾村而出這個詞一點也不夸獎,畢竟在大剛身上寄托著的是大家的希望。大家都讓大剛他爸讓大剛復讀。大家都認為,兩分不是問題,當然,大剛父親的想法也是一樣。
就在大剛十八歲那年的秋天,我們這個貧窮的小山村的人這家三塊那家兩元的湊齊了大剛復讀的學費,他又踏上了去縣城補習的復讀之路。
十九歲那年的夏天,黑色的七月還沒有來臨,大剛的父親卻接到了大剛班主任約見的口信。他第一次走進了縣城,那個夏日的黃昏,在步行兩百里路后,疲憊不堪的大剛父親就在縣高中破舊的校門前見到了大剛的班主任老師。班主任講了很多,他都沒有記住。他記住的是大剛談起了戀愛,他喜歡上了班里一個縣城的姑娘,那姑娘的父親是一個局的頭頭。那個局長讓班主任轉告大剛父親,讓大剛父親好好管教大剛,不要去騷擾自己的女兒,畢竟要高考了……
大剛的父親把手里拿的土特產一股腦交給了班主任,他沒有見大剛,跌跌撞撞、失魂落魄地走了兩百里路,到家時已是第二天的早上。
黑色的七月如期而至,考完后,大剛喜滋滋地回來了,他很有把握。他向自己的父親坦白,如果自己考上了,他就去局長家提親——他與那姑娘都決定報考同一所學校!見他很有把握,大剛的父親很是欣慰,就沒有追究他預算外多用了兩百元錢的事實,而是默默地賣了家里那只正奶著小羊的母羊,湊足了錢讓他去還了幾個老師。上世紀的那個年代,我父親在村里做民辦教師,每個月的工資是八十五元,兩百元是個大數目,特別是對大剛這樣貧困的家庭來說更是如此。
發榜后,這次大剛成績較前一年有了較大提高,但這一年高考的錄取分數線卻也比去年高了很多——大剛又落榜了!和大剛好上的那個女孩也沒有考上,她做局長的父親給她在自己的下屬單位早已找好了位置。他們見過一面,局長女兒說是大剛死皮賴臉地纏著自己,以至于自己也沒有考上。她那涂著口紅的小嘴,畫著胭脂的臉蛋,穿著連衣裙的身體,讓大剛覺得生活是那樣的陌生。
在父母及村人失望的眼光中,大剛整整一個星期沒有出門。大剛不甘心,他還要復讀。這次,他的父親不允,接連兩年的打擊,大剛已沒了往日的神采。我父母親已把大剛當作在校不務正業,不認真讀書的典型,告誡我要好好讀書,認真學習。
大剛堅持要復讀,他的父親堅決不準!大剛整整一個月沒有出門。他一個人在屋里,反復寫著那個局長女兒的名字。大剛父親生氣了,他為十九歲的大剛找了個媳婦,大剛自是不允,從未教訓過他的父親動手教訓了他,我就在我家的豬圈樓上,躺在亂草堆里聽隔壁的大剛那連綿不斷的哭聲,到后來是哽咽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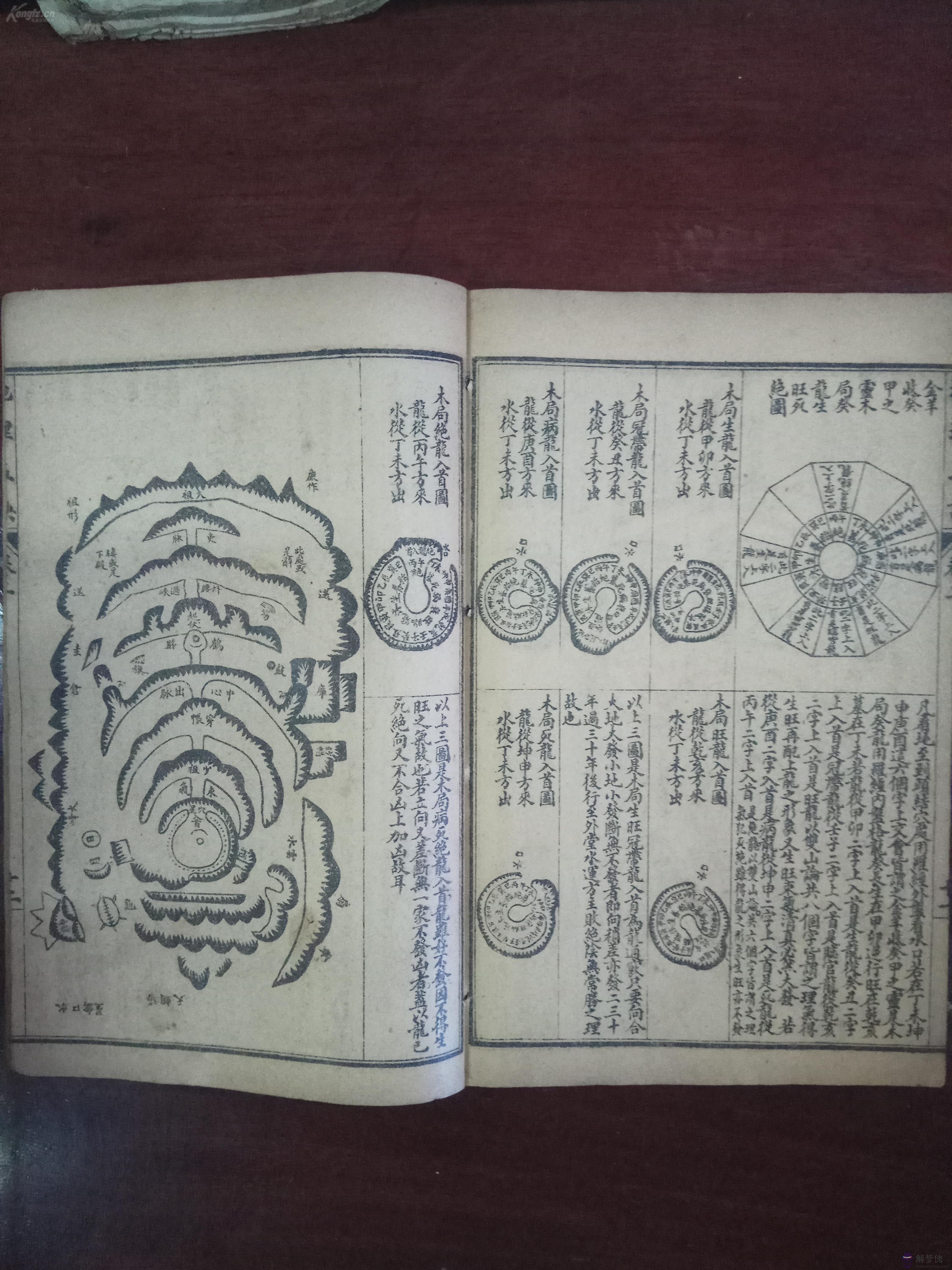
就在大剛十九歲那年的國慶節,他的妹妹丁小琴跑來對我說自己的哥哥要結婚了。我和丁小琴同歲,那年她十歲。我很羨慕她,她家要熱鬧了,她有新衣服穿了,她可以有一天不用上課了。但我的羨慕很快就變成了幸災樂禍,因為丁大剛瘋了,這下丁小琴在我面前再也神氣不起來了。丁大剛不娶,他父親逼著他娶,又動手教訓了他,結果就在他婚禮前的一天,他又哭又笑,一邊叫著那局長女兒的名字,一邊念著要上大學。就在這一哭一笑中,就在這哭哭笑笑中,丁大剛瘋了。
劉半仙一語成讖!劉半仙名聲大震。大剛瘋了,大剛父親這才覺得劉半仙是那樣的神,算命是那樣的準,也感到很后悔:當初為什麼要負氣而出,自己太無知了,為什麼沒有向劉半仙討個預防解救的法子?他兩口子捉了一只自己舍不得吃,甚至還在生病的兒子都吃不上的大公雞去找劉半仙:他們要給女兒算一次命,絕不能再像他哥哥一樣了。劉半仙照舊用右手大拇指在其余四個手指的關節上來回游走一番,口里模模糊糊地念著子午卯酉之類的話語,睜開微閉眼睛對等候多時的大剛父母說:“這孩子也要瘋……瘋……”
“什麼,也要瘋?”大剛的父母急切地問道。
“不是要瘋,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我們知道你算得很準,說小琴要瘋,那小琴一定也會瘋的!你說,要多少錢才能化解?”
劉半仙一聽到錢,后面的話就生生地吞了下去……
九七年的時候,我與丁小琴一起考上了師范。一九九九年的第一場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晚一些。下雪了,我悄悄地捏了個雪球放到了丁小琴的桌子里,但丁小琴卻沒有出現在教室里,一個早上,我看著那雪球慢慢變小,最后化為一攤水的時候,她還是沒有出現。她的書桌里也是空空的,這個與我青梅竹馬的小女孩去哪里了?在那個沒有手機,沒有QQ的年代,我看著丁小琴那空空的書桌,人在教室心在外,心里充滿了遐想和猜測。在痛苦的煎熬中,終于捱到早上的課結束,我沒有像往常一樣去食堂搶飯吃,我去找班主任老師。班主任老師說丁小琴家里來電報,讓她趕回去。原來如此,是什麼事這麼急,讓她來不及與我告別呢?
我姨媽家在鄰村,頗有點錢,花了一千多元錢裝了個電話。丁小琴一去一個月不返,我急了,便打電話到我婕媽家,請我姨媽讓我母親在某天打電話給我。我和姨媽說的是有些想母親了,有些想家了。實際上,我是想知道丁小琴為什麼還沒有回來。電話中母親告訴我一個讓我不能接受的事實:丁小琴也瘋了!
原來劉半仙給丁小琴開的解救的辦法是讓丁小琴在某天一定要回去認樹里的一棵柏樹為爹,在柏樹前親手燒三柱平安香,磕三個響頭,當然,還有1200元的算命的報酬……
于是,丁小琴便在那個下雪的早晨消失在那所師范學校,她的電報上只有幾個字:母親生病,望見最后一面。也難怪丁小琴沒有來與我告別。不幸的是那日早上路滑,核定載客十九人的客車急匆匆地載著三十五人,在冰天雪地、寒冷異常的日子,重重撞上向一輛運煤的車后,再重重地撞向了馬路后的一片石壁,丁小琴去得早,她買了前面的一號位置,她受傷最重,不僅失去了一條腿,還失去了一只眼睛。丁小琴死去活來,她卻無法面對自己的樣子,她那脆弱的神經無法接受自己如花的容顏變得那樣丑陋。她也如她哥哥一般,在哭哭笑笑中瘋了!村人很為她冤屈,要是也能如期趕到村里的那棵柏樹下,親手點燃父親早已準備好的香燭……
劉半仙再次一語成讖!他名聲更響了!找他算命的人絡繹不絕。
我師范畢業后在一個小山村里教書,那時工資極低,農民賣的一挑煙能抵我半年工資,一個做皮鞋的表哥聽說我每個月的工資數后,讓我放棄教書,跟他學做皮鞋賣——他一個趕集天賣的鞋,利潤超過我一個月的工資,還有親戚讓我去學理發、甚至還有人叫我去學殺豬、做牛販子的!
父親見我工資這麼低,他也坐不住了。父親說我從小口才就好,學算命準超過劉半仙!再說,算命沒有本錢,還受人尊敬——他讓我去跟著劉半仙學算命。我不同意,父親再說,我還是不同意,父親生氣了,動手教訓了我……
父親把劉半仙請到家里來,把一瓶幾年沒有舍得喝的酒拿了出來。父親說了讓我跟著劉半仙學算命的打算,劉半仙把頭擺得飛快,還是不同意。父親又往劉半仙碗里夾了菜,杯子里倒滿酒。見父親是真誠的,劉半仙沉思了一會,端起酒一飲而盡。
劉半仙說:“這孩子是文曲星下凡,怎麼能和我學這騙……騙人的營生?”
父親說:“你算得準,大家都相信你!”
劉半仙不語,搖了搖頭:“其實不準,我心里有數。”
父親不信:“丁家那兩個娃,不是你給算的命麼?太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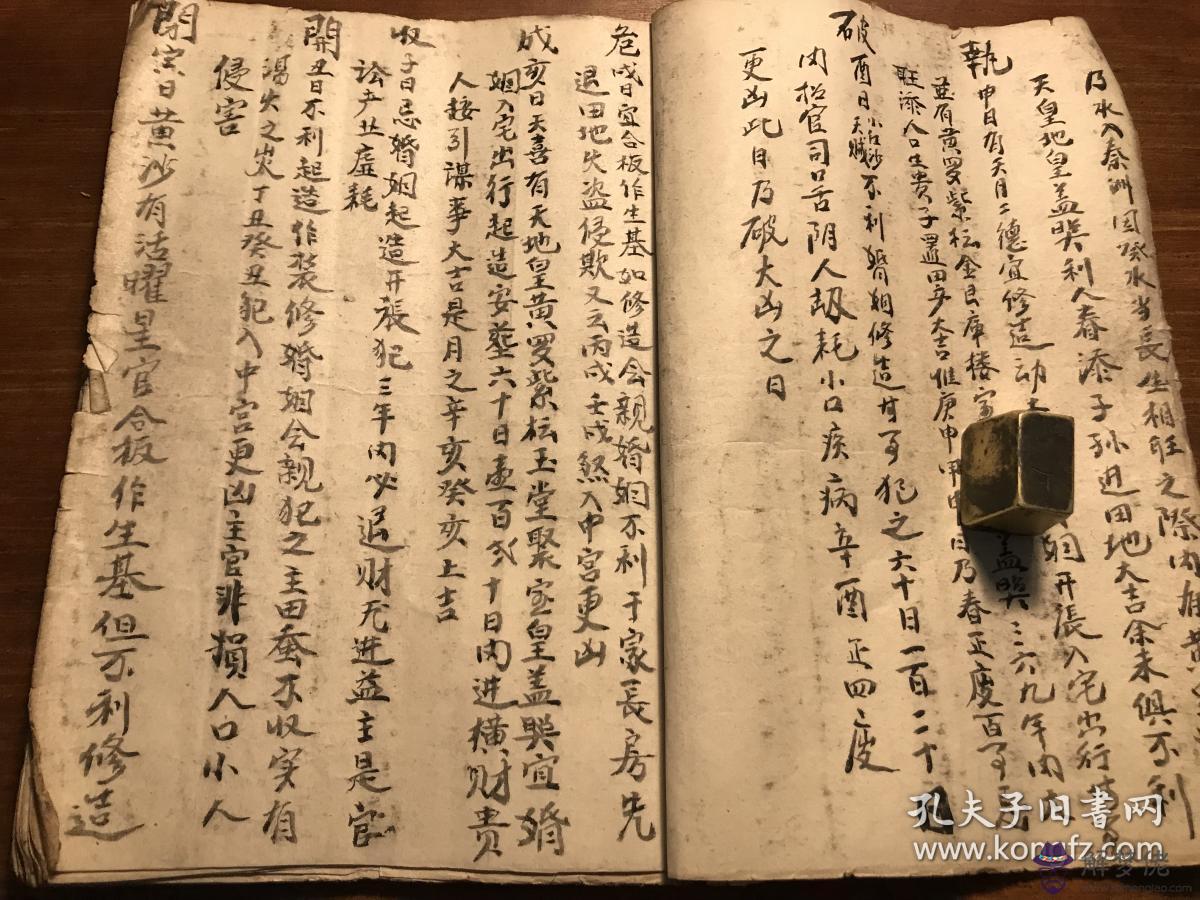
父親把酒再次滿上。
劉半仙一飲而盡!
“唉,還是和你說實話吧,你是個老實人。我也不打算再給人家算……算命了,我家窮,這些年靠算命,我……我也掙了不少的錢,可我總覺得良心過……過不去啊!”
父親睜大眼睛,懷疑自己聽錯了,他向我看了兩眼,我沒有理他。
“大剛和小琴我都是……都是說的,他們……他們要風……風光一生啊!命是自己造的啊,沒有人能……能算得中啊!”
……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5184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