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杜陽林。
杜陽林是四川南部縣人,在成都曾經從事新聞工作,一度成為傳媒江湖的風云人物,撰寫的報道多次榮獲新聞獎。但他一直放不下自己的文學夢,離開媒體從事文學創作,成了巴金文學院的簽約作家。他在推出新作《驚蜇》之前,已經出版了長篇小說和非虛構等一系列作品。
他的散文集《長風破浪渡滄海》,透視了這位70后作家走過的人生歷程。
如果你沒有讀過他的一些非虛構作品和這部剛剛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驚蜇》,你不會將作品與這個安靜內斂,為人謙遜又特別沉穩的成都中年人聯系在一起。他與《驚蟄》主人公凌云青一樣,父親早亡、母親寡居,和兄弟姊妹在極端貧困的家庭長大,甚至有著與主人公相似的成長圖譜。
《驚蜇》最容易讓讀者聯想到《人生》、《平凡的世界》等早期的小說。小說從主人公凌云青以四歲之軀,在父親的葬禮上打引魂幡開始,到少年云青考上大學離開家鄉觀龍村戛然而止,呈現了中國上世紀70年代鄉村少年的個人奮斗史,同時也呈現了整個觀龍村的真實生態,人情世故,以及人性的善良與丑惡。
熟悉《驚蜇》寫作過程的著名作家阿來認為,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映照了杜陽林成長的影子。對此,杜陽林說,“其實在那個特定的時期,家鄉真實的生活,比《驚蟄》還要艱難。”
在杜陽林質樸寫實的筆墨中,我們也跟著主人公回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主人公凌云青走進學校的這一年,也是國家恢復高考的第二年。
物質的貧乏,使小說中云青的兄弟姐妹們成為“饑餓的小孩”,因為缺失文化,造成鄉村人的無知和愚蠢,也使少年云青成長中,周圍一些人充滿自私、兇蠻和涼薄的人性。面對自己的故鄉,自己的童年,杜陽林的筆墨毫不花哨,也沒有多余的“花腔”,人性之善與人性之惡一并端上,描繪出了一幅真實的人間生存群像。
正如路遙說的,觀龍村,也不過是個“平凡的世界”。
這個觀龍村的小世界,不僅顯示出杜陽林小說的情感投射,也顯示出作家那種中國鄉村田野調查式的客觀性,一種超越了個人經驗的,在更高維度的深刻審視和打量。
所以一些文學評論家說,杜陽林講的,是又一個鄉村為主場的“中國故事”。
讀完這個長篇,記者又去讀了之前杜陽林寫的同題材的非虛構散文。其中,有寫到自己的母親的,有寫到童年自學、生病、與細妹子的情誼等個人回憶的,以小說和非虛構的不同形式,與這一部《驚蜇》,緊密地回應叩擊魂靈的那份交織和糾纏。
這是杜陽林一個人的私人記憶,一個人的人生版圖,一個人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小說中的時間似乎與當下拉開了幾十年的距離,定格在一種“回望”的姿勢上,也定格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鄉村。
我們知道的大背景是,此后,無論是中國的城市與鄉村,都發生了巨變。我們不由想,《驚蜇》中的一個個人物,他們后來怎麼樣了呢?是否有新的機遇,能夠改變自己的生活?
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的觀龍村,再過十年二十年,是否也將跟外面的世界發生更多的聯系,而更多的云青、云鴻、小木匠,以及村莊里那些似乎命運被過早“規定“的女性,是否將離開,去未知的遠方?
杜陽林說,他還將面對同一塊土地,將當下的鄉村呈現出來。或許,那將是《驚蜇》的續曲。
“有些刻骨銘心的感受,我從文字中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如今的作家杜陽林說。
7月炎夏,《驚蜇》甫一出世,既見讀者反響熱烈。7月7日下午,一場《驚蟄》研討會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行,國內老中青20多位國內頂尖文學批評家、作家參會討論。研討會由《十月》雜志主編陳東捷主持,著名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阿來出席會議并做主題發言。研討會的陣容相當強大,包括梁鴻鷹、孟繁華、賀紹俊、劉慶邦、陳福民、張學昕、劉瓊、王春林、何平、楊慶祥、張莉、劉大先、李云雷、饒翔、楊青、虞文軍、曹元勇等在內的眾多文壇名家,參與了當天的研討。他們和作者杜陽林就時代與個人、鄉村文明的現代化、個人奮斗改變命運等多個重要主題,展開了深入全面的探討。
打開杜陽林的《驚蜇》,也打開了一個時代的驚蜇之變,一個群體的驚蜇之醒。
以下是錢江晚報記者與杜陽林的對話——

【一個人的刻骨銘心:從童年到少年的十年】
錢江晚報:《驚蟄》從父親的葬禮始,云青出發上大學終,跨度是主人公從4歲到14歲前后十年,你在構思這個小說時,為什麼選取的是這一個十年的時段,是一種深思熟慮后的選擇嗎?
杜陽林:這十年時間,對于小說主人公凌云青,是非常重要的成長經歷。在十年里,他完成了從一個懵懂兒童到準大學生的人生蛻變,這是對“人”的重要性。而對“時代”而言,1976年到1986年的中國大地,風起云涌,發生了很多令人刻骨銘心的大事,橫跨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光”,個體與大時代背景相疊加,成為我選取這十年時段的重要緣由。
錢江晚報:寫《驚蟄》,我們知道有原型,鄉村和人物都有原型,那麼在你的書寫過程中,個人記憶和對時代、對鄉村的一種普遍性上的,大局上的把握,哪個更重要一些?在兩者之間,你又是怎樣去平衡的?
杜陽林:馬克思曾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他總是處在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之中。在我記憶中的原型個體,都是“大時代下的‘那一個’”,他們個體的典型性離不開大時代的影響,所以,在我書寫時,對于“個體和大局”并不存在矛盾取舍,而是沿著記憶之路,順理成章地呈現出來。
錢江晚報:你在書中寫了不少女性,徐秀英和采萍母女、還有吉祥是善良的、忍辱負重的,被欺凌的一類;還有一類女性,比如劉翠芳、岳紅花、采萍的婆婆等,雖然也是普通農村婦女,不是十惡不赦,但她們身上似乎人性丑惡的東西特別多,她們的身上人性的缺陷特別多,你覺得這是完全客觀的真實鄉村女性的呈現嗎?為什麼這些女性自身也是“弱者”,卻作惡多端,似乎對孤兒寡母起碼的同情心都沒有,你揭露的是人本性中的劣根性,還是因為沒文化、愚昧,必然會是這樣的一種“鄉村女性”群體的人性?
杜陽林:我先解釋一下,劉翠芳、岳紅花等女性,雖然身上體現了惡的一面,但同樣也體現了深深的無奈,比如劉翠芳,她因為狐臭而被丈夫嫌棄,甚至與之分床,這對一個女人的自尊心是不小的傷害,而岳紅花和孫鐵樹之間,一直都缺乏有效溝通,孫鐵樹對于往事諱莫如深,對于如今幫助寡婦秀英的事同樣只字不提,作為妻子的岳紅花,只能靠著猜疑過日子,這對她同樣是種折磨。劉翠芳和岳紅花之惡,與她們自身性格有關,與她們的家庭關系,乃至當時的“鄉村生態氣候”也有關系的。那時鄉村尚保留傳統封建思想的殘渣,一句“寡婦門前是非多”便可將清白無辜的徐秀英釘死在恥辱柱上,劉翠芳、岳紅花等人,既是這種糟粕思想的施暴者,同樣也是愚昧的受害者。
無論歷史還是現實,我們常常會看到讓人痛心的一幕反復上演:最為難女人的往往是女人。女人更能明白女人的軟肋,抓住弱點“精準傷害”,并樂此不疲。在戕害和凌辱“弱者女性”時,這些自忖為“正義守護者”的女性得到了什麼呢?也許得到了一種虛妄的優越感,認為自己更為完美和強大,抑或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她們的憤怒和不幸,必須要找到另一個更弱的對象來發泄。鄉村女性也好,都市女性也罷,當她們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手中揮舞大棒,狠狠砸向無辜且弱小的女性時,暴露的不僅僅是個體的劣根性,還表現了某種陳腐、惡臭觀念對她們的侵蝕和扭曲。
錢江晚報:我們看到一些鄉村為背景的作品中,似乎像格非的《望春風》等等,每個村莊里都有一兩個真正有文化的人,比如小說《驚蟄》中的周爺夫婦。在我們江南,我也聽一位藝術家朋友說,他從小在富陽鄉下成長,他的文化底子得益于文革時村里從城市下放來的一位學者文人,跟你寫的周爺的境遇完全吻合,這些外來文化人,似乎是給了文化貧瘠的鄉村社會一口文化的“氧氣”,使鄉村有了接上文明的燈塔,你怎樣看待周爺這樣的外來文化人對當地鄉村的影響?為什麼你寫周爺最后還是在觀龍村養老,而不是回到城市,有沒有什麼考慮呢?
杜陽林:小說《驚蟄》中的周鳳藻從城市到鄉村,一開始是被迫的,受制于時代對他的驅趕,但在廣袤的土地之上,周氏夫婦漸漸學會了融入鄉村生活,并與生存環境之間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到了后來,周鳳藻和上官云萼決定在觀龍村養老,已經不受任何外力的限制,成為人物自主的選擇。他們作為有知識有文化的人,給偏遠閉塞的鄉村吹來了一縷文明的氣息,激蕩著像凌云青這種貧窮孩子向學不輟的純真心靈,但同時,鄉村也給予他們尊重和自由,讓周氏夫婦千瘡百孔的心得到療愈的可能,他們和鄉村之間,是一種良好的互動關系,這也為周鳳藻最終決定“回觀龍村”埋下了伏筆。

【觀龍村:一方水土一方人,以及食物的味道】
錢江晚報:如果從田野調查的角度,“窮山惡水出刁民”這句話真的有道理嗎?書的最后,凌家幾個孩子紛紛表示“不喜歡觀龍村”,因為記憶中太多痛苦而不是溫情,雖然觀龍村也有善良的人在幫助這一家,但凌家孩子似乎更急需擺脫的是關于家鄉、家鄉人給他們的痛苦記憶,我這樣理解或許有誤差?也許像小說里寫的,離開了的云鴻云青的那份心情,“也許,只有到了很遠的地方,才會讓我們真正明白,觀龍村也給我們留下了這麼多的溫暖和牽絆”?
杜陽林:小說中的凌家孩子們急于逃離觀龍村,并不因為它是“窮山惡水”,而是有了人的覺醒,想要找到一條更好的出路。對于云青而言,他的離開也許是那個時代鄉村孩子最優選也最羨慕的選擇,通過知識改變命運,去往城市的他,懷揣一張大學錄取通知書,他內心是篤定的,未來的路已隱約成型。可就算是這樣,云青坐上綠皮火車,還是有著牽連不已的脈脈柔情,對家人,對故鄉,他的愛是那麼深刻,哪怕曾在這片土地上受盡折磨,也從未斷絕和改變。以云青為代表的鄉村少年,熱愛家鄉,與離開家鄉,二者之間并非矛盾關系,家鄉給予云青的苦楚是真實的,但同樣也給予他滋養,讓他有機會成長為一個堅強善良純真勇敢的少年,他永遠都不會割舍對故土的這份情誼,這種深愛。
錢江晚報:《驚蜇》中有很多饑餓年代的食物的味道,比如徐秀英做的酸菜、壓的豆腐、云青重病時借的肉等等,食物與艱難時世緊緊貼在一起,食物又昭顯四川的舌尖上的味道,淳厚的風土人情,母親做的食物,是否也是你記憶中的家鄉的味道?
杜陽林:也許在孩子的記憶中,每一位母親都有讓他驚嘆的“魔力”。小時候家境很不好,“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可我母親常常能用最簡單樸實的食材,盡量做出一道道鄉間美味,存留在我記憶中的味道,至今仍“齒頰留香”。母親以她的巧手來推豆腐、做酸菜,她沒有什麼文化,一生也說不出多少大道理,但她給予我為人要正直上進的教導,就像她巧手烹出的粗茶淡飯一樣,永遠難忘。當我回憶母親食物的味道,我回憶的也是家鄉的味道,時代的味道。
錢江晚報:書中有幾個細節,提到兩家鄰居為了土地的界石而起爭端,也寫云青和同學為課桌界線起的紛爭,又聯想到了周爺夫婦從城市分配到觀龍村,城鄉之間當時似乎毫無互通可能的界線,在你的書寫中,“界線”在當下的中國人身上到底是什麼,你是不是有什麼隱喻?
杜陽林:從過去到現在,“界線”的形式和內容會變,但它一直存在。比如云青念書時,同桌錢金寶硬要在課桌上標注一條“三八線”,如果云青越線他就有了嚷嚷喊打的權力;農村各家各戶的地塊之間由界石、界溝甚至“界山”相隔阻,標注了各自的“領土權”;周氏夫婦是被人驅逐到觀龍村,在他們面前,城市和鄉村之間橫亙著一條巨大鴻溝,城市已不再有他們的立錐之地。這些“界線”都帶著時代的烙印而存在。到了現在,社會上依然有界線,比如“階級壁壘”,社會階級的溝壑仍然存在,一些出生于貧寒家庭的孩子,并非自身不努力或缺乏天賦,但因為他們沒有在人生的分岔口做出正確選擇,難以獲取自己想象中的成功。我認為“界線”的存在,既然是難以一筆抹除的,最好的選擇不是去抨擊去抱怨,而是正視它,在此基礎上認真思考,做出最理性的判斷和選擇。

【化纖褲子以及一個時代的物質符號】
錢江晚報:在書中看到一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物質符號,比如化纖褲子,你寫得很有趣,讓人看得笑出眼淚,化纖褲子成了“高級和文化”的象征,還有上宮云萼擁有的村里的第一架照相機,一個作家總是有獨特敏感的眼光,去捕捉時代里最有代表性的細節,當你書寫七八十年代的事務時,你做過一些什麼準備?怎麼才能把握那個年代的精準印象?
杜陽林:我生于1972年,在書寫《驚蟄》時,其實是借助了兒時“記憶庫”里的很多素材,物質貧乏的時代,人們反而會更加珍視物質,云青辛苦攢錢才買來的牙刷、小木匠送給心上人的化纖褲子、細妹子的哥哥專程從北京寄一本文學期刊給妹妹……那時的人們,對于“東西”有一種鄭重和神圣的態度。我回想著貧瘠時代這些酸甜苦辣的往事,也通過閱讀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老報紙、舊雜志來獲得“那時的語感”,以此更好地把握和呈現那個時代。
錢江晚報:現在很多12歲的孩子,還是在長輩膝下承歡的無憂無慮的少年,而凌云青的12歲已經成為人生的重大轉折點,已經明白“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我們說不同時代似乎沒有可比性,當年你年少時經歷的物質之貧,身體苦難之痛,當下這個時代的鄉村少年也很少會經歷了,但當下的鄉村孩子也有他們的問題:比如留守兒童,物質上雖然不那麼匱乏,但鄉村童年依然有當下的匱乏,你對現在的鄉村狀況有沒有觀察?是否準備有新時代的記錄?
杜陽林:每個時代都有它的美麗,也有它的隱痛。我一直都對當下鄉村現狀很感興趣,也準備在下一部長篇小說里,對此有所呈現。當代鄉村的少年,也許不再像凌云青這樣,過著食不果腹的貧寒生活,因為喪父而遭受外界的凌辱,但他們又有著新時代下的煩惱和迷茫,每一代人的“突圍”,也許都要經過自我的“驚蟄之醒”,才能真正獲得成長的力量。
錢江晚報:你寫了凌云青屢次遭遇的身體的巨大疼痛,從很小被惡意燒傷,到患骨膜病差點死去,還有各種毒打,挨餓受凍,一個少年肉身的痛苦記憶,似乎已經成為本書主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在寫作時,是否想以肉體之痛的書寫來宣泄自己童年至少年的切身痛苦記憶?這樣的私人記憶的表達,現在的你從中能得到什麼?個體的痛苦,是遺忘在時間里好,還是作為私人史,需要被記住?
杜陽林:書寫云青的肉身痛苦,我不僅僅是想宣泄自己的切身痛苦記憶,因為身體的傷痛,早已在時間的河流中愈合與消退,我并不需要通過書寫的方式來進行自我療愈。在一部虛構的小說中,帶著大量非虛構的細節記憶去回溯往事,我更想隔著光陰的距離,去審視一個孩子,是如何在傷痛中艱難走出一條路來,完成他的個體覺醒和成長。
錢江晚報:我還注意到一個問題,一般我們理解中的鄉村中國家庭是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但你書中,沒有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這些角色的出現,似乎家中失去了男人這頂梁柱,只剩下寡母帶著孤兒,我奇怪的是,為什麼《驚蜇》中幾乎沒有老人呢?
杜陽林:在《驚蟄》中,其實驚鴻一瞥般出現過“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影子,不過在1976年到1986年的時間線中,他們都已作古。文中通過秀英的回憶,簡單勾勒了她母親早逝,和繼母一起生活的少女往事。而陳金柱當年多虧云青的爺爺奶奶收養,才不至于流離失所。

【個體經驗、鄉土寫作和遠方】
錢江晚報:因為《驚蜇》,鄉土中國的作家榜上又有了杜陽林這一個書寫者。我想問一下,之前關注其他中國作家的這方面的寫作嗎?你覺得自己的鄉土中國的書寫與他們最不同的是什麼,有什麼獨特性?
杜陽林:也許和我個人經歷有關,我一直很喜歡閱讀鄉土小說,無論是近代還是當代鄉土作家的作品,只要能從里面讀到泥土的芬芳,如絲的鄉愁,都讓我內心有所觸動,發生共鳴。我寫鄉村小說,目前還在探索與實踐階段,虛心學習別的鄉土作家的優勢,個人并不認為有格外的獨特性。
錢江晚報:語言上的拿捏是你寫作本書時很在意的一個問題嗎?我們看到了有很多四川特色的語言,比如瓜娃子、老漢,還有當地民歌的引用,寫作中你是否刻意去尋覓一種最適合你的觀龍村場域的語言來表達?
杜陽林:語言是小說的載體,在寫作時我并沒有刻意地“精心挑選”,語言是自然而然地聚集到指尖,像流水般慢慢淌下來。可以這麼說,在整個寫作過程當中,我都是處于一種松弛的狀態,語言無需“拿捏”,它以自然面目呈現。
錢江晚報:你是一名非專業的作家,還有繁忙的其它工作要做,你如今是怎樣安排你一天的時間的?文學這個夢想需要在這麼繁忙的人生中實現,是否需要強大的毅力和放棄一些別的什麼?
杜陽林:魯迅先生早就說過了,“時間就像海綿里的水,只要愿擠,總還是有的。”這句話很是激勵我,也促使我養成了面對時間的珍重態度。我們常常聽到“堅持”兩個字,似乎做很多事都需要毅力,需要自律,需要一種戀戀的舍棄,但我在面對寫作這件事時,初心還不是“堅持”,而是“喜愛”,喜愛是一種自然的態度,不需要太過用力地“持之以恒”,而是快快樂樂地做一件“讓靈魂感到舒服的事”。也許這正是我作為“非職業作家”所能獲得的一點“優勢”吧——不將寫作當任務,興趣便是最好的“堅持”。
錢江晚報:我聽說你還沒有到過杭州?可否對仍然屬于你私人地圖中屬于“遠方”的杭州的讀者說幾句?
杜陽林:雖然還未到過杭州,但我很早以前,就對杭州這座城市充滿了浪漫的想象,“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白居易也曾說過“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在我想象中,這是一座詩情畫意、有著眾多歷史名勝以及美麗傳說的城市。有杭州朋友告訴我,他們生活在錦繡山河中,春來賞蘇堤桃花,夏來采莼湖心亭,秋時望月六和塔,冬時吳山看松盆,一年四季這般愜意且雅致的日子,令我羨慕不已。有機會我一定要去杭州,看西湖的菡萏,嘗醋魚之美味。也希望杭州的讀者喜歡《驚蟄》,歡迎他們來成都作客,看看四川的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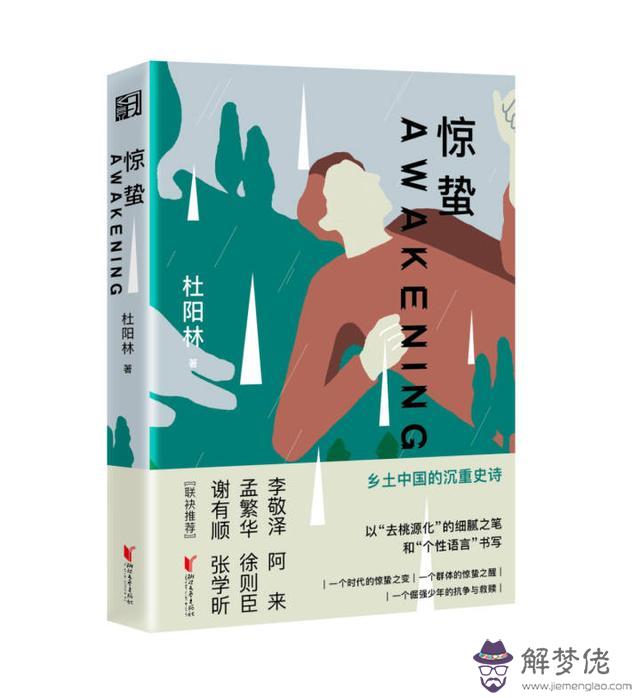
杜陽林:中國作協會員、四川省作協全委會委員、小說專委會副主任、巴金文學院簽約作家;曾任華西都市報首席記者、部門主任、成都女報總編輯;作品散見《十月》《收獲》《中國作家》《美文》《海燕》《湖南文學》《四川文學》《青年作家》等文學期刊;著有《驚蟄》《步步為營》《長風破浪渡滄海》等小說和散文集;四川南部縣人,長居成都。
本文為錢江晚報原創作品,未經許可,禁止轉載、復制、摘編、改寫及進行網絡傳播等一切作品版權使用行為,否則本報將循司法途徑追究侵權人的法律責任。
來源:錢江晚報·小時新聞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4907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