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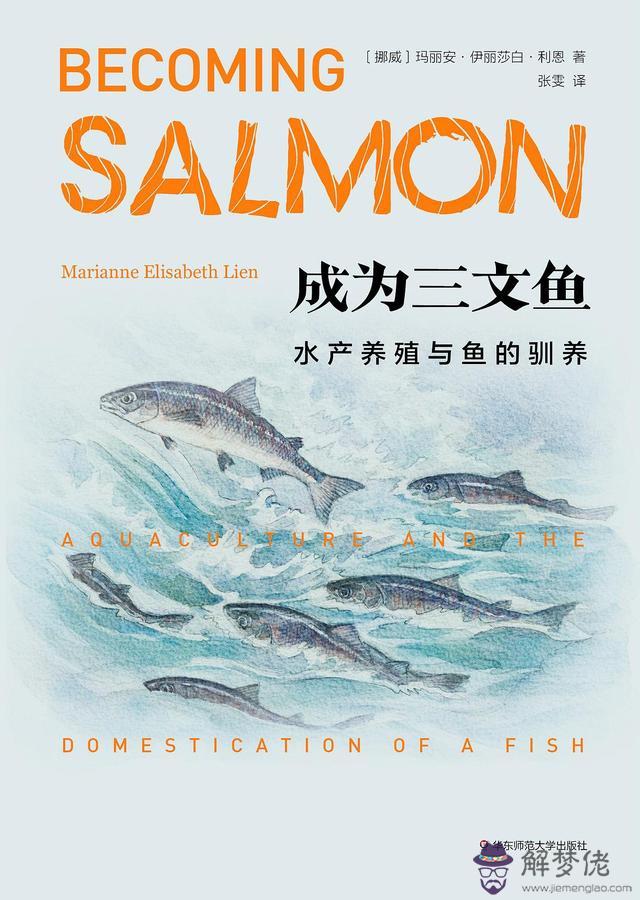
《成為三文魚:水產養殖與魚的馴養》,[挪威]瑪麗安·伊麗莎白·利恩著,張雯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352頁,75.00元
一、臨淵羨魚
涼爽的秋風徐徐吹過,人們悠閑地在海邊散步,仿佛橫行肆虐的病毒已經遠去。岸邊不斷有成群的小魚兒隨著波浪緩緩搖曳,我不知不覺停下了腳步,欣賞著它們的裊娜多姿。魚群猶如龍蛇般柔韌,組合千姿百態,圓形、八字形、梨形……好不快樂。
時間倒退一點點,它們的長輩亦是如此,集群在寬闊的海洋里,嬉戲玩耍,涌向岸邊,進入港口。擁擠引發缺氧的時候,個別魚兒還會躍出水中,在空中劃出一道道美麗的弧線。這時,我年幼的孩子會興奮地叫道:“媽媽,飛魚,魚在飛!”它們是我夏末秋初的生活樂趣。有時,為了追尋它們,我還會沿著海岸線驅車一路偵查。
它們是當地人不屑入口的一種大西洋鯡魚(俗名Bunker)。沒有垂釣愛好者的叨擾,沒有漁民思量著如何將之一網打盡,這對它們來說,或許是幸運的。它們在大海里雀躍,歡騰,跳著集體舞,營造出歡快的氛圍。對于觀魚者來說,這該是臨淵羨魚的最高層次吧!可是,它們能夠體會快樂,感覺悲傷嗎?目前的科學研究告訴我們,魚類可能缺乏這些感受。

形成梨形的大西洋鯡魚幼魚群(洪緯攝)
二、努力“成為”魚
回到家,我從書架上取下漂洋過海、歷經三個月旅程緩慢抵達的中譯本《成為三文魚》。看著封面上奮力前行的三文魚們,我好像不再那麼開心。
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以來,三文魚開始在挪威密集養殖,三文魚的全球供應量由此大增。酷愛三文魚的北美人和歐洲人為此振奮不已。以三文魚為生的北美阿拉斯加人卻愁苦不堪,在相對廉價的養殖三文魚供應充足的沖擊下,野生三文魚的價格曾經一度跌入谷底。
好景不長,養殖三文魚很快成為微生物滋生的溫床,由此波及野生三文魚。始作俑者是海虱和一些病毒。海虱是海洋中的一種常見寄生蟲,屬于微小甲殼綱動物,營體外寄生,吃寄主的黏液、表皮組織和血液。其下的魚虱屬和瘡痂魚虱屬寄生在海魚身上。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有學者警告人工養殖三文魚將對未來的自然環境存在巨大的破壞力。養殖三文魚密度大,一旦魚體感染了海虱,就會大量暴發。由此,局部海域海虱濃度大幅度攀升,游經此地的野生三文魚無辜遭殃。
水域里的病毒傳播也是一個極度危險因子。1995年,一種病毒攻擊了南澳大利亞水域,每天傳播三十公里,留下了大量的死魚。大量塘鵝、企鵝被活活餓死。有些病毒一晃而過,有些病毒連綿不絕,三文魚貧血癥病毒就是這樣的頑固分子。首次發現該病癥是在1984年,在挪威的一個養殖場里。當時傳播緩慢,過了幾年才出現大規模爆發。養殖場內的三文魚感染該病后的死亡率高達百分之百。再過了一些年頭,該病毒從北半球漸次傳到了南半球,2007年世界上最大的三文魚養殖公司“海洋捕撈”(Marine Harvest)在南美智利首次發現了傳染性的三文魚貧血癥。
面對疾病的大肆進攻和逐漸消失的野生三文魚,科學家、經濟學家、人文學者紛紛開始反思養殖三文魚的弊端,試圖喚醒人們對自然母親的敬畏之心。除卻大量學術論文,我們還可以找到更多關于三文魚的著作,比如裘德·伊莎貝拉(Jude Isabella)的科學回憶錄《三文魚》(Salmon),馬丁·李·穆勒(Martin Lee Mueller)的《做三文魚,做人》(Being salmon,Being human),還有馬克·庫蘭斯基(Mark Kurlansky)最近出版的《三文魚:一條魚,一個地球,以及它們共同命運的歷史》(Salmon: A Fish, the Earth, and the History of Their Common Fate)等等。想起這些,一種悲傷感在我心里油然升起,之前觀魚獲得的愉悅感消失殆盡。在我看來,養殖三文魚是不幸的,也是痛苦的。它們在飽受疾病的困擾時,還無形地承擔著“大自然破壞者”的惡名。我手里捧著的《成為三文魚》是要為養殖三文魚正名,還是要突出工業化養殖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抑或是其它?這只能通過閱讀慢慢尋找答案。
與《成為三文魚》的首遇是在美國的一個社交網站。書名里的“Becoming”甚是醒目。一條魚,有什麼好“成為”的呢?經過一段時間的閱讀,我似乎體會到了作者挪威人類學家瑪麗安·伊麗莎白·利恩(Marianne E. Lien)的用心,明白了“成為”的意思。
利恩筆下的主角正是工業化養殖生產的三文魚。她與其他書寫三文魚的人文學者一樣,深入水產前線,進行著人類學家口中的田野。她訪談了參與三文魚一生的眾多人員,并竭力參與到相關勞作中。“成為”是書的主線,養殖三文魚成為饑餓,成為生物群,成為外來物種。
不可避免的是,當提到一種生物從野生轉變為人工養殖或者栽培時,我們首先會想到生物學術語“馴化”一詞。利恩提出的“成為”包括了馴化,意義更加豐富。馴化是人工干預野生動物和植物的自然繁殖過程,從而使它們成為人類理想或接近理想中的物種。從經濟學意義上來講,就是將野生動植物變成了人工養殖的新型經濟品種。人類馴化了水稻、小麥、玉米等五谷雜糧,馴化了豬牛狗羊等動物,這些馴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漸變過程。
先人的鍥而不舍也讓部分魚兒獲得了在人工喂養和密集環境下生存的能力,他們鑿池養魚,稻田養魚,相傳春秋時期的范蠡著有《養魚經》。唐朝以后中國又發展了四大家魚的養殖。宋代出現了具有觀賞性的金魚。到了明末,金魚的花樣品種達到了一個高峰。相應地,在中國歷史上,關于魚類的書籍也是層出不窮,其中包括了本人偏好的明代萬歷年間出品的《閩中海錯疏》和《朱砂魚譜》。在其他國家,水產養殖業也發展得很早。來自尼羅河的羅非魚在古埃及就已經被池塘圈養,大英博物館收藏的古埃及底比斯古墓中的繪畫和浮雕可為例證。
古代發展起來的這些水產養殖方式幾乎不需要采取任何高難度技術措施,比如改變魚兒產卵方式,控制生命周期,精密計算飼料成分等繁雜手段,農民就可以收獲一籮筐又一籮筐的魚肉蛋白。古人的書寫和藝術創作無不展現著人與動物之間的一片祥和,激勵著現代人對田園牧歌的夢幻追求。

云南稻田養魚的大豐收(圖片來自: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613128)

古埃及墓內壁畫中的池塘養魚(內巴蒙的莊園花園,大英博物館館藏)
與鯉科魚類、羅非魚共同構成當今經濟魚類重要支柱的三文魚,它的養殖史是另外一個故事,它基本上是現代科學的產物。歐洲和北美食用三文魚的歷史非常長,但是三文魚的養殖歷史非常短暫,距今不過半個世紀。如若用“馴化”來表達三文魚從野生到人工養殖的過程,似乎有點與我們的固有觀念有些格格不入,而“成為”恰到好處。
鯉科魚類和羅非魚都生活于淡水,而三文魚屬于溯河洄游性魚類,不同的生命階段必須在淡水和海水中分別完成。年幼的三文魚在淡水中生活,生長到一定的尺寸和成熟度,完成生命中一個最關鍵的“銀化階段”,再游向大海。在海水中生存一定時間后,它們又開始溯河產卵,完成生命的意義,走向生命的終點。由此可見,養殖三文魚不僅需要轉換不同的場地,人們還必須準確地知道它們的生長規律。
銀化與光照變化密切相關。在自然狀態下,不同季節下的光照時間和強度均有不同。不同種類的三文魚進入銀化階段需要不同的時間。比如,在北大西洋的河流中,三文魚一般要在淡水里生活一到四年,才能發生銀化。這意味著,三文魚在進入大海之前需要做的事情便是等待,等待成熟時機的到來。
但由于利潤的驅動,動物蛋白的需求量居高不下,人類沒法等。在更短時間內獲得數量更多和體重更大的三文魚,成為養殖場的主要目標。他們想盡辦法主宰自然,控制三文魚,制造銀化需要的光照,還有掌控魚兒生活環境的溫度。只有完全了解三文魚,破解三文魚一生所有的秘密,養殖場才能獲得巨大收益。這一切只能依靠科技實現。
率先掌握養殖三文魚秘訣的是挪威人。挪威人給年幼的三文魚建立一個黑色屋頂,遮擋了所有的自然光,打破了三文魚的生命節奏。三文魚的銀化季節提前了,不用等到來年的春天,初秋就可以完成。舉個例子,一種大西洋三文魚的幼年淡水階段在野外需要兩到三年,在貯水池中只需要半年到一年便能完成從卵到幼魚、魚苗階段,隨后被轉移到海水中繼續養殖。
三文魚的壽命在縮短,體重卻在迅速增加。
三、它已經不是魚
為了研究三文魚,利恩做了不少田野筆記。她在養殖場看到了海量數據,層層疊疊。她沒有重復這樣的記錄,而是以人類學家的觸覺去記錄每一個工作場景。將魚苗倒入貯水池中時,她會用上活潑、小小這樣的詞來形容小魚苗,將“長達幾厘米的小魚苗”這樣的冷硬數據蛻化成一個鮮活的場景。我們來共同領略下:
昨天,約翰和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將人工草皮孵化盤里剛孵化的小小的、活潑的魚苗倒進位于一個被叫做維沙倫或者“白廳”的建筑里的50個圓柱形貯水池中。(189頁)
白天,她和一位養殖場同事在孵化場共同喂養魚苗。夜深人靜的時候,她便將白天的工作進行“人類學理論式”的提煉:
這里不是產科病房,而且我們不是最好的朋友。我注意到的僅僅是這些:在這種實踐中,有一種人類-動物的“聯結”正在進行,或者說是一種正在生成的關系。雖然短暫,但是在人類這邊具有關心和情感的要素,并且誰知道在水底會發生什麼呢?另外這種實踐也是性別化的。(192頁)
這種記錄通常不會發生在現代的實驗記錄本中。利恩細膩地捕捉到喂食三文魚是一個需要調整、投入情感的過程。工作人員必須緊密觀察,回應他們所感覺到的東西。也就是說,如果原來喂養的方法不奏效的話就必須進行一些新的嘗試。利恩將一種誠實的科學態度進行了完美的感官闡釋。
也正是她的密切觀察和情感投入,三文魚的“成為”過程才富有生機,讓人感覺到養殖場里的三文魚群體是由一條條鮮活的生命組成,而非“多少厘米”“多少克”“多少天”這樣毫無生機的數字的代稱。它們是有情感的動物!
利恩懂魚,作為食客的我們可能更加關心的是三文魚的口感,魚肉里的Omega-3不飽和脂肪酸含量。三文魚是肉食性的,它們吃魚。在養殖場,它們承擔著不斷增重的使命,無時無刻不在覓食。最終,重量被轉化為價格和利潤。為了減少成本,加快增重速度,植物類飼料部分取代了海洋魚類飼料。在許多養殖場,三文魚已經習慣吃高達含量百分之二十五的大豆,猶如在吃豬飼料。坊間流傳這樣一個說法:它們的外形像魚,本質上已經更像豬。事實上,由于羅非魚生長快速的特點,早已經被人稱為“水生雞”了。
三文魚的飲食結構在人類的操控下發生了巨大改變。作為富含Omega-3不飽和脂肪酸的海洋魚類,三文魚的這個賣點受到了威脅。自詡為萬物之靈的人類相信人定勝天,他們開始給三文魚投喂含有Omega-3的大豆。
人類的餐桌已經被快速生長的雞、豬、牛、羊包圍了,它們滿足了龐大人口對蛋白質的需求。酒足飯飽之后,人類又開始擔心生長激素在濫用、埋怨肉味不夠鮮美,呼吁動物也需要自由。市場上早就打起了散養雞、散養豬、天然牧場飼養的招牌。肉的等級和價格與動物的飼養環境呈正相關。可以想象,人們對待三文魚的態度也是如此。

美國某超市,左圖的野生三文魚價格高于右圖的養殖三文魚(洪緯攝)
我們也許會說,魚與雞和豬的養殖還是存在差異的。三文魚歷經銀化后的養殖場設立在天然的海域。事實上,與禽業、豬業的工業化生產相同,所有的密集水產養殖都會引發海洋生態問題,海草生長失衡,寄生蟲和病原微生物傳播迅速。
三文魚被圈養在海洋里的網箱里。儀器使用不善,或者一些不可抗拒的外力均會導致網箱破損。沖破束縛,魚兒也許可以游向更廣闊的天地。下意識地,我們都可能會認為養殖三文魚的命運應該就此被改寫了,可以由自然界來結束自己的生命,而非進入人類的屠宰場。
可悲的是,唯一等待它們的處決仍然是死亡。它們生來就該被圈養,是外來物種,是本地物種的天敵。這個天敵可以悄無聲息地讓本地三文魚無影無蹤。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挪威河流中的主要區分是在鱒魚和三文魚之間。在今天,養殖三文魚和野生三文魚是一個重要的區分。經驗豐富的漁夫可以快速地區分養殖和野生三文魚,如同三文魚的頭頂上刻了養殖公司的名號。
2017年,美國庫克水產養殖公司(Cooke Aquaculture)的一個網箱破裂,數萬條非本地大西洋三文魚逃進了普吉特海灣(Puget Sound)。沿海原住民爭相捕捉,擔心危及他們生計依賴的本地三文魚。華盛頓州州長暫停了新的網箱租賃,州自然資源部開始審查庫克公司的業務。到2018年,華盛頓州已經完全禁止了網箱養殖,結束了該州水域三十年的大西洋三文魚養殖。
人類在試圖改變甚至創造物種,反過來又擔心大自然創造的物種會由此消失。人類該是一個怎樣的矛盾體!這就是人與自然的“纏繞”吧!
責任編輯:彭珊珊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4670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