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景凱旋)于1983年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攻讀唐宋文學專業,畢業后即留校教書,教的也是古代文學。但自己性本疏懶,又不愿局限于專業,終老一經。自忖學問之事,不在謀生,而在追求人生價值。有很長一段時期,興趣轉至東歐文學,故雖從名師,術業未精,終無所成。所幸彼時大學尚寬容,得免東坡“磨牛”之喻。
大約七八年前,《財經》雜志邀開專欄,談東歐文學,后因不能賡續,遂重拾本行,改談唐代詩歌。由于是隨筆,可以盡興發揮,倒也寫得走心。寫了兩年,文章略有所積,友人陳卓讀后,建議擴展成集。正好前年剛完成一部書稿,付梓無日,便欣然答允。因選二十詩人,大致按其年代編次,各加評論。
庚子歲初,新冠病毒突然肆虐,全城商鋪關門,街上空無一人。閉門寫書,每當入夜時分,從窗戶望去,只見萬家燈火通明。因想人類真是多災多難,迄今依然綿延不絕。即以唐代而論,近三百年間,瘟疫頻發,死者枕藉。唐玄宗曾詔令各州置醫學博士,又自撰《廣濟方》,頒布村坊要路,以療人疾。代宗大歷四年,杜甫亦有詩云:“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回棹》)詩人晚年漂泊無依,身處疫中,仍覺天地廣闊無邊。
禁足半年后,疫情稍緩,遂于庚子初夏應友人之邀,赴浙江衢州。此城為南孔居處,通達四省,衢江穿城而過,周遭茂林修竹,神話中的爛柯山亦在此地。自前年與友人一別,世事變幻,如山中弈棋,渾不知歲月短長。疫中相會,感慨系之,因集唐人句以志:“南州溽暑醉如酒,舊苑荒臺楊柳新。今日亂離俱是夢,到鄉翻似爛柯人。”
唐代詩人面目各殊,但視人生如羈旅則一。西方詩尋求無限,立意在崇高;中國詩思慮有限,指歸在優美。兩相對照,各具特色,皆足以興發感動。每思平生所讀,雖廣覽外國文學,然于中國古詩卻更多共鳴,其可怪乎?質言之,唐詩自有其永恒價值,欲成意會,唯心游詩中,與古人精神相往來。此亦為本書解詩方式,未敢言研究。(導語摘自景凱旋《再見那閃耀的群星:唐詩二十家》后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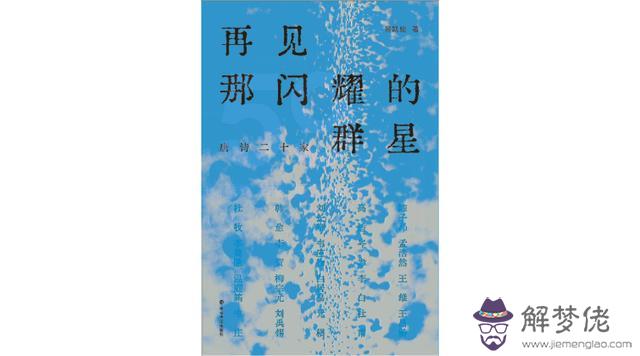
本文出處:《再見那閃耀的群星:唐詩二十家》,作者:景凱旋,版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1年11月
杜甫強烈的個體意識
唐玄宗天寶十載(751)秋,京城長安的一家旅舍,躺著一個奄奄生病的舉子。自從他來到長安求仕,已經有五年光景。前一段日子,他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皇帝賞識,一時間賓客盈門,但此后久久沒有當官的消息,門前車馬又漸漸稀落下去。正值秋雨連綿,貧病交加,一位友人突然來訪,他十分感動,寫下一篇很短的散文《秋述》: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
當時恐怕沒有人會意識到,這位潦倒京城的寒士杜甫將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詩人。他被后人奉為“詩圣”是因為他的作品體現了儒家的社會關懷,但他的價值恰恰在于強烈的個體意識。中國詩歌的特征是抒情,早期的詩歌中,抒情主人公常常是“我們”,而不是“我”。《秋述》在語言上接近口語,描述的純粹是個人的日常情緒,這實際上反映了一種思維模式的轉變。自《詩經》以降,中國詩歌走過的是一條從整體意識向個體意識漸漸轉變的道路,至杜甫終于達到了一個高度。
人類的原始神話反映的是一種整體性思維,關于這一點,只要舉出追日的夸父和怒而觸不周山的共工就足夠了,他們其實都是一個氏族的名字。早期詩歌對世界的感受是出于本能和群體意識,這也是《詩經》、樂府及古詩十九首的特征。“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小雅·采薇》)、“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隴頭歌辭》)、“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古詩十九首》),吟詠的都是一種普遍的人性感受,抒情主人公仿佛在代表人類訴說悲歡離合,個人的憂傷就是人類的憂傷。初唐詩人仍然保留了這種抽象的群體意識,如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便是如此。
詩歌中本能的消退意味著理性的逐漸成熟,盛唐開始出現更多具有個性的人物,其標志之一,就是思維中的公共自我向私人自我轉變,促成了詩歌感覺的個人化和詩歌題材的多樣化。隋唐建立的科舉制度提升了平民階層的地位,他們將理性的儒家思想作為立身之本,使得儒家思想在經歷了漢末以降的衰退后,再一次成為士人的正統觀念,都市生活的繁華更是促進了士人個體意識的發展,認識到自己的內在才能,并盡量去實現它。而杜甫正是這一理性精神的代表,幼時的他就已立下濟世之志:
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
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
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飲酣視八極,俗物皆茫茫。
——《壯游》
這首詩是杜甫晚年在夔州所作,是他對自己一生的總結。孔子曾被春秋時的隱士楚狂接輿比作鳳凰,而鳳鳥不至也的確使孔子感嘆天命不與。歷史上的許多杰出人物往往都對自我充滿信心,在某個人生階段對自身生命的深刻認識使他們擁有不可一世的氣慨,預見到自己未來所能達到的高度,并朝那個方向奮斗不已。但像杜甫那樣以孔子自喻,且生前遭際(充滿艱難困苦)及后世地位(最終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圣人)也像孔子一樣,就未免太具有天意般的神奇了。
然而杜甫是不相信天意的。他出生于鞏縣一個篤行儒家思想的書香門第,遠祖是晉朝名將杜預,祖父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他自幼天資聰慧,母親早亡,父親在外地做官,從小寄養在姑母家,整日在書齋讀書寫字,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并意識到實現才能有賴于個人品性。杜甫中年時在成都寫的文章《說旱》中說:“至仁之人,常以正道應物,天道遠,去人不遠。”杜甫始終都沒有超越性的觀念,家道中落使他墜入平民階層,這個階層的情感特征就是世俗性。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超越性觀念常常會導向群體意識,而世俗性觀念開啟的往往是自我意識。在某種意義上,杜甫站在傳統的終結之處,終其一生奉行的都是儒家的濟世精神,同時又熱愛世俗的日常生活。
四歲時,杜甫在堰城觀看公孫大娘的舞蹈,幾十年后他還能清晰地回憶起表演者雄健的舞姿和觀者如堵的盛況:“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這里面有一種豪氣干云的俠意,與李白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俠客行》)、王維的“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少年行》)一道,共同體現了盛唐那種自由不羈的元氣,而杜詩的氣象更為闊大。
生逢開元盛世,杜甫是幸運的,又是不幸的。兩次應試都未中第,先后客居長安十年,生活常常陷于困窘,不得不奔走權貴之門,四處投獻干謁。《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就是寫于這一期間: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李邕求識面,王翰愿卜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今人常引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以證明杜甫的忠君思想,但這只是詩人投謁時自詡的一句高調。堯舜之治從來都是儒家的烏托邦理想,唐朝的皇帝做不到,唐朝的臣子更做不到。高調的背后是渴望立登要津,擺脫自己在長安“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貧賤生活。所幸杜甫幾次參加科舉考試都沒有成功,否則中國歷史上可能會多出一個正直的官僚,卻少了一個偉大的詩人。
可以說,沒有一個同時代詩人比杜甫更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他詩歌中的敘事者都是他本人,這與他詩歌的生活化特征有著密切關系。此前的詩人抒發現實感受都是借漢魏以來的樂府舊題,表達征人思婦的相似內容,這種情感既是個人性的,又是普遍性的。而杜甫則是第一個自創樂府新題的詩人,他寫時事,寫個人,寫日常,擴大了詩的題材范圍,在他筆下,幾乎一切都可以入詩。如果不是這種自覺的主體意識,杜甫是否會贏得崇高的文學史地位是需要打一個問號的。
大多數古代詩人都會離我們遠去,我們往往只對他們的詩感興趣;而杜甫卻能一直活在今天,我們讀他的詩,同時也很想了解他的心路歷程。
杜甫在長安這段時期曾與李白、賀知章、張旭等名流交往,寫下《飲中八仙歌》。在這群放浪不羈的文人中,他是唯一一個清醒旁觀的人,從盛世的一片承平氣氛中察覺到潛伏的社會危機。在寫下《秋述》后,杜甫又寫出了《兵車行》和《麗人行》。一邊是邊庭流血,田園荒蕪;一邊是權臣當道,歌舞升平。杜甫對民間疾苦的同情使得他能夠敏銳地捕捉到時代即將發生劇變,這是帝國大廈將傾的前夜。
天寶十四載(755)是唐王朝的轉折點,帝國深刻的內在矛盾最終導致安史之亂,同時也造就了杜甫。這一年,杜甫終于被任命為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他旋即前往奉先省家。時值寒冬,他在夜半時分從長安城出發,清晨經過驪山,想象著戒備森嚴的離宮中正在舉辦盛大的歡宴。大多數唐代詩人寫到宮廷,往往是表達一種繁華或宮怨,杜甫卻以普通百姓的貧困作對比,轉向對社會矛盾的揭露: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經過艱苦的旅程回到家中,剛進家門就傳來一片哭聲,原來幼子已經餓死。
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
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
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
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
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
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赴奉先詠懷》
詩人再一次從自身的不幸遭遇聯想到整個社會,并為自己可以免除賦稅征役而感到慚愧。這種反思精神是前所未有的。歷史上那些杰出的詩人都有杰出的人格,他們像常人一樣有自己的小苦惱、小波折,但又總能從個人生活中感受到天下蒼生的困境,將自我意識擴展到社會意識,表現出博大的悲憫之情。

蔣兆和《杜甫像》
矛盾是杜詩的主要元素
就在杜甫赴奉先省家的時候,安史之亂暴發了,杜甫的生活也陡然發生了劇變。在中國歷史上的各種大動亂中,安史之亂只是其中的一個歷史性瞬間,但對于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來說,這一瞬間就是一生。此后杜甫飽經喪亂,流離失所,先后寫下《悲陳陶》《哀江頭》《北征》《彭衙行》《羌村》、“三吏”、“三別”等即事命篇的古體詩。同時代的詩人很少描寫這場戰亂本身,只有杜甫突破了漢以來儒家的忠君觀念,沒有無條件地站在朝廷一邊,而是在詩中反映了官軍給百姓造成的苦難,表現出直面現實、“善陳時事”的能力。
晚唐孟棨在《本事詩·高逸》中稱:“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在表現生活的真實方面,杜甫開創了一種見證的文學。“詩史”的稱號將詩歌的作用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重新定義了詩人的角色。安史之亂對于唐王朝是一場災難,但這場災難似乎又是為杜甫的詩史而發生的。
只要將《彭衙行》或《無家別》與漢樂府《十五從軍征》比較一下,就會發現,杜甫的這些新題樂府不但繼承了漢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而且采用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不再是漢樂府那種概括性的描寫,而是更加個人化、細節化。肅宗至德二載(757),杜甫從左拾遺任上請假回鄜州羌村探親,風塵仆仆地在薄暮時分到達家中:
崢嶸赤云西,日腳下平地。
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
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鄰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欷。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羌村》
這簡直就像一篇小說的情節。日頭落到地平線下,門外的鳥雀看到客至,歡快地鳴噪起來,詩人突然出現在家人面前,妻兒先是不敢相信,繼而默默地擦著眼睛。鄰人聽說詩人回到家中,全都攀在墻上觀望,陪著一起嘆息垂淚。到了深夜,鄰人散去,兒女也睡著了,夫妻二人這才手持蠟燭,仔細對視,懷疑自己依在夢中。
江淹《別賦》的“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道出了古往今來一種普遍的情感。后世詩人對于“別易會難”都有著很深的體驗,如李益的“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喜見外弟又言別》),司空署的“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云陽館與韓紳宿別》),而晏幾道的“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鷓鴣天》)更是化用杜詩。然而,他們描寫悲歡離合的心理程度皆不如杜甫的“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語言越是平實就越是深切。
杜甫在敘事上的細致感覺說明他具有一種小說家的眼光,能抓住生活中最具沖突性的場景,這是其他詩人都不曾擁有的能力。“三吏”“三別”反映的都是戰爭期間的具體事件,其中《石壕吏》已被選入今天的各種教科書,而《無家別》人們則談得較少,實際上這首詩更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凄愴。詩的開頭像是仿漢樂府《十五從軍征》,描寫一個士兵從戰場歸來,看到家鄉已變成廢墟。他剛要獨自出門去收拾田地,縣吏就前來逼他再去服役。
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
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
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
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
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
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
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
人生無家別,何以為烝黎。
——《無家別》
《十五從軍征》的結尾寫道:“出門東相看,淚落沾我衣。”而杜甫顯然是在接著往下寫:“人生無家別,何以為烝黎。”杜甫之所以能超越自己的時代,就在于他繼承的是孟子民貴君輕思想,詩中那種悲天憫人的情懷發自天性,對一切生命都有一種敬畏。因此,這首詩就不僅是在描寫安史之亂,更是在描寫整個歷史了。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實錄的傳統,各個歷史事件在正史、雜史、別史和傳記中都有記錄,但那些都只是事件敘述,卻沒有人物塑造。杜甫在詩歌中描寫自己,也描寫他人,讓我們看到了一千多年前一個個真實而具體的生命。清人袁枚評道:“人但知杜少陵每飯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兒女,何在不一往情深耶?”這種“情深”要歸于杜甫性格中的真誠,他就像生活在我們周圍的一個普通人,整天為日常生活的拮據而愁眉苦臉,內心卻藏著一個豐富的情感世界。
因此不難理解,當杜甫在戰亂中與友人久別重逢時會寫出如此動人的詩句:“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贈韋八處士》)這十個字透露出多少真切的人生經驗,以至于千載之下的讀者都能感受到其中蘊含的那種人性的深度與廣度。平常人的命運,不尋常的感受,造就了杜甫的詩史,沒有這類詩,我們對歷史的了解就永遠是抽象的。
肅宗乾元二年(759),杜甫離開戰亂的關中,流徙到蜀地,投靠時任綿州刺史,后遷成都尹、劍南節度使的友人嚴武,在成都郊區的浣花溪邊蓋了一間草堂住下,就是在那里,他寫下了那首傳頌千古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
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儒家的“仁愛”是基于宗親血緣關系的,但杜甫突破了這個藩籬,他從來都沒信奉過佛教,卻有真正的佛教的博大擔當,以一種自我犧牲的精神,將仁愛之心施及眾生,仿佛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都與他自己的生命有關。我們知道,儒家思想在唐代重新成為官方哲學后已經僵化,杜甫的博愛情懷源于他對“仁”的體認。也許他已經意識到,孔子將“德”轉化為“仁”,是因為天道不會對“德”做出現世回報,所以必須將外在的德行轉變為內心的信念,或者說內化為一種人格,不計任何利害地同情他人。
這一切同樣是出于杜甫的主體意識,他是第一個直接表現內心沖突的詩人。他寫自然,滲透了人際之間的情感;寫歷史,貫穿了現實世界的關懷。張若虛、李白詩歌中的月夜澄明高遠,這種自然的宇宙圖景是杜甫所沒有的。同是受樂府詩的影響,李白可以寫出“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杜甫也可以寫出“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但李白卻寫不出“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而杜甫也寫不出“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李白將此前的詩歌境界發展到頂峰,杜甫則突破了這個境界,登上了另一座頂峰。
這里主要說的還是杜甫后期的近體詩。“詩史”固然是一個美譽,但中國詩歌的本質特征終究是抒情性,是讓讀者產生情感上的共鳴。年齡日漸老大,此時的杜甫似乎已徹底放棄仕途,轉而將寫詩作為生活的主要內容,并將精力放在更講究藝術技巧的近體詩上。盡管近體詩不適宜敘事,但卻更適宜用來表現個人的內心生活。畢竟,一個人要想跟他人發生關聯,就必須先跟自己發生關聯。與此同時,嚴格遵循格律也使杜甫對漢語言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進行了前所未有的開拓性探索。
杜甫曾用“沉郁頓挫”四字評價揚雄、枚皋的辭賦,其實這也正是他自己詩歌的風格,尤其是他晚年的近體詩。“沉郁”是情感的深沉,“頓挫”是筆意的跌宕。寓居浣花溪邊的日子里,杜甫似乎又回到了在京城寫《秋述》時的心境。生活雖依然困窘,卻也變得安定了,平日來拜訪的客人不多,有喜歡的,也有不喜歡的。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
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糲腐儒餐。
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賓至》
同樣是寫來客,杜甫另一首更有名的《客至》有著歡欣明快的調子,對于友人的來訪感到由衷的快活,而《賓至》卻顯得有點不耐。僻居老病,貴客不期而至,來時輕車肥馬,驚動四鄰,引起詩人不快,又不得不竭誠款待,謙和中有反諷,自嘲中有尊嚴,顯露出杜甫戲謔幽默的一面。正是從杜甫開始,唐代詩人開始更多地在近體詩中描寫自我。
代宗廣德元年(763)六月,好友嚴武再任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并保薦杜甫為節度使參謀。杜甫不得不住在幕府,可寄人籬下的生活總讓他感到不安。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
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
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宿府》
清秋之夜,詩人獨宿幕府,眼看蠟燭燃盡,卻難以入眠。次聯在音律節奏上變上四下三為上五下二,給人一種沉郁頓挫之感。似乎沒有一個唐代詩人比杜甫有更多的內心沖突,這種沖突源于事物本身的復雜性,以至于矛盾成為杜詩的主要元素。杜甫接受好友的邀請出來做官,卻在詩中流露出不愿受束縛的心態,不久便辭職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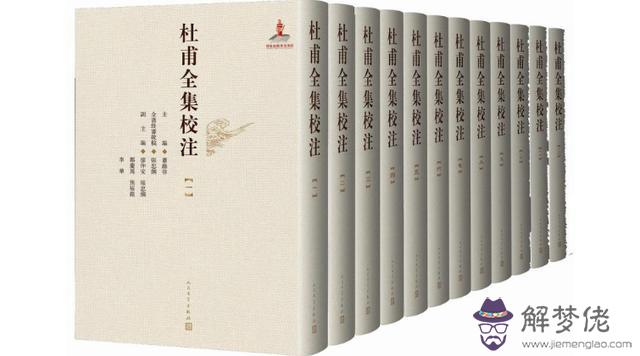
《杜甫全集校注》,作者:杜甫,主編:蕭滌非,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4年4月
杜甫的詩始終行走在路上
廣德元年十月,吐蕃起兵攻破松、維、保等州,繼而再攻陷劍南、西山諸州,杜甫對此深感憂慮,他在春天時分登上高樓,憑欄遠眺。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后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登樓》
前四句意境闊大悠遠,后四句全是議論,又回到入蜀前憂世傷時的主題,借歷史教訓暗諷朝廷重用宦官,造成國事維艱的局面。
全詩結構謹嚴,從明亮到晦暗的天色變化表明時間的順序,前七句的第五字尤見杜甫對語言的錘煉功夫。“錦江春色”“玉壘浮云”,既是眼前之景,更是詩人內心的反映,與《春望》中“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一樣,屬于主觀自我的移情。這是詩歌表現方式的一個大變化:如果說初、盛唐詩人大多還是即景生情,那麼在杜甫筆下,所有的景物都在為自我的情感服務。
就在寫下《宿府》和《登樓》的第二年,嚴武突然病逝,杜甫失去依靠,決意離開成都,沿長江而下,再次踏上流浪的征途。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
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旅夜書懷》
詩人在黑夜中舟行的前程是未知的,他不知道這一次的漂泊將在何時何地結束,也許永遠都不會結束。在此之前,李白也曾從峨眉乘船東下,滿懷信心地走向更廣闊的世界,而杜甫卻非常明白這世界是難以預料的。如果說李白的“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是眼前之景,自然而明朗;那麼杜甫的“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則是構想之景,經過了一番仔細推敲。在遼闊的星空下,詩人的心事像江水一般浩茫。“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已不是自然思維的見物起興,而是理性思維的以物自喻,是對個體的孤獨性最具形上意味的描述。
這種理性思維讓杜甫時常突破詩歌慣例,句子之間似乎沒有字面上的邏輯關系。宋代吳沆評論道:“杜詩句意,大抵皆遠,一句在天,一句在地。如‘三分割據紆籌策’,即一句在地;‘萬古云宵一羽毛’,即一句在天。如‘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即上句在地,下句在天。……惟其意遠,故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句意的跳躍表明杜甫是有意識地將看似不相關的意象聯系在一起,以增加詩的表現力。詩終究是想象的藝術,想象有多遠,詩就能走多遠。
從成都來到夔州,杜甫在那里居住了兩年,這段時間他寫了四百多首詩,他的律詩也達到了最成熟的階段,如《閣夜》《登高》《詠懷古跡五首》和《秋興八首》,都有著“意遠”的特點,現代作家郁達夫將這種特點總結為“辭斷意連”和“粗細對稱”。如《詠懷古跡》(其三):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夜月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歷來描寫昭君的詩中,杜詩是最具悲憫和同情的。郁達夫在解釋這首詩的句法時說:“頭一句是何等的粗雄浩大,第二句卻收小得只成一個村落。第三句又是紫臺朔漠,廣大無邊,第四句的黃昏青冢,又細小纖麗,像大建筑上的小雕刻。”句子之間的遞進、轉折、倒置、跳躍擴大了律詩的容量,同時表現出時間的力量對個人命運的永恒作用。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
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
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閣夜》
時間是杜甫律詩中的核心,在他早年的《望岳》中就用到過“陰陽”一詞,那是古代中國人對宇宙本質的認識。《易經·系辭》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二者的交替變化代表了自然的四季晝夜,也構成了生命的本源。杜甫對于唐詩的轉變作用就在于他已經從自然意識轉向歷史意識,把人看作歷史的主體。但是,他的思維依然囿于自然時間,而不是歷史時間。在宏觀的宇宙中,具體的歷史事件是不足道的。這首詩的頷聯從戰亂的悲傷突然跳到生活的日常,句意之間有很大的跨度。將全詩各聯意思聯系起來的是末聯的議論,既然古往今來所有人的終點都一樣,也就不必太介意世間的艱難。
然而,杜甫終究不是一個能放得下的人,他在夔州寫下的《秋興八首》以組詩的形式描敘自己的身世之感。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
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云接地陰。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秋興八首》其一
秋天的巫山是陰郁的,漫山遍野的楓林加深了詩人凋傷的心緒。頸聯在句式上采用倒裝,“叢菊兩開”指時間上的兩度秋天,“孤舟一系”指空間上的漂泊他鄉,這樣寫不僅是為了協律,更是有意造成一種閱讀障礙。杜甫很懂作詩的原理,詩歌的語言流不可太順,太順則容易流于熟滑,滯澀的句式往往能造成某種陌生感,讓讀者不得不停下來,細細體味詩人通過景物描寫表現出來的復雜的內心世界。
王國維曾將中國詩詞的境界分為“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后者是以物觀物,物我合一,前者是以我觀物,物皆著我之色彩。這一美學理論受到過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啟發,某種程度上,“無我之境”即是優美,屬于無利害關系的直觀;“有我之境”即是崇高,屬于理性的判斷,并與人的道德情感相關聯。宋代的嚴羽以“妙悟”贊揚盛唐詩,實際上是以“無我之境”為最高標準,使得“情景交融”幾乎成為后世評價古典詩歌的慣用詞語。
然而,杜甫的寫景卻不是“情景交融”四字可以概括的。他描寫自然景物時,總是摻雜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常給人一種不愉快的感覺,有點類似康德對崇高的定義。詩人面對的是比自我更強大的力量,意志與之對抗,經歷著瞬間的生命力的阻滯,立刻又產生更強烈的生命力的噴射,在對抗的同時顯示出詩人的道德能力。
也就是說,杜詩的力量不在外境的雄渾闊大,而在內心的思力,它反映的是詩人內心無日無之的沖突,思力愈是深厚,情感就愈是內斂。杜甫晚年的律詩雖然更精于錘煉,表達卻極其平和,如同在寫家書,結尾常常不追求意境的高揚,而以平常的敘事或議論結束: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登高》
歷代對《登高》一詩的評價都極高,甚至有人譽為“古今七律第一”。盡管如此,王世貞仍稱其“結亦微弱”,沈德潛亦稱此詩“結句意盡語竭”,這其實是囿于盛唐詩的結尾往往都有著言盡而意不窮的韻味,而杜甫這首詩卻落在困窘的實處。實際上,杜甫代表了一種新的審美意識,“沉郁頓挫”不僅是一種風格,更是一種觀念,他意識到表現日常生活的艱難也是一種美。
代宗大歷三年(768),客居夔州兩年后,杜甫又開始了他的南方漂泊,先到江陵,再到岳陽,又到潭州、衡州。此后兩年,他一直在湘江的船上來回漂泊。因在途中以腐肉充饑,他于大歷五年(770)病卒于潭州到岳陽的船上。在去世前一年寫的《登岳陽樓》,融入了他一生的悲涼情感: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清代詩評家黃生稱這首詩寫景闊大,自敘卻由闊入狹,殊不知這種由大向小、由外向內的描寫正是要凸現個體在這個廣漠世界的存在境況。杜甫一生遭逢亂世,漂泊無依,他的矛盾與均衡,他的擔當與幽默,都是一種人性的甚至是太人性的表現。當他剛從夔州乘舟到達江陵時,正值暮春時節,他寫下一首送別友人的詩:“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他想超越自我,卻擺脫不了存在的限度,因為他的精神世界里只有“人情”的觀念,而沒有“天意”的慰藉,他不相信那種無時間性的永恒,不能像其他詩人那樣逃避到佛道的慰藉里。
對于杜甫來說,“天意”固難知曉,人世又再無可共語者。這一刻,他的內心一定是凄涼的,因為生命的意義在他就是活在這個世上,去愛他人,而世上最珍貴也最容易失去的就是人的親密關系。杜甫是一個誠實對待自己和他人的人,注重的是尋常的智慧。他放不下具體的人世情感,那是因熱愛而產生的掙扎,是生命無法避免的悲哀。在他的詩里,人類可悲的命運在永恒面前顯露無疑。
詩歌自從誕生之日起,就與痛苦而不是幸福聯系在一起。古今中外那些偉大的詩人都有一種人生的悲劇意識,體味到個體生命與永恒存在之間的巨大鴻溝,即使在最快樂的時候,也對苦難的況味有一種迷戀。就詩歌所呈現的生命樣式而言,王維的詩渴望歸去,李白的詩憧憬遠方,杜甫的詩則始終行走在路上。
“他鄉復行役。”(《別房太尉墓》)這就是杜甫的人生概括,純粹的遠方與歸去都已褪去理想的色彩,詩意的棲居就在此處,在當下,在實際的人生中,那是對人類真實生活的深切理解。因此,不同于王維的當下,杜甫的當下連著遠方;也不同于李白的自然,杜甫的自然中沉淀著歷史。
幾千年的中國文學史中,只有少數幾個詩人能夠一直活在后世人的心中,而杜甫就是其中的一個,因為正是杜甫給生活的日常性賦予了永恒和普遍的意義,將實際人生提升到崇高的境界。
原文作者|景凱旋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琳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4182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