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丨馮友蘭
人對于宇宙人生的覺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對于人的意義,亦有不同。人對于宇宙人生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的覺解,因此,宇宙人生對于人所有的某種不同的意義,即構成人所有的某種境界。
佛家說,每人各有其自己的世界。在表面上,似乎是諸人共有一世界;實際上,各人的世界,是各人的世界。“如眾燈明,各遍似一。”一室中有眾燈,各有其所發出的光。本來是多光,不過因其各遍于室中,所以似乎只有一光了。說各人各有其世界,是根據于佛家的形上學說的。但說在一公共的世界中,各人各有其境界,則不必根據于佛家的形上學。照我們的說法,就存在說,有一公共的世界。但因人對之有不同的覺解,所以此公共的世界,對于各個人亦有不同的意義,因此,在此公共的世界中,各個人各有一不同的境界。
例如有二人游一名山,其一是地質學家,他在此山中,看見些地質的構造等;其一是歷史學家,他在此山中,看見些歷史的遺跡等。因此,同是一山,而對于二人的意義不同。有許多事物,有些人視同瑰寶,有些人視同糞土。有些人求之不得,有些人,雖有人送他,他亦不要。這正因為這些事物,對于他們的意義不同。事物雖同是此事物,但其對于各人的意義,則可有不同。
世界是同此世界,人生是同樣的人生,但其對于各個人的意義,則可有不同。我們的這種說法,是介乎上所說的佛家的說法與常識之間。佛家以為在各個人中,無公共的世界。常識則以為各個人都在一公共的世界中,其所見的世界,及其間的事物,對于各個人的意義,亦都是相同的。照我們的說法,人所見的世界及其間的事物,雖是公共的,但它們對于各個人的意義,則不必是相同的。我們可以說,就存在說,各個人所見的世界及其間的事物,是公共的;但就意義說,則隨各個人的覺解的程度的不同,而世界及其間的事物,對于各人的意義,亦不相同。我們可以說;“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我們不能說,這些意義的不同,純是由于人之知識的主觀成分。一個地質學家所看見的,某山中的地質的構造,本來都在那里。一個歷史學家所看見的,某山中的歷史的遺跡,亦本來都在那里。因見這些遺跡,而此歷史家覺有“數千年往事,涌上心頭”。這些往事,亦本來都在那里。這些都與所謂主觀無涉,不過人有知與不知,見與不見耳。莊子說;“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就其知不知、見不見說,就其知見時所有的心理狀態說,上所說諸意義的不同,固亦有主觀的成分。但這一點的主觀的成分,是任何知識所都必然有的。所以我們不能說,上文所說意義的不同,特別是主觀的。由此,我們說,我們所謂境界,固亦有主觀的成分,然亦并非完全是主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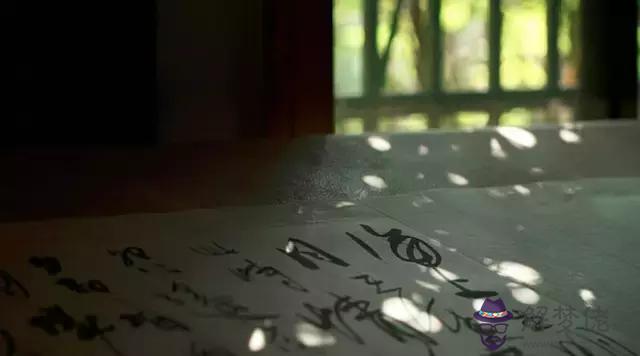
各人有各人的境界,嚴格地說,沒有兩個人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每個人都是一個體,每個人的境界,都是一個個體的境界。沒有兩個個體,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亦沒有兩個人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但我們可以忽其小異,而取其大同。就大同方面看,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為四種;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此四種境界,以下各有詳論,本章先略述其特征,以資比較。
自然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種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順才或順習的。此所謂順才,其意義即是普通所謂率性。我們說,我們稱邏輯上的性為性,稱生物學上的性為才。普通所謂率性之性,正是說,人的生物學上的性。所以我們不說率性,而說順才。所謂順習之習,可以是一個人的個人習慣,亦可以是一社會的習俗。在此境界中的人,順才而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亦或順習而行,“照例行事”。
無論其是順才而行或順習而行,他對于其所行的事的性質,并沒有清楚的了解。此即是說,他所行的事,對于他沒有清楚的意義。就此方面說,他的境界,似乎是一個混沌。但他亦非對于任何事都無了解,亦非任何事對于他都沒有清楚的意義。所以他的境界,亦只似乎是一個混沌。
例如古詩寫古代人民的生活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識天工,安知帝力?”此數句詩,很能寫出在自然境界中的人的心理狀態。“帝之則”可以是天然界的法則,亦可以是社會中人的各種行為的法則。這些法則,這些人都遵奉之,但其遵奉都是順才或順習的。他不但不了解此諸法則,且亦不覺有此諸法則。因其不覺解,所以說是不識不知,但他并非對于任何事皆無覺解。他鑿井耕田,他了解鑿井耕田是怎樣一回事。于鑿井耕田時,他亦自覺他是在鑿井耕田。這就是他所以是人而高于別的動物之處。
嚴格地說,在此種境界中的人,不可以說是不識不知,只可以說是不著不察。孟子說 “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生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朱子說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不著不察,正是所謂沒有清楚的了解。
有此種境界的人,并不限于在所謂原始社會中的人。即在現在最工業化的社會中,有此種境界的人,亦是很多的。他固然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但他卻亦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此種境界的人,亦不限于只能做價值甚低的事的人。在學問藝術方面,能創作的人,在道德事功方面,能做“驚天地,泣鬼神”的事的人,往往亦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 “莫知其然而然”。此等人的境界,亦是自然境界。

功利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種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為利”的。所謂“為利”,是為他自己的利。凡動物的行為,都是為他自己的利的。不過大多數的動物的行為,雖是為他自己的利的,但都是出于本能的沖動,不是出于心靈的計劃。在自然境界中的人,雖亦有為自己的利的行為,但他對于“自己”及“利”,并無清楚的覺解,他不自覺他有如此的行為,亦不了解他何以有如此的行為。
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對于“自己”及“利”,有清楚的覺解。他了解他的行為,是怎樣一回事。他自覺他有如此的行為。他的行為,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財產,或是求發展他自己的事業,或是求增進他自己的榮譽。他于有此種種行為時,他了解這種行為是怎樣一回事,并且自覺他是有此種行為。
在此種境界中的人,其行為雖可有萬不同,但其最后的目的,總是為他自己的利。他不一定是如楊朱者流,只消極地為我,他可以積極奮斗,他甚至可犧牲他自己,但其最后的目的,還是為他自己的利。他的行為,事實上亦可是與他人有利,且可有大利的。如秦皇漢武所做的事業,有許多可以說是功在天下,利在萬世。但他們所以做這些事業,是為他們自己的利的。所以他們雖都是蓋世英雄,但其境界是功利境界。
道德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種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行義”的。義與利是相反亦是相成的。求自己的利的行為,是為利的行為;求社會的利的行為,是行義的行為。在此種境界中的人,對于人之性已有覺解。他了解人之性是涵蘊有社會的。社會的制度及其間道德的政治的規律,就一方面看,大概都是對于個人加以制裁的。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大都以為社會與個人,是對立的。對于個人,社會是所謂“必要的惡”。人明知其是壓迫個人的,但為保持其自己的生存,又不能不需要之。
在道德境界中的人,知人必于所謂“全”中,始能依其性發展。社會與個人,并不是對立的。離開社會而獨立存在的個人,是有些哲學家的虛構懸想。人不但須在社會中,始能存在,并且須在社會中,始得完全。社會是一個全,個人是全的一部分。部分離開了全,即不成其為部分。社會的制度及其間的道德的政治的規律,并不是壓迫個人的。這些都是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中,應有之義。人必在社會的制度及政治的道德的規律中,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為人者,得到發展。
在功利境界中,人的行為,都是以“占有”為目的。在道德境界中,人的行為,都是以“貢獻”為目的。用舊日的話說,在功利境界中,人的行為的目的是“取”;在道德境界中,人的行為的目的是“與”。在功利境界中,人即于“與”時,其目的亦是在“取”;在道德境界中,人即于“取”時,其目的亦是在“與”。

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種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事天”的。在此種境界中的人,了解于社會的全之外,還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時,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為人者盡量發展,始能盡性。在此種境界中的人,有完全的高一層的覺解。此即是說,他已完全知性,因其已知天。他已知天,所以他知人不但是社會的全的一部分,而并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不但對于社會,人應有貢獻;即對于宇宙,人亦應有貢獻。人不但應在社會中,堂堂地做一個人;亦應于宇宙間,堂堂地做一個人。人的行為,不僅與社會有干系,而且與宇宙有干系。他覺解人雖只有七尺之軀,但可以“與天地參”;雖上壽不過百年,而可以“與天地比壽,與日月齊光”。
用莊子等道家的話,此所謂道德境界,應稱為仁義境界;此所謂天地境界,應稱為道德境界。道家鄙視仁義,其所謂仁義,并不是專指仁及義,而是指我們現在所謂道德。在后來中國言語中,仁義二字聯用,其意義亦是如此。如說某人不仁不義,某人大仁大義,實即是說,某人的品格或行事,是不道德的;某人的品格或行事,是道德的。道家鄙視仁義,因其自高一層的境界看,專以仁義自限,所謂“蹩[插圖]為仁,跽跛為義”者,其仁義本來不及道家所謂道德。所以老子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但有道家所謂道德的人,亦并不是不仁不義,不過不專以仁義自限而已。不以仁自限的人所有的仁,即道家所謂大仁。
我們所謂天地境界,用道家的話,應稱為道德境界。《莊子·山木》篇說“乘道德而浮游”, “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此是“道德之鄉”。此所謂道德之鄉,正是我們所謂天地境界。不過道德二字聯用,其現在的意義,已與道家所謂道德不同。為避免混亂,所以我們用道德一詞的現在的意義,以稱我們所謂道德境界。
境界有高低。此所謂高低的分別,是以到某種境界所需要的人的覺解的多少為標準。其需要覺解多者,其境界高;其需要覺解少者,其境界低。自然境界,需要最少的覺解,所以自然境界是最低的境界。功利境界,高于自然境界,而低于道德境界。道德境界,高于功利境界,而低于天地境界。天地境界,需要最多的覺解,所以天地境界,是最高的境界。至此種境界,人的覺解,已發展至最高的程度。至此種程度人已盡其性。在此種境界中的人,謂之圣人。圣人是最完全的人,所以邵康節說 “圣人,人之至者也。”

在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中的人,對于人之所以為人者,并無覺解。此即是說,他們不知性,無高一層的覺解。所以這兩種境界,是在夢覺關的夢的一邊的境界。在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中的人,知性知天,有高一層的覺解,所以這兩種境界,是在夢覺關的覺的一邊的境界。
因境界有高低,所以不同的境界,在宇宙間有不同的地位。有不同境界的人,在宇宙間亦有不同的地位。道學家所說地位,如圣人地位、賢人地位等,都是指此種地位說。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地位是圣人地位;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地位是賢人地位。孟子說,有天爵,有人爵。人在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地位是人爵。因其所有的境界,而在宇宙間所有的地位是天爵。孟子說;“君子所性,雖大行弗加焉,雖窮居弗損焉,分定故也。”此是說,天爵不受人爵的影響。
一個人,因其所處的境界不同,其舉止態度,表現于外者,亦不同。此不同的表現,即道學家所謂氣象,如說圣人氣象、賢人氣象等。一個人其所處的境界不同,其心理的狀態亦不同。此不同的心理狀態,即普通所謂懷抱、胸襟或胸懷。
人所實際享受的一部分的世界有小大。其境界高者,其所實際享受的一部分的世界大;其境界低者,其所實際享受的一部分的世界小。公共世界,無限的大,其間的事物,亦是無量無邊的多。但一個人所能實際享受的,是他所能感覺或了解的一部分的世界。就感覺方面說,人所能享受的一部分的世界,雖有大小不同,但其差別是很有限的。一個人周游環球,一個人不出鄉曲。一個人飽經世變,一個人平居無事。他們的見聞有多寡的不同,但其差別是很有限的。
此譬如一個“食前方丈”的人,與一個僅足一飽的人,所吃固有多寡的不同,但其差別,亦是很有限的。但就覺解方面說,各人所能享受的世界,其大小的不同,可以是很大的。有些人所能享受的一部分的世界,就是他所能感覺的一部分的世界。這些人所能享受的一部分的世界,可以說是很小的。因為一個人所能感覺的一部分的世界,無論如何,總是很有限的。有些人所能享受的,可以不限于實際的世界。這并不是說,一個人可將世界上所有的美味一口吃完,或將世界上所有的美景一眼看盡。而是說,他的覺解,可以使他超過實際的世界。他的覺解使他超過實際的世界,則他所能享受的,即不限于實際的世界。莊子所說:“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似乎都是用一種詩的言語,以形容在天地境界中的人所能有的享受。
或可問:上文說,在高的境界中的人,其所享受的一部分的世界大;在低的境界中的人,其所享受的一部分的世界小。這種說法,對于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及在天地境界中的人,是不錯的。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只能享受其所感覺的事物;在天地境界中的人所能享受的,則不限于實際的世界。他們所能享受的境界,一個是極小,一個是極大。但道德境界,雖高于功利境界,而在功利境界中的人所能享受的一部分的世界,是否必小于在道德境界中的人所能享受的,似乎是一問題。例如一個天文學家,對于宇宙,有很大的知識。但其研究天文,完全是由于求他自己的名利。如此,則他的境界,仍只是功利境界。雖只是功利境界,但他對于宇宙的知識,比普通行道德的事的人的知識,是大得多了。由此方面看,豈不亦可說,在功利境界中的人所能享受的世界,比道德境界中的人所能享受者大?

于此我們說,普通行道德的事的人,其境界不一定即是道德境界。他行道德的事,可以是由于天資或習慣。如其是如此,則其境界即是自然境界。他行道德的事,亦可以是由于希望得到名利恭敬。如其是如此,則他的境界,即是功利境界。必須對于道德真有了解的人,根據其了解以行道德,其境界方是道德境界。這種了解,必須是盡心知性的人,始能有的。我們不可因為,三家村的愚夫愚婦,亦能行道德的事,遂以為道德境界,是不需要很大的覺解,即可以得到的。愚夫愚婦,雖可以行道德的事,但其境界,則不必是道德境界。
天文學家及物理學家雖亦常說宇宙,但其所謂宇宙,是物質的宇宙,并不是哲學中所謂宇宙。物質的宇宙,雖亦是非常的大,但仍不過是哲學中所謂宇宙的微乎其微的一部分。物質的宇宙,并不是宇宙的大全。所以對于物質的宇宙有了解者,不必即知宇宙的大全,不必即知天。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已盡心知性,對于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于別的動物者,已有充分的了解。知性,則其所知者,即已不限于實際的世界。所以其所享受的一部分的世界,大于在功利境界中的人所享受的。
境界有久暫。此即是說,一個人的境界,可有變化。上章說,人有道心,亦有人心人欲。“人心唯危,道心唯微。”一個人的覺解,雖有時已到某種程度,因此,他亦可有某種境界。但因人欲的牽扯,他雖有時有此種境界,而不能常住于此種境界。一個人的覺解,使其到某種境界時,本來還需要另一種功夫,以維持此種境界,以使其常住于此種境界。
伊川說;“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致知即增進其覺解,用敬即用一種功夫,以維持此增進的覺解所使人得到的境界。關于此點,我們于以下另有專章說明。今只說,平常人大多沒有此種功夫,故往往有時有一種較高的境界,而有時又無此種境界。所以一個人的境界,常有變化。其境界常不變者,只有圣賢與下愚。圣賢對于宇宙人生有很多的覺解,又用一種功夫,使因此而得的境界,常得維持。所以其境界不變。下愚對于宇宙人生,永只有很少的覺解。所以其境界亦不變。孔子說;“回也三月不違仁,其余日月至焉而已。”此即是說,至少在三個月之內,顏回的境界,是不變的。其余人的境界,則是常變的。
上所說的四種境界,就其高低的層次看,可以說是表示一種發展,一種海格爾所謂辯證的發展。就覺解的多少說,自然境界需要覺解最少。在此種境界中的人,不著不察,亦可說是不識不知,其境界似乎是一個混沌。功利境界需要較多的覺解。道德境界,需要更多的覺解。天地境界,需要最多的覺解。然天地境界,又有似乎混沌。因為在天地境界中的人,最后自同于大全。我們于上文嘗說大全。但嚴格地說,大全是不可說的,亦是不可思議,不可了解的。所以自同于大全者,其覺解是如佛家所謂“無分別智”。因其“無分別”,所以其境界又似乎是混沌。不過此種混沌,并不是不及了解,而是超過了解。超過了解,不是不了解,而是大了解。我們可以套老子的一句話說;“大了解若不了解。”

再就有我無我說,在自然境界中,人不知有我。他行道德的事,固是由于習慣或沖動,即其為我的行為,亦是出于習慣或沖動。在功利境界中,人有我。在此種境界中,人的一切行為,皆是為我。他為他自己爭權奪利,固是為我,即行道德的事,亦是為我。他行道德的事,不是以其為道德而行之,而是以其為求名求利的工具而行之。
在道德境界中,人無我,其行道德,固是因其為道德而行之,即似乎是爭權奪利的事,他亦是為道德的目的而行之。在天地境界中,人亦無我。不過此無我應稱之為大無我。《論語》謂;“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橫渠云;“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象山說;“雖欲自異于天地,不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與天地相似”,不得“自異于天地”,可以做大無我的注腳。道學家常用“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八字,以說此境界。人欲即人心之有私的成分者,有為我的成分者。
有私是所謂“有我”的一義。上所說無“我”,是就此義說。所謂“有我”的另一義是“有主宰”。“我”是一個行動的主宰,亦是實現價值的行動的主宰。盡心盡性,皆須“我”為。“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由此方面看,則在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中的人,不唯不是“無我”,而且是真正的“有我”。在自然境界中,人不知有“我”。在功利境界中,人知有“我”。知有“我”可以說是“我之自覺”, “我之自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許多小孩子,別人稱他為娃娃,亦自稱為娃娃。他知道說娃娃,但不知道于說娃娃時,他應當說“我”。
在功利境界中,人有“我之自覺”,其行為是比較有主宰的。但其做主宰的“我”,未必是依照人之性者。所以其做主宰的“我”,未必是“真我”。在道德境界中的人知性,知性則“見真吾”,“見真吾”則可以發展“真我”。在天地境界中的人知天,知天則知“真我”在宇宙間的地位,則可以充分發展“真我”。上文所說,人在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中所無之我,并不是人的“真我”。人的“真我”,必在道德境界中乃能發展,必在天地境界中乃能完全發展。上文說,上所說的四種境界,就其高低的層次看,可以說是表示一種發展。此種發展,即是“我”的發展。“我”自天地間之一物,發展至“與天地參”。
所以在道德境界中及天地境界中的人,才可以說是真正的有我。不過這種“有我”,正是上所說的“無我”的成就。人必先“無我”而后可“有我”,必先無“假我”,而后可有“真我”。我們可以說,在道德境界中的人,“無我”而“有我”。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大無我”而“有大我”。我們可以套老子的一句話說;“夫唯無我耶,故能成其我。”

在上所說的發展中,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是海格爾所謂自然的產物。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是海格爾所謂精神的創造。自然的產物是人不必努力,而即可以得到的。精神的創造,則必待人之努力,而后可以有之。就一般人說,人于其是嬰兒時,其境界是自然境界。及至成人時,其境界是功利境界。這兩種境界,是人所不必努力,而自然得到的。此后若不有一種努力,則他終生即在功利境界中。若有一種努力,“反身而誠”,則可進至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
此四種境界中,以功利境界與自然境界中間的分別,及其與道德境界中間的分別,最易看出。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中間的分別,及自然境界與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中間的分別,則不甚容易看出。因為不知有我,有時似乎是無我或大無我。無我有時亦似乎是大無我。自然境界與天地境界,又都似乎是混沌。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中間的分別,道家看得很清楚。但天地境界與自然境界中間的分別,他們往往看不清楚。自然境界與道德境界中間的分別,儒家看得比較清楚。但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中間的分別,他們往往看不清楚。
但此各種境界,確是有的,其間的分別,我們若看清楚以后,亦是很顯然的。例如《莊子·逍遙游》說;“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此無己是大無我,到此種地位的人,其境界是天地境界。《莊子·應帝王》說;“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于于”,司馬彪說是“無所知貌”。此種人亦可說是無己的,但其無己是不知有己。在此種境界中的人,其境界是自然境界。此兩種境界是決不相同的,但其不同,道家似未充分注意及之。
又例如張橫渠銘其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即所謂東銘西銘也。此二銘,在橫渠心目中,或似有同等的地位,然西銘所說,是在天地境界中的人的話。此于本書第七章所論可見。東銘說戲言戲動之無益,其所說至高亦不過是在道德境界中的人的話。又如楊椒山就義時所作二詩,其一曰“浩氣返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與后人補”,其二曰“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此二詩,在椒山心目中,或亦似有同等地位。但第一首乃就人與宇宙的關系立言,其所說乃在天地境界中的人的話。第二首乃就君臣的關系立言,其所說乃在道德境界中的人的話。
又如張巡、顏杲卿死于王事,其行為本是道德行為,其人所有的境界,大概亦是道德境界。但如文天祥《正氣歌》所說,“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則此等行為的意義又不同。此等行為,本是道德行為,但《正氣歌》以之與“天地有正氣”連接起來,則是從天地境界的觀點,以看這些道德行為。如此看,則這些行為,又不止是道德行為了。這些分別,以前儒家的人,似未看清楚。
或可問:凡物皆本在宇宙中,皆本是宇宙的一部分。本來如是。凡物皆“雖欲自異于天地不得也”,何以象山獨于此“得力”?何以只有圣人的境界,才是天地境界?
于此我們說;人不僅本在宇宙之內,本是宇宙的一部分,人亦本在社會之內,本是社會的一部分,皆本來如是,不過人未必覺解之耳。覺解之則可有如上說的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不覺解之則雖有此種事實而無此種境界。孟子說;“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此道是人人所皆多少遵行者,雖多少遵行之,而不覺解之,則為眾人;覺解之而又能完全遵行之,則為圣人。所以圣人并非能于一般人所行的道之外,另有所謂道。若舍此另求,正可以說是“騎驢覓驢”。

所以雖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所做的事,亦是一般人日常所做的事。伊川說;“后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悌,只是一統的事。就孝悌中,便可盡性至命。至于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的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然今時非無孝悌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遺書》十八)由之而不知,則一切皆在無明中,所以為凡;知之則一切皆在明中,所以可為圣。圣人有最高的覺解,而其所行之事,則即是日常的事。此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
所以上文所說的各種境界,并不是于日常行事外,獨立存在者。在不同境界中的人,可以做相同的事,雖做相同的事,但相同的事,對于他們的意義,則可以大不相同。此諸不相同的意義,即構成他們的不相同的境界。所以上文說境界,都是就行為說。在行為中,人所做的事,可以就是日常的事。離開日常的事,而做另一種與眾不同的事,如參禪打坐等,欲另求一種境界,以為玩弄者,則必分所謂“內外”、“動靜”。他們以日常的事為外,以一種境界為內,以做日常的事為動,以玩弄一種境界為靜。他們不能超過此種分別,遂重內而輕外,貴靜而賤動,他們的生活,因此即有一種矛盾。此點我們于下文第五、第七章中另有詳論。
或問:所謂日常的事,各人所做,可不相同,例如一軍人的日常的事是下操或打仗,一個學生的日常的事是上課或讀書。上文所說日常的事,果指何種事?
于此我們說:所謂日常的事,就是各色各樣的日常的事。一個人是社會上的某種人,即做某種人的日常所做的事。用戰時常用的話說,各人都站在他自己的“崗位”上,做其所應做的事。任何“崗位”上的事,對于覺解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意義。因此,任何日常的事,都與“盡性至命”是“一統的事”。做任何日常的事,都可以“盡性至命”。
或又問:人專做日常的事,豈非不能有新奇的事,有創作,有發現?
于此我們說,所謂做日常的事者,是說,人各站在他自己的“崗位”上做其所應做的事。并不是說,他于做此等事時,只應牢守成規,不可有新奇的創作。無論他的境界是何種境界,他都應該在自己的“崗位”上,竭其智能,以做他應做的事。既竭其智能,則如果他們的智能,能使他有新奇的創作,又如果他的境界是天地境界,則他的新奇創作,亦與“盡性至命”是“一統的事”。

這一點我們特別提出,因為宋明道學家說到“人倫日用”,似乎真是說,只是一般人所同樣做的事,如“事父事君”等。至于其余不是一般人所同樣做的事,如藝術創作等,他們以為均是“玩物喪志”,似乎不能是與“盡性至命”、“一統的事”。這亦是道學家所見的不徹的處。灑掃應對,可以盡性至命;作詩寫字,何不可以盡性至命?照我們上文所說,人于有高一層的覺解時,真是“舉足修途,都趨寶渚;彈指合掌,咸成佛因”。無覺解則空談盡性至命,亦是玩物喪志;有覺解則作詩寫字,亦可盡性至命。
宋明人的語錄中,有許多討論,亦是不必要的。例如他們討論人于用居敬存誠等功夫外,名物制度,是不是亦要講求。這一類的問題,是不成問題的。如果一個人研究歷史,當然他須研究名物制度。如果一個人研究工程,當然他須研究“修橋補路”的方法。他們如要居敬存誠,應該就在這些研究工作中,居敬存誠。道學家的末流,似乎以為如要居敬存誠,即不能做這些事。他們又蹈佛家之弊,所以有顏李一派的反動。
我們于《新理學》中說,凡物的存在,都是一動。動息,其物即歸無有。人必須行動。人的境界,即在人的行動中。這是本來如此的。上文說;“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并不是平凡庸俗。對于本來如此的有充分的了解,是“極高明”;不求離開本來如此的而“索隱行怪”,即是“道中庸”。
◎本文摘自《馮友蘭隨筆:理想生活》,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4143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