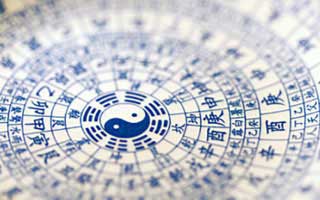大多數人每天都會吃肉。但很少有人仔細想過,我們吃的肉究竟從何而來?它們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這些動物的處境和我們又有什麼關系?
現代肉食工業興起于20世紀30年代,很快以其高效低價迅速取代傳統農業。這種肉食工業正以隱秘而深刻的方式,影響著大眾的生活。時至今日,“吃動物”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哲學議題,還是一項年產值超過1400億美元的產業,涉及全世界1/3的土地,深刻影響著海洋生態系統與氣候變化。
美國作家喬納森·弗爾花了三年時間,調研走訪美國現代肉食工業的各個環節。他結合來自政府與學術界的嚴謹數據,真實記錄所見所聞,反思工業化養殖給生態環境、公共衛生、食品安全、動物福利、勞工權益等領域帶來的嚴峻考驗。
下文經授權節選自《吃動物》(有刪節),在文中,喬納森·弗爾用詞典的形式梳理了“吃動物”這一議題的倫理面向以及鮮為人知的殘酷現實。
《吃動物》,喬納森·弗爾著,陳覓譯,新經典文化|文匯出版社2021年5月。
吃動物詞典
撰文|喬納森·弗爾
摘編|李永博
動物
造訪農場之前,我花了一年多時間閱讀相關材科:農業史、美國農業部資料、業界信息、宣傳冊、哲學書,以及形形色色涉及吃動物這一主題的書籍。人們對“痛苦”“愉悅”“殘酷”等概念的模糊定義,時常讓我困惑。很多時候作者似乎有意如此。語言從來不可信,尤其在談論吃動物時,文字總是用來誤導和遮掩,而不是交流。諸如“小牛肉”等詞語,可以讓我們忘掉它們是活生生的牛;“放養”一詞撫慰了良心不安的人;宣傳冊上的“快樂”意味著它的反面,包裝盒上的“天然”實則言之無物。
沒有什麼比人與動物之間的界限更“自然”了。然而,并非所有文化中都有“動物”一詞或與之相對應的概念——《圣經》中就沒有與英語的“animal”(動物)對應的詞。根據字典的定義,人類既是動物,又不是動物。人類當然是動物界中的一員,但我們經常用“動物”來指代除人類以外的其他生命,從猩猩到狗到蝦。每種文化、每個人對動物的理解都不同,甚至同一個人心中也可能有好幾種理解。
動物是什麼?人類學家提姆·英格爾德向社會和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生物學、心理學、哲學和神學等多個領域的學者提出這一問題。
答案五花八門,無法達成一致,但有兩點重要的共識:“首先,我們關于動物性的觀念暗含著強烈的情感;其次,客觀地審視這些觀念能夠揭露人類自我認知中的敏感區與盲點。”追問“動物是什麼”,或是給孩子講一個關于小狗或者關于支持動物權益的故事,必定會觸及我們對自身的理解,也就是追問“人類是什麼?”
擬人論
將人類經驗投射到其他動物身上。例如兒子問我喬治會不會感到孤獨。
意大利哲學家埃瑪紐埃拉·瑟納米·斯巴達寫道:
我們必須大膽賦予動物人格,因為我們必須從自身的體驗出發,來探尋動物的體驗…...(擬人論)唯一的“解藥”是不斷挑戰現有定義,以便為我們的疑惑和動物帶來的難題提供更準確的答案。
“難題”是什麼?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人類經驗投射到動物身上,我們是(又不是)動物。
層架式雞籠
擬人論就能讓我們想象待在籠子中的滋味嗎?
標準的蛋雞籠,平均每只雞的籠床面積約為0.04平方米——介于這一頁書紙和一張A4打印紙之間。籠子通常放在無窗的棚屋中,一個摞一個,通常有3到9層——日本的世界紀錄高達18層。
你可以想象自己置身于一部擠得水泄不通的電梯,幾乎無法轉身,腳都常常落不了地。這還算好的。要知道雞籠并不平整的,底部的鐵絲很容易就劃傷腳底。
不久之后,電梯中的人就會開始喪失心智,有人變得暴力,有人開始發狂。由于饑餓和絕望,少數人開始自相殘殺。
無法喘息,無法解脫。沒有維修人員會來解救你。電梯門只打開一次,在你生命的最后一刻,將你送往一個更可怕的地方。
紀錄片《肉食者》(Eating Animals,2017)劇照。該紀錄片的創作過程中受到了喬納森·弗爾《吃動物》這本書的啟發,娜塔莉·波特曼等演員參與了制作。
肉雞
不是所有雞都必須忍受層架式雞籠。單從這點來說,供食用的肉雞(不同于專門下蛋的蛋雞)算得上幸運,它們的活動空間或許能有0.09平方米。
如果你沒在農場工作過,可能會疑惑,不都是雞嗎?其實近半個世紀以來,雞分成了兩種——肉雞和蛋雞。盡管統稱為雞,但根據用途進行過基因改造后,兩者的身體和新陳代謝截然不同。蛋雞產蛋(20世紀30年代以來,蛋雞的產蛋量翻了一番),肉雞產肉(肉雞能長到原來的兩倍大,且只需花費原先一半的時間,日均生長速度增加了3倍。雞的壽命原為15到20年,但現在的肉雞普遍只能活6周。)
我腦中冒出無數個千奇百怪的問題——在得知有兩種雞的存在之前我從沒想到過的問題——例如,那些蛋雞的雄性后代會怎樣?它們無法下蛋,又不被賦予肉的功能,那它們有何用處呢?
什麼用都沒有。蛋雞所產的小公雞——美國一半的蛋雞,每年約2.5億只——一律被處死。
處死?似乎有必要了解細節。
大多數雄性蛋雞會被吸入管道,送至電板,執行死刑。除了被電死,其他死法也一樣慘,要麼被扔進大型塑料容器,弱小的被踩壓到底部,強壯的躺在頂部,全都慢慢窒息而死。要麼被活著送進絞碎機(想象一臺木材切削機中塞滿小雞)。
殘忍嗎?取決于你對殘忍的定義。
殘忍
故意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并且冷漠待之。變得殘忍比我們想象中容易。
人們常說自然冷酷無情。農場經營者尤其愛說這句話,試圖表明他們是在保護農場動物免受外界疾苦。大自然當然不是郊游的地方,頂級農場中的動物也的確過得比在野外更舒適。但自然并不殘忍,野生動物也不會隨意殺戮或折磨其他生命。是否殘忍取決于我們如何定義殘忍,以及我們是選擇反對它還是漠視不理。
放養
常見于肉類、雞蛋、奶制品的標簽上,偶爾連魚類也會標上(放養金槍魚?)。然而這個標簽跟“純天然”“新鮮”“神奇”一樣,完全是胡扯。
符合放養標準的肉雞必須“能接觸戶外”,細想之下你會發現,這就是句空話。(試想,3萬只雞擠在一個雞棚中,只有一扇偶爾才會打開的小門,通向一塊5米見方的泥地。)
至于散養蛋雞,美國農業部沒有嚴格定義,全看農場的說辭。很多工業化農場出產的雞蛋——那些擠在大谷倉中的母雞下的蛋——都被打上“放養”標簽。(還有“非籠養”標簽,顧名思義,下蛋的雞不是養在籠子里,這點倒沒錯。)也就是說,“放養”(或“非籠養”)的雞同樣可能被去喙、喂藥,一旦產量下降就被殘忍屠宰。我完全可以在洗碗槽底下養一群雞,同時宣稱它們是“放養”。
新鮮
更是胡說。根據美國農業部的規定,“新鮮”雞肉的溫度必須維持在約零下3攝氏度到零下4攝氏度之間,可以冷凍(因此有了自相矛盾的說法“新鮮冷凍”),但沒有明確規定保鮮期。受病原體感染或糞便污染的雞也可以說是新鮮、非籠養、放養的,并在超市合法出售(只要將糞便清洗干凈)。
紀錄片《肉食者》(Eating Animals,2017)劇照。
人類
人類是如此獨一無二的物種,會有目的地繁衍后代、與他人保持(或斷絕)聯系、慶祝生日、浪費時間、刷牙、懷舊、清除污漬、信仰宗教、成立政黨、制定法律、把紀念品穿在身上、在犯錯多年之后道歉、說悄悄話、擔驚受怕、解夢、遮掩生殖器、刮胡子、埋藏時間膠囊以及出于道德考量選擇不吃什麼。但無論選擇吃肉與否,背后的邏輯往往是一致的:我們和它們不一樣。
KFC
KFC原意是肯塔基炸雞(Kentucky Fried Chicken),現在大家都忘了,所以KFC三個字母變得毫無意義。KFC對雞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傷害。他們每年要購買近10億只雞——一只一只摞起來,足以覆蓋整個曼哈頓,還會從高樓的窗戶溢出來。KFC的運作方式對整個雞肉行業影響甚巨。
KFC堅稱其“關心動物福利,堅持以人道方式對待雞”。這些話的可信度如何?在一家為KFC供貨的西弗吉尼亞州的屠宰場,員工曾砍下活生生的雞的頭,將煙吐到雞的眼睛里,朝它們的臉噴漆,將它們重重地踩在腳下。這些行為多次被人目擊,而這家屠宰場并不是“一粒老鼠屎”,而是“年度最佳供貨商”。難以想象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真正的“老鼠屎”是什麼樣。
KFC在官網上聲明:“我們持續監管供貨商,以確保他們的飼養與處理過程足夠人道。我們致力于挑選符合高標準的供貨商,與我們共同實現關懷動物福利的承諾。”這句話半真半假。KFC的確只和承諾保障動物福利的供貨商合作,但官網上沒有告訴我們的是,供貨商有權自行定義動物福利的標準。
KFC對供貨商進行的稽查(即上文中所說的“監管”)同樣是典型的公關行為。這些事先張揚的稽查給了供貨商足夠的時間應對,將見不得人的部分藏起來。不僅如此,稽查報告完全忽視了公司專門聘請的動物福利專家的意見,五位專家因此憤然辭職。其中一位專家阿黛爾·道格拉斯告訴《芝加哥論壇報》,KFC“從未召開過相關會議,也沒征求過專家意見,卻向公眾宣傳他們組建了動物福利顧問委員會。我覺得自己被利用了”。另一位前委員會成員、圭爾夫大學動物福利協會榮譽主席伊安·鄧肯,是北美禽類福利方面首屈一指的專家,他指出,“改進實在太慢,這是我辭職的原因。任何事都被往后推,標準遲遲不定......我懷疑管理層根本不在乎動物福利。”
取代這五名委員的是誰?在那之后,KFC動物福利委員會成員包括皮爾格林普拉德公司副主席——前文提到的虐待動物的“最佳供貨商”正是由這家公司運營;泰森食品公司董事——該公司每年屠宰22億只雞,其雇員多次被發現在肢解活的火雞(還有雇員在屠宰線上小便);還有公司自己的“高管及其他雇員”。簡而言之,KFC所謂的監督供貨商的顧問,就是供貨商本身。
與KFC這個名字一樣,該公司在動物福利上的承諾毫無意義。
KFC官網展示的產品示意圖。
PETA(善待動物組織)
善待動物組織(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的英文縮寫與皮塔餅發音相同,但在我遇到的農夫中,這一動物保護機構遠比這款中東食物出名。它是世上最大的動物權益機構,成員超過200萬名。
在合法的前提下,他們極力地推進自己的主張,絲毫不顧忌自身形象(這點令人折服),也不管冒犯了誰(這點不敢恭維)。他們派發給孩子的“不快樂套餐”,包含渾身是血、揮舞著剁肉刀的麥當勞玩偶。他們制作西紅柿圖案的貼紙,上面寫著“把我扔到穿皮草的人身上”。他們還去四季酒店把死掉的浣熊放到《時尚》雜志主編安娜·溫特的餐桌上(把生蛆的動物內臟寄到她辦公室),破壞從政要到皇室等各界名流的畫像,向兒童分發“你爸爸殘殺動物!”的傳單,還要求寵物店男孩(Pet Shop Boys)樂隊改名為“動物收容所男孩”(樂隊并未照辦,但承認這個問題值得討論)。這些一根筋的行為讓人覺得好笑又可敬,但顯然沒人希望他們把矛頭對準自己。
無論名聲如何,善待動物組織比其他任何機構都更讓工業化養殖業感到恐懼。美國最著名、最有影響力的動物福利科學家坦普·葛蘭汀(美國一半以上的屠牛場都由她設計)說,在善待動物組織盯上快餐行業后,動物福利1年之內的改善幅度比過去30年的總和還要大。該組織的頭號敵人史蒂夫·科佩魯德(肉類工業顧問,10年來一直致力于研究反抗善待動物組織的對策)如是說道:“這個行業內,人人皆知善待動物組織的能耐,不少高管都聞之色變。”聽說不少公司會定期與善待動物組織協商,并悄悄改善公司的動物福利政策,以避免受到該組織的公開責難。對此我一點兒也不驚訝。
善待動物組織有時被指以極端手段獲取關注,此言非虛。還有人指責他們宣揚動物與人類應該受到平等對待,這有失偏頗。(什麼叫“平等對待”?讓牛投票嗎?)他們并非情緒化的烏合之眾;相反,他們十分理智,堅定地推行樸素的理想——“動物不是供我們食用、穿戴、做實驗或娛樂的”,他們努力讓這句口號就像穿泳裝的帕米拉·安德森一樣深入人心。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他們支持安樂死:如果讓一只狗終其一生關在狗籠中或者安樂死,善待動物組織會選擇后者,還會廣泛提倡這一理念。他們當然反對殺戮,但他們更不愿動物遭受折磨。善待動物組織的成員都很喜歡貓狗,他們的辦公室里總有不少寵物相伴,但他們的目標并非激發人們善待小貓小狗。他們想要的是一場變革。
他們稱這場變革是為了爭取“動物權利”,但總的來說他們為農場動物(他們的關注重點)爭取到的,與其說是權利,不如說是福利:更大的飼養空間、更規范的屠宰方式、更舒適的運輸條件,等等。善待動物組織的手段常有嘩眾取寵之嫌,但這些“過火”行為取得的改善結果大部分人都不會覺得激進。(有人會反對更規范的屠宰方式和更舒適的運輸條件嗎?)所以,關于善待動物組織的爭議可能不在于其過激行為,而在于它令我們羞愧——換言之,善待動物組織成員在為我們出于懦弱或忘性而拋棄的價值觀奮斗。
善待動物組織網站上發布的動物權利大會的活動信息。
激進
事實上,人人都同意動物也有痛覺,分歧在于它們能夠感覺到的疼痛程度,以及我們的在乎程度。經調查,96%的美國人認為動物應該受到法律保護,76%的人認同動物福利比低廉肉價重要,還有超過60%的人認為應當通過“嚴格立法”規范農場動物的飼養。大概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大眾意見如此一致的社會議題。
另一個大部分人都能達成共識的是環境的重要性。無論你是否贊成近海石油開采,無論你是否相信全球氣候變暖,無論你是開著大排量車還是離群索居,你大概都會同意每天呼吸的空氣和飲用的水十分重要,并且對子孫后代也同樣重要。即便那些始終否認環境出現危機的人也同意,環境惡化是件糟糕的事。
美國人直接接觸的動物中,超過99%是農場動物。至于我們對“動物世界”造成的影響——無論是讓動物遭受折磨,還是破壞生物多樣性,后者已經打破數百萬年進化達成的物種間平衡——這些都比不上飲食選擇帶來的后果。在我們的所作所為中,沒有什麼比吃肉對動物造成的傷害更大;同樣,在我們的日常選擇中,沒有什麼比飲食對環境的影響更大。
我們處于一個奇怪的境地。幾乎所有人都同意要善待動物、保護環境,卻鮮有人認真思考過我們與動物和環境的關系。更奇怪的是,按照這些價值觀行事,拒絕吃肉(每個人都認為這既能減少受虐動物的數量,也能減少一個人的生態足跡),往往會被認為是邊緣行為,甚至是激進之舉。
紀錄片《肉食者》(Eating Animals,2017)劇照。
物種屏障
柏林動物園里豢養著約1400種動物,是世界上物種最豐富的動物園。它建于1844年,是德國第一家動物園,最初的動物來自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捐贈。它每年的客流量高260萬,是歐洲最受歡迎的動物園。1942年,盟軍空襲摧毀了動物園的全部設施,只有91只動物幸存。(當時的柏林,連公園里的樹都被砍得一干二凈,拿去當柴火,能有動物幸存簡直是奇跡。)如今動物園共有15000只動物,然而明星只有1個。
2006年12月5日出生的克努特,是柏林動物園30年來迎來的第一只北極熊。他的媽媽托斯卡20歲,是德國馬戲團退休的表演熊,她拒絕喂養幼崽,克努特的孿生兄弟出生4天后死亡。聽上去像一部平庸電影的開頭,然而對一個幼小生命而言著實艱難。小克努特在保溫箱中度過了最初的44天。他的飼養員托馬斯·德爾夫萊恩睡在動物園,以便24小時照顧他。他每隔2小時用奶瓶給克努特喂一次奶,用吉他給睡前的克努特彈奏貓王的《偽裝的惡魔》,還常常被大吵大鬧的克努特弄得滿身是傷。克努特出生時只有0.8千克,3個月后我去動物園時,他的體重已經翻了一倍。一切順利的話,他的體重將達到出生時的200倍。
任何語言都不足以形容柏林人對克努特的愛。市長克勞斯·沃維萊特每天早晨都會搜索新聞,看克努特的新照片。柏林市冰球隊北極熊隊向動物園申請讓克努特當球隊吉祥物。包括柏林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每日鏡報》在內,許多媒體都開設了博客,專門報道克努特的日常活動。克努特不僅有自己的播客和網絡直播節目,還取代了很多日報上的半裸模特。
克努特的首次公開亮相吸引了400多名記者,風頭完全蓋過當時正在召開的歐盟峰會。克努特領帶、克努特背包、克努特紀念盤、克努特睡衣、克努特塑像都熱銷一時,可能(盡管我沒有確認)還有克努特內褲。德國環境部長西格馬·加布希爾是克努特的教父。克努特的明星效應造成了另一只動物熊貓嫣嫣的悲劇。據工作人員推測,每天多達3萬名游客涌入動物園看克努特,令嫣嫣過度興奮或壓力過大,導致了她的死亡。說到死亡,一個動物權益組織提出——他們后來宣稱只是假設——對一只動物實施安樂死,也比讓它生活在動物園那樣的環境要好,為此大批小學生走上街頭高喊“克努特必須活下去”。連球迷也拋開自己支持的球隊轉而為克努特吶喊。
如果你去看克努特時肚子餓了,它的圈舍不遠處就有小攤出售“克努特香腸”,這些肉來自工業化農場飼養的豬,它們的智力絕不遜于克努特,然而我們不屑一顧。這便是“物種屏障”。
紀錄片《肉食者》(Eating Animals,2017)劇照。
壓力
業界用這個詞來替代下面這個詞:
痛苦
什麼是痛苦?這個問題假定了談論的對象具有痛感。如今,動物會“感到疼痛”已是共識,但有不少觀點認為動物遭受的痛苦——在一般的心理、感情或所謂的“主觀”層面——與人類的痛苦不具可比性。我想很多人都這麼認為,即動物的痛苦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并不是真的要緊。
我們都本能地知道什麼是痛苦,但很難用語言表達。從小到大,我們通過與其他人(尤其是家庭成員)以及動物的互動,了解到痛苦的含義。痛苦這個詞暗示著某種對其他生命的感同身受——一種共通的生命體驗。當然,人類有自己獨特的痛苦——夢想破滅、種族主義、身體羞恥,等等。但這就足以證明動物的痛苦“不是真正的痛苦”嗎?
對于痛苦的定義及相關思考,重要的不是我們被告知的概念——神經通路、傷害性受體、前列腺素、阿片受體,等等——而是誰在遭受痛苦,以及我們如何看待那樣的痛苦。或許,某種哲學能設想出一個世界,在那里痛苦的定義不適用于動物。這有悖常識,但我承認這種可能性。如果認為動物并不真的有痛感與認為它們有痛感的雙方,都能提供強有力的證據,我們是否就應對此半信半疑呢?是否就應認定動物并不真的痛苦——或者至少它們的痛苦無關緊要呢?
我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我不想在這一點上爭論。我只想指出,當我們問“什麼是痛苦”時,必須意識到問題的核心是什麼。
什麼是痛苦?我不知道它是什麼,但我知道痛苦是所有嘆息、尖叫和呻吟的原因,這些聲音無論是大是小,是嘶吼還是哀鳴,都牽動我們的心。這個詞比我們所見之物更能定義我們的內心。
撰文|喬納森·弗爾
摘編|李永博
導語校對|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