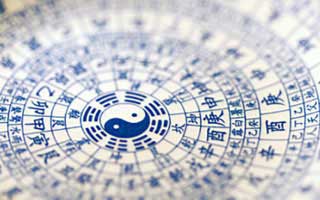本文來源于 真實故事計劃(id:zhenshigushi1),歡迎關注及投稿,符合者將獲得【1800元或2500元/每篇】稿酬。
在醫院陪床,要與病人朝夕相處,陪護病人已經身心俱疲,更有甚者還要親歷死別。一些經歷陪床的年輕人說,那是一次親情與個人發展之間的抉擇。他們中的很多人,經歷糾結,當家人突發疾病,他們在工作學業和照顧家人之間作出權衡,許多人暫時放棄了原有的人生進程,為了自己的責任,選擇陪護在家人身邊。親歷醫院陪護,他們對親情、責任以及生死有了更多切身體會。
第一次陪床,第一次無措
Dana 20歲時第一次陪護20歲那年,我獨自一人在醫院陪護做完腰椎手術的爸爸。第一次準備幫父親擦澡,作為女兒的我,還沒有開始就陷入無限的糾結。我肯定會因為害羞不敢看他的身體,也可能因為害怕弄疼他不敢用力。結果,拿著毛巾杵在床邊站了半個小時,最后是病房里一個護工叔叔幫的忙。
向上 25歲時第一次陪護上完一天班,就碰到晚上爺爺出事住院。因為是疫情期間,醫院只能允許一位家屬陪護,我留了下來。從進醫院當晚到第二天中午,我沒敢合眼。平時我早睡,很少熬夜,那天晚上不知道怎麼地就撐下去了。
陪護期間,我還要負責簽醫生給我的一堆通知書,它們告訴我這是什麼病,需要做什麼樣的手術,成功率是多少。
爺爺病情比較急,當時就做了手術。那種手術擁有5%的失敗率,雖然很低,但放在我的爺爺身上,我還是很擔心。醫生說術后還有危險需要一直盯著,我就真的一晚上沒敢合眼。因為和爺爺很親,那天晚上更加難熬,除了身體要撐著時刻關注老人的狀況,我還躲在一邊偷偷哭。
珍惜當下吧,多陪陪家人,孝順老人。那天晚上的陪床我想了很多很多,小時候爺爺奶奶經常帶我去旅游,等我爺爺出院康復后,我要帶他去旅游,還要買個監控安在家里平時看看他們,也能記錄一些生活片段當做美好的回憶。后來我爺爺出院,我帶我爺爺奶奶去了五臺山燒香拜佛,也算是逛一逛。
吹門風 20歲時第一次陪護外婆的尿袋滿了,我要把尿袋開關打開,用盆接住里面的液體,端到衛生間倒掉,再把盆沖洗干凈放回原地。每天上午,外婆要掛五六瓶不等的點滴,我得看著,一瓶快吊完了,及時喊過來拔針,不然空掉的點滴管會把血液從外婆的血管里抽出來一截。可每天掛這麼多瓶點滴,一日三頓按時按量吃藥,每天晚上外婆還是會疼醒,痛得直哼哼。
外婆生養了5個孩子,年輕時沒有好好養著,一輩子病痛沒斷過。后來年紀大了,脾氣更差,一點小事就會暴跳如雷。
那天下午,姨父過來送飯,語氣上有些冷淡發牢騷,外婆感覺到了,筷子一扔就罵了起來。她耳朵不好,罵人時嗓門更大了。我一邊哄她,一邊小聲讓姨夫快點走。半個小時后,終于好了些,但她堅決不吃姨父帶來的飯,我又去樓下食堂買了一份上來弄給她吃,病房才平靜下來。
晚上十點多,我回家洗完澡準備回醫院,就接到外婆的主治醫生打來的電話,說外婆大吵大鬧著要回家,他們攔不住了。我火急火燎趕過去,住院部熄了燈,外婆一個人穿著病號服坐在樓梯旁,身上還掛著尿袋,口里念叨著所有人都要害她。
我感覺太陽穴突突地跳起來,走過去想拉她回病房。外婆只有七十多斤,但是犟起來我幾乎拉不動她。一回頭,還看到兩位主治醫生無措地站在不遠處,我喊他們幫忙,才把人“架”回了病房。四五米遠的走廊,她罵了一路,用詞是農村罵街常用的臟話。病房里的病人聽到聲響,不斷有人開門出來張望,我感覺那段路是那麼漫長。
到了病房,我又羞又氣,控制不住吼她:“你就不能安分點嗎?我們哪點對你不好了?”
人在失去理智的情況下,能說出很多帶刀子的話,那一刻我跟外婆同樣瀕臨崩潰。發泄了十分鐘左右,同病房的一個奶奶開始勸我:“你外婆年紀大了,一個人在這兒害怕,今天醫生又說要做穿刺,她偷偷跟我們說她不想做,肯定會很痛的……”
后來醫生開了一針安定給外婆,我坐在床邊,好一會兒才傳來勻勻的呼吸聲,心才算放下了。我到樓道抽了支煙,一整晚都沒有睡意。
雪楠 35歲時第一次陪護35歲那年,我第一次陪母親住院。她得了抑郁癥,中度,急性發作期,醫院不允許抑郁癥患者獨自住院,我也覺得自己應該去陪護。精神專科醫院有些不同,即便患者行動自如、溝通無障礙,所有跟醫生護士的溝通,也都要求讓家屬去,所有點滴、理療都要家屬陪著才可以。
剛開始,母親抗拒吃藥,說吃藥難受,控訴醫生非要逼著她吃。每次哄母親吃藥,我都會想起《哈利·波特》里,哈利給神志不清的老校長鄧布利多灌魔法藥水的那一幕。在醫院里的每一天,我都要陪著母親一直說話聊天,要輕松愉快,還要理解她、安慰她。一次我說到,抑郁癥發展到這個程度,也是我這個做女兒的疏忽了,以后我一定多陪陪你,多關心你。我媽哭了。
那是個熬人的環境。置身其中,你會覺得周圍的人多少都有些不正常。有時候,你和一個看起來很正常的人聊天,對方的家屬卻一臉防備地看著他,擺出時刻準備控制住他的姿態,這讓我害怕。不過直到出院,我也沒遇到什麼亂子。
以前,我只覺得母親性格古怪,現在知道是抑郁癥的緣故,就更加關心她。出院后,我看了一些關于抑郁癥的書,對母親就更加包容了。我知道她的敏感點在哪里,也知道一旦她進入那個狀態,要怎樣等待她慢慢走出來。
那次陪伴母親出院后,我開始關注周遭每個人的心理狀態,有人狀態不對,我會更加細心地去開解,而不是喝一頓酒,吵吵幾句“沒啥事兒”就過去了——我現在知道,抑郁癥過不去,人只能慢慢找到與它共存的方式。
蘑菇 15歲時第一次陪護患癌后,媽媽沒有化療,直接進行了手術。那時候我剛中考完,家里的大人都要忙,只能由我陪護媽媽住院。
一天傍晚,我陪媽媽去逛醫院旁的批發市場。她開心得像個孩子一樣,挑了一件綠色的衣服,說那是“生命的顏色”。回去我幫她把新衣服先洗一遍,結果那衣服掉色嚴重,把滿滿一盆水染成了綠色,衣服的顏色掉了不少,變成了淡綠色。我一下子就慌了,在衛生間抱著那盆水和衣服嚎啕大哭。
小月月 27歲時第一次陪護爸爸血栓突然復發、媽媽在外地做手術、秋招0 offer——今年10月,這些事一齊壓在我身上。
姥姥、姥爺負責照顧媽媽,我負責陪護爸爸,主要就是買飯、打水、看吊瓶。我是應屆畢業生,當時趕上秋招。有場筆試被安排在上午10點到12點。爸爸躺在病床上輸液,我在旁邊支了個小桌子,在電腦上做題。題目很多,我怕答不完,開始前還囑咐爸爸:“盡量不要和我說話。”但有些事避不開。醫院中午11點開午飯,去晚了可能買不到飯菜,我總不能讓爸爸提著吊瓶去買飯。糾結了有10分鐘,還是爸爸吃飯要緊,我急忙跑去醫院飯堂買了飯,再繼續答題。最后沒能答完,卡著時間交上去,當時我就知道肯定沒戲了。
我一直撐著,直到陪護第3、4天左右,我回家看到貓突然吐紅色沫子,一下子憋不住,蹲在浴室里哭得停不下來。那段日子積攢的壓力全部爆發,我哭到嗓子都變了聲。
圖|打印完病例,終于平安出院
為陪護親人暫停事業的進程
Zian 23歲時第一次陪護收到媽媽發來的微信時,我正在劇組實習。看到“爺爺腦梗了”5個字,我在劇場里一動都不敢動。
我很糾結要不要回去陪護。我沒有任何影視相關背景,對我這樣的人來說,得到這次進組實習的機會來之不易。中途離開,我不知道之后還能不能遇到這樣的機會。而且我當時還有一周就要提交畢業論文終稿,回去陪護,也意味著要背上因完成不了畢業論文,畢不了業的風險。
但想到我居然為了自己的工作和學位猶豫要不要照顧家人,又覺得自己很可恥。
考慮了十幾分鐘,想到腦梗一般都會在急診過道或者卒中急診門口留觀,條件很艱苦。我爸慢性疾病也很多,所以想回去替他減輕一點負擔。趁著拍攝間隙,我向劇組領導請假,在領導的幫助下,坐劇組的車連夜趕回了家。之后一周,掛號、開藥、付費、取藥、買飯、陪爺爺輸液、帶爺爺做檢查,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我只能在門診化療室門口用手機修改論文。
看著爺爺一點點好起來,自己作為陪護者被爺爺信任和依賴,我慶幸當時劇組領導幫我堅定了我的選擇。他什麼都沒說,一系列的安排就是在告訴我:工作沒有家庭重要。
曹宇 25歲時第一次陪護父親因突發腦溢血做開顱手術那天,正好是我公務員面試的日子。大學畢業后,我遵從父母意愿回家考公,筆試考了第一名,不出意外面試問題不大。當時其他人還沒趕回來,只有我一人陪護。手術前一天,我坐在父親的病床前,想著一面是安穩的工作,一面是只有一次的親情,無法兩全。最終促使我放棄面試的只有一個念頭:希望在外邊工作一年后回家叫一聲爸媽,還能有人回應。
我永遠忘不了透過ICU的玻璃看到的場景,父親鼻子插著管,帶著呼吸機,頭被白紗布包著。那時我每次看著近1米長的賬單,都在祈禱父親趕快醒過來。轉進普通病房后,父親需要24小時看護,我和母親輪流給他做康復訓練。不到一周,父親的手指動了一下,那之后他的手慢慢可以動了,然后是腿和整個身體有勁兒了。一個月后,父親出院,我們一家人終于松了一口氣。現在六年過去,我養成每周給父母打電話的習慣。每次回家能叫聲爸,我都覺得很幸福。
JESSIE 25歲時第一次陪護25歲的時候,我在杭州工作。原本計劃打拼7、8年后,就能在杭州買房定居,把在河北老家的父母接到身邊照顧。
2019年12月,我在出差期間突然接到父親的電話,說母親的咳嗽加重需要住院,必須有家屬陪同以隨時調整治療方案,來詢問我的意見。我沒怎麼猶豫,交接工作、請假、買動車票,還算冷靜。但從得知這個消息開始,我的心里就亂糟糟的。平時我坐車就睡覺,但那天四個半小時的車程,我沒有絲毫睡意,全程揪著心。
回家路上我才意識到,父母都已經50多歲,我無法保證他們能等到我攢夠房子首付的那一天。我第一次生出回家工作的念頭。但是那時我已經在公司工作三年多,即將升任主管,薪資預計是原來的三倍,離職則意味著重新找工作,從零開始。
回家后我帶母親去省城一家醫院,CT、抽血、超聲波等各種檢查都做了一遍。印象最深的檢查是經食管超聲心動圖,我看著母親側躺在床上,像手指一樣粗的超聲探頭伸入她的口中,為的是經過食管插入到心臟后方檢查心臟內部情況。但事實上母親喝麻醉藥時就一直干嘔,探頭根本無法插入,最后不得不放棄。
圖|母親當時的報告單
我把做完檢查的母親送回病房,醫生把我單獨叫到辦公室,說懷疑母親是淀粉樣變心肌病,這種疑難雜癥即便確診也沒有太好的治療方案。聽到“只有5年生命”時,我一下子就被嚇哭了,邊流淚邊用手機查這個病。母親做檢查的痛苦畫面和醫生的話不停出現在我腦海里,我就在想自己如果連父母都照顧不好,升職加薪又有什麼用呢?于是當天下午我直接向領導提出辭職。
我全程陪護了二十天,讀大學之后我已經很久沒有和母親這樣朝夕相處了,我們兩個的角色仿佛被交換,她變成了需要我照顧的“小孩子”。好在母親平安出院,我也在老家鄰近的城市工作、定居。現在想來,從被照顧到照顧家人,大概就是這次陪床帶給我的成長。
嚴曉君 19歲時第一次陪護2000年冬天,父親心臟病復發同時誘發尿毒癥,主治醫師判斷,父親很可能挺不到年底。
當時我正備戰高考。我的家庭條件貧苦,高考是我們這樣家庭的孩子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我很清楚這點,但當時我一心想的是:錯過高考還可以復讀,但是我只有這一個父親。唯恐錯過父親最后的生命時光,我向學校請假在醫院陪護。我們不敢告訴父親具體情況,他一直責怪母親:“高考這麼緊張,這不耽誤他時間麼?”
陪床的日子里,我看著父親的身子一天天腫脹起來,全身疼痛越發嚴重,到最后連個囫圇覺都睡不了。有一次,他直接從床上翻下來,跪倒在地上,嚷嚷著受不了。一天傍晚,父親讓我扶他坐起來,他靠在我身上,很虛弱地和我說:“咱家存折上有一萬塊錢,你考上大學后,可以用一段時間。”我哭著點點頭,說不出任何話。就在當晚,父親走了。
嚴格來說,我在醫院陪床的日子不多,但回到學校后,我總會走神想起父親躺在病床上虛弱的樣子,然后幻想有人把我從教室叫出去,說父親又活了。
后來,我還是考上了大學。某天晚上,我夢見和父親在一個不大的澡堂池子里并排坐著,一個出水口在我倆中間嘩嘩流水,我倆沒說任何話,就那麼一直哭,一直哭。
生死之外,都是小事
零 23歲時第一次陪護我從小被外婆帶大,我18歲那年她患了阿爾茲海默癥。疫情期間我在家里準備本科畢業答辯,外婆盆骨骨折住院,我和媽媽一起在醫院陪護了24天。我每天喂外婆吃飯喝水,侍候她大小便。她便秘導致幾天一次大號,我要拿盆接,很臭很惡心。因為癡呆有時候她自己動手去挖,等到清醒她又覺得難堪,我既心酸又難過。
媽媽的生日是在醫院過的,那天傍晚外婆難得清醒,拉著我說起媽媽小時候的糗事。等外婆睡著后,媽媽特別鄭重地和我說:“父母是擋在死神和孩子面前的那堵墻。”我知道,她在害怕自己面前的那堵墻倒下。
圖|病房里看到的溫馨一幕
小鑫 20歲時第一次陪護爸爸患惡性腫瘤的第六年,病魔在他體內肆意流竄作案。那年我20歲,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媽媽告訴我假期爸爸要住院治療,我責無旁貸一起陪床。
我負責陪護爸爸,保證媽媽在醫院跑手續、找醫生、做飯時爸爸病床邊不離人。當時爸爸身體虛弱到極致,上廁所都需要人攙扶借力。每到上廁所,他都會強迫癥發作。家里買的衛生紙,會有較光滑和較粗糙的一面,他上完廁所出來,手把手教我辨別這兩面,叫我把光滑那一面折在外面放手邊。當時不覺有什麼,現在想來這竟是爸爸親手教會我的最后一件事。眼看著假期快要結束,不知道爸爸要住院到什麼時候,也不知道我返校后媽媽一個人要怎麼辦,還有,我不知道爸爸這次還能不能出院。
有一天吃完午飯跟媽媽去刷碗,在水房我問媽媽,爸爸還要住到什麼時候。媽媽一聲不吭,后來想想我那麼問怕是在她心上扎了一刀,畢竟爸爸當時情況已經很不好。
后來,父親真的沒有出院。姐姐從外地請假回來,當晚的我仿佛被抽離到半空,看著病房里發生的一切,每一分每一秒都漫長到崩潰。
我從此羨慕那些有爸爸的人,從此明白“久病床前無孝子”不是玩笑話。我也清楚,我有了新的使命,也就是代替爸爸照顧媽媽。我后來和對象講過這些故事,他說,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我嚎啕大哭。
小秋 18歲時第一次陪護18歲,我在手術室外決定給父親用什麼材質和價格的心臟支架、簽手術同意書。在醫院陪護的那一個多月里,我見了太多喪失自理能力的人,當時最大的體會就是,當一個人面對疾病甚至死亡,屬于他的社會身份都失效了。無論性別、年齡、地位如何,在不可避免的死亡面前都是無力的。
Y 17歲時第一次陪護媽媽做闌尾炎手術住院,我在假期陪床。一天凌晨1點多,媽媽可能是睡覺不小心扯到了傷口,痛得出汗,我不敢耽擱,跑去找醫生護士。夜里的醫院走廊真的很刺激,我不是個信奉鬼神的人,但穿過走廊就覺得踏遍了生死輪回。在這個地方,只要死神發牌,誰都得接著。
丹丹 22歲時第一次陪護研一寒假前夕,爸爸突發腦出血進醫院,術后觀察階段出現了狀況,被搶救過來后就陷入昏迷。直到我寒假開學,爸爸的病情都沒有很穩定。
腦出血病人很容易發生癲癇。一天上午醫生剛查完房,我實在太困在病床邊打盹,爸爸輸著液,突然開始全身抽搐,我當時被嚇懵了,害怕他咬到舌頭,情急之下把手伸進了他嘴巴里。醫生及時趕到采取急救措施,但是沒一會兒爸爸就又開始抽搐,血氧飽和度越來越低,爸爸嘴里像是有痰堵住了,無法呼吸。監護儀上的數字一直往下掉,醫生直接在病房里做了氣管切開手術。我忘記害怕,只想著要配合醫生救他。怕爸爸亂來,我在慌亂中握住了他的雙手。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必須留下來,因為不敢想象再有這種意外發生。
圖|爸爸清醒時我們寫給他的話
我一開始申請了暫緩開學注冊,延遲兩周返校。那天我直接聯系導師和輔導員,和他們商量決定申請退掉課程,等到下學年重修。
爸爸后來進出綜合ICU數次,病情反反復復,換了近10次床位。每天早上醫生的查房、讓人喘不過氣來的各種檢查和賬單時刻都在提醒著我:這是離死亡很近的地方。
我們和爸爸在醫院里戰斗了139天,6月11日凌晨4點55分,他還是離開了。那天夜里,我來回跑了三次喊急救的值班醫生,每一次都是和醫生在走廊狂奔。第三次,心電圖變成直線。媽媽已經慌了神,我強裝鎮定處理后事,等父親的遺體告別儀式結束,我才意識到,我真的沒有爸爸了。
回校后,我重修了之前落下的課程。妹妹的高考分數是611分,和爸爸離開的時間一樣,像是一種祝福和紀念。對于暫時放棄學業陪護爸爸這個選擇,我從未后悔過,唯一的遺憾就是和爸爸分別得太久了。我想大部分人在面對這樣的情況時,都會做和我類似的決定吧,因為那是我愛的家人啊。生死之外,都是小事——這是我在22歲學會的道理。
- END -
本期策劃 | 宮宇凡
編輯 | 溫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