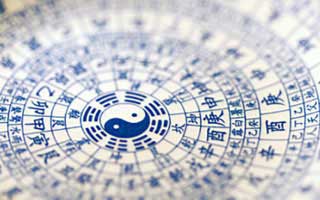清錢大昕曾說:在司馬遷以前,“古者列國之史,俱稱《史記》” [1]。王利器先生據之,舉證達四十三例之多[2]。可是如將王先生所舉諸例仔細讀之,再聯系有關史料,便可發現,準確地說,這些例子中的“《史記》”,很可能本應理解為“史《記》”(或“《史 < 記 > 》”[3])而不是今人觀念中的“《史記》”。此“史”是史官之“史”,而不是文史之“史”、歷史之“史”。
一
1 .《竹書紀年》周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王國維疏證以為此“王”、此“左史戎夫”,即《逸周書·史 < 記 > 解》中之“王”與“左史戎夫”。其原文是:“王……召三公、左史戎夫。……取遂事(指歷代亡國者二十八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聞”。晉孔晁注“集取要戒之言,月朔日望于王前讀之” [4]。可見此“主之”即當理解為首先要“作《記》”,然后方可“于王前讀之”;而《史 < 記 > 解》之“史 < 記 > ”原本稱《記》 ,因是“左史”所記,故又稱“史《記》”,其“史”指史官左史戎夫。
2. 《春秋公羊傳注疏》僖公二年“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亡而齒寒”。何休解詁“《記》,史記也” [5]。可見此“史記”本名《記》,據上《竹書紀年》例,自當理解為“史”所記,稱“史《記》”。
3 .《墨子·非命下》“昔者紂執有命而行”,周武王“非之”,曰“子胡不尚(上)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卜簡》之篇以尚(上)皆無之也” [6]。此《記》自類似上引《竹書紀年》所說寫下歷代“遂事之要戒”之“史《記》”,方能據以對紂之統治“有命”說“非之” 。
4. 《呂氏春秋·務本》“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高誘注“上古《記》,上世古書也” [7]。從文意看,此古書當是“史《記》”。
5. 《韓非子·說疑》凡三見《記》:“其在《記》曰堯有丹朱”云云、《記》曰“周宣王以來”云云、“故《周記》曰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云云[8]。此三《記》自是“史《記》”。
6. 《史記·蒙恬列傳》“昔周成王初立”,年幼,“有病甚殆”,周公旦“自揃其爪以沉于河”,向神表示愿代成王“受其不祥” ,并將此事“(命史官)書而藏之《記》府”。后成王長大,“觀于《記》府”,知周公忠心[9]。此證周初乃記事于《記》即“史《記》”中,并由專門之“府”收藏。文中“書而藏之《記》府”,自毋須周公親自動手,而是史官之事。《史記·封禪書》秦繆公稱夢見上帝命自己“平晉亂”,于是“史(官)書而記藏之府”(疑當依《蒙恬列傳》作“史書而藏之《記》府”)[10],是其側證。
7. 《史記·六國年表》序講到《秦記》共三處,即“太史公讀《秦記》”、“獨有《秦記》”、“因《秦記》”。索隱“即秦國之史記也” [11]。這表明秦國史書本稱《記》,為區別他國之《記》則稱“秦《記》”(上引“周《記》”同),《記》前無“史”字。我這樣說,還有以下強證:首先是《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12]。這是上奏文書中的用語,可見無“史”字之“秦《記》”,必為本名或正式名稱。其次,由于與諸侯史書被秦始皇焚毀者不同,秦國史書曾保存到漢晉以后很長一個時期,而見到它的人也一律稱之為“秦《記》”,并無“史”字。甲、《史記·秦始皇本紀》末附漢明帝詔問班固,固答文中有曰:“吾讀秦《紀(記)》,至于子嬰車裂趙高”云云[13]。乙、晉摯虞《決疑錄要》注曰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之義”,“侍中彭權對曰秦《記》云……” [14]。丙、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僰道縣》“故秦《紀(記)》言僰童之富”云云[15]。由此三例再一次證明流傳到漢晉時的秦史書本名或正式名稱是“秦《記》”,《記》前無“史”字[16]。
以上七點可證錢大昕說不準確,“古者列國之史”本名《記》[17],而不是“《史記》”。
二
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先秦兩漢史料中大量見到的列國之史被稱引時,卻不是《記》,而往往是“《史記》”,錢大昕說的根據,王利器先生所舉之證,都源于此(往下為了敘述方便,除今版書名外,凡引文稱古列國“《史記》”者,一律依拙說作“史《記》”)。
如泛稱“諸侯史《記》”:《史記·六國年表》序“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 [18]。
如“周史《記》”:《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第一,《疏》引《閔因敘》“昔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 [19]。
如“魯史《記》”:《漢書·司馬遷傳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 [20]。
其所以如此,我以為原因有二:
第一,這些《記》乃“史(官)”所記。《史記·秦本紀》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記事”[21]、前引《竹書紀年》左史“作《記》”、秦繆公事“史(官)書而記藏之府(或'藏之《記》府')”,均《記》乃“史”所記之證。因而《史記·周本紀》幽王三年“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下《正義》“諸國皆有史以記事,故曰史《記》” [22]。本名《記》,因史所記,有時亦可稱“史《記》”,這是很自然的。前引《竹書紀年》稱左史“作《記》”,《逸周書》篇名作《史< 記> 解》,或即此故[23]。
第二,但是在古代其所以往往將國家史書《記》稱“史《記》”,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把國家史書與其他著作、文書區別開來,因為當時《記》之名稱不限史書,使用是很泛的。
一般著作稱《記》。如《老子》稱《記》。《莊子·天地》“《記》曰通于一而萬事畢”。王先謙《集解》“《記》曰”下引《經典釋文》“書名,老子所作” [24]。
《莊子》稱《記》。《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記》之文字為“既雕且琢,還歸其樸”,乃出之《莊子·山木》[25]。
《孟子》稱《記》。《韓非子·忠孝》“《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蹙)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文見《孟子·萬章上》。故陳奇猷曰“則所謂《記》者,《孟子》書也” [26]。
陰陽家言稱《記》。《呂氏春秋·至忠》“臣之兄嘗讀故(古)《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高誘注“比三月必死,故曰不出也”。楚王令人查找,“于故《記》得之”。同書《貴當》“《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高注“《志》,古《記》也”。陳奇猷校釋以為以上兩處“皆陰陽家言” [27]。
按稱《記》之一般著作,兩漢猶有存者。《大戴禮記·保傅》“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云云[28],證明戴德所見著作僅稱《記》,為免與他《記》相混,故標明乃“青史氏”之《記》[29],而到《漢書·藝文志》中則又被改稱《青史子》,歸入小說家[30](或許《藝文志》其他以作者名定先秦著作名者,也是這樣由各種古《記》演變的,這應是我國書史上的一個進步)。
一般文書、官文書稱《記》。如《戰國策·齊四》“后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田文)收責(債)于薛者乎?'馮諼署(此《記》)曰能” [31]。此貴族家文書稱《記》。又《越絕書》卷十吳國左校司馬王孫駱“移《記》”于東掖門亭長公孫圣,“公孫圣得《記》,發而讀之” [32]。此官府文書稱《記》。
儒家《禮》書中補其《經》之不備者等,文亦稱《記》。如《儀禮·士冠禮》“《記》:冠義”,賈疏“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 [33]。胡培翚引熊伯耒等三家說,指出《儀禮》十七篇中“有《記》者十有三篇,……必出于孔子之后,子夏之前”[34]。再如《禮記·曾子問》“孔子曰:'……《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此之謂乎'”。孔疏“舊《記》先有此文,故孔子引之”。又《禮記·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疏稱漢代作《禮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故此處“引之” [35]。《禮記·學記》“《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疏“謂舊人之《記》先有此議”,此乃“引舊《記》之言”。又,“《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疏“引舊《記》”。又“《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疏“引舊《記》” [36]。
由上可見,在先秦,《記》之名稱滿天飛,故稱引《記》者,一般很難判別其為何書,是否史書,為將作為國家史書之《記》與其他著作稱《記》者區別開來,凡有三法:
一是《記》上冠以國名,如周《記》、秦《記》等,證明是國家之《記》(史書)。
二是另立特殊名稱,如晉史書又名《乘》,楚史書又名《梼杌》,魯史書又名《春秋》[37]。墨子便引用過“周”、“燕”、“宋”、“齊”四《春秋》[38];甚至說過“吾見百國《春秋》” [39]。但《春秋》一名作為國家史書之義并不明確,私人著作論述歷史者,也有名《春秋》的,如《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等[40]。
三即稱引者在《記》上加一“史”字,證明乃史官所作之《記》,必為國家史書,而不是私人著作等。開始只是為了與后者區別,“史《記》”二字尚非專名,猶是史官所作之《記》的意思,但行之既久,約定俗成,便與《春秋》等一樣,成為專名了[41]。由于作為國家史書之意它比《春秋》之名來得明確,所以適用最為廣泛。強證便是司馬遷在《史記》一書中,凡提及古代國家史書,除原名本為《春秋》者(即孔子《春秋》)[42],因襲稱之不變外,其他皆稱“史《記》”。如前引《周本紀》“太史伯陽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論史《記》舊聞”、《六國年表》序“諸侯史《記》尤甚”等等[43]。這一“史《記》”與單稱秦《記》、周《記》的區別是,后者兼分清史書之國別,而前者則多用于泛指(如上引“諸侯史《記》”等),然而與一般私人著作、文書等有明顯區別,二者則同。
關于前人所稱古之《史記》,實乃“史《記》”,通過司馬遷書之得名《史記》,也可證明。
三
按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楊明照先生在《太史公書稱史記考》一文中,便曾詳盡地考證了此《史記》之名“起自后漢靈、獻之世”,并舉有《武榮碑》等五證;在此之前凡有名稱者五,即《太史公書》、《太史公》、《太史公記》、《太史公傳》、《太史記》[44]。請參看。但他沒有涉及以下這樣兩個問題,即長達三百年時間里為什麼司馬遷此書卻沒有“《史記》”之名?而到了東漢末年為什麼它又得到了“《史記》”之名?先看第一個問題。
我以為司馬遷此書其所以長期無“《史記》”之名,原因就在于自先秦以來直到東漢末,稱“《史記》”(往下依前例但稱“史《記》”)便是指國家史書,而司馬遷此書乃私人著作:
1. 《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談告誡司馬遷,要他成為大孝,務必留下史學著作,“揚名于世” [45]。《漢書·司馬遷傳》受宮刑之后在報任安書中說,其所以茍活是因為“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為的就是要完成這一史學著作, “成一家之言” [46]。兩處皆指揚個人之名的私人著作,甚明。若古“史《記》”,如《禮記·玉藻》所說,天子(國君)“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47],亦即由史官如實記下每天之統治事務,其《記》如后代的《起居注》,哪里談得上個人揚名后世?即使如《周禮·宰夫》下之“史”,“掌官書以贊治”,鄭注“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 [48],也只是根據統治者意思起草文書和進行匯編,何能“成一家之言”?
2. 更重要的是,《史記·太史公自序》自稱要將這部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 [49]。如是國家史書,豈能由司馬遷如此支配!
3. 正因司馬遷此書乃私人著作,才僅得到《太史公書》等五個名稱(見上),而不是“史《記》”。其中最典型的是《太史公》。如《法言·君子》“《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 [50]。《漢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 [51]。可見從西漢到東漢司馬遷此書皆可以名《太史公》。為什麼?就因為司馬遷曾自稱“太史公”。如《史記·太史公自序》之篇名及其中三稱“太史公曰”均其證[52]。而依先秦漢代之風氣,個人著作往往可以作者之姓名(或尊稱)稱之,如《孟子》、《伊尹》、《太公(呂望)》、《莊子》、《毛公》等[53 ]。以此例之,稱《太史公》自意味其為私人著作無疑。又《太史公書》一名最初乃出自司馬遷自稱[54],而如前所述,他屢屢稱引古“史《記》”,而對自己著作卻另定此名(意指司馬遷所著之書[55]),其非指國家史書甚明。至于《太史公傳》,其“傳”,意同于“書”。《史記·趙奢傳》子趙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56],是“書”、“傳”同義之例。“傳”古可指個人著作[57]。則《太史公傳》之非國家史書性質同樣很清楚(《太史公記》、《太史記》反映問題同,見下)。
固然,司馬遷職太史令,但他主要是“主天官”、“掌天官(觀察天象)” [58],同時還保管、整理國家文書[59],而非記事之史。固然,魏如淳曾說漢太史公“序(敘)事如古《春秋》”;唐劉知幾也以為太史本“記言之司” [60]。可是首先漢武帝封禪泰山不讓司馬遷父太史公司馬談隨從,如是序事、記言之司,如此大事,豈能不去?其次司馬遷全書包括《自序》無一語及太史公序事記言之任。可見西漢太史令已無此職任。這就是為什麼甲、司馬談臨死叮囑司馬遷“汝為太史(掌握著大量國家文書),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指留下私人著作,揚名于后世)”。如“論著”是太史本身職任,何來忘不忘的問題?乙、司馬遷自稱要繼孔子《春秋》之后留下著作,上大夫壺遂與之討論創作意圖,如是太史公職任,豈有討論之必要[61]!何況司馬遷所要“繼”的孔子《春秋》正是私人著作[62]。
由于在漢人觀念中,很長一個時期內(大體上直至東漢末年),如前所述,根據古代傳統,稱“史《記》”,便指國家史書,則司馬遷個人著作沒有“史《記》”之名,是必然的。
再看第二個問題,為什麼到東漢末年它又得到了“史《記》”之名了呢?
我以為這和到漢代稱引國家史書名之為“史《記》”已不多見,二者關連已逐漸淡化緊密聯系。據《漢書·藝文志》,西漢記事之國家史書已漸改稱《漢著記》,凡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63]。《漢書·五行志》“凡《漢著紀(記)》,十二世(由高祖至平帝),二百一十二年” [64]。《漢書·谷永傳》成帝時上書言災異,稱“八世《著記》(由高祖至元帝)” [65]。《后漢書·皇后紀》和熹鄧皇后時平原侯劉毅上書稱“漢之舊典,世有《注記》” [66]。《后漢書·文苑李尤傳》安帝時“受詔”與劉珍等“俱撰《漢 < 記 > 》”[67](后漢應劭《風俗通義》卷八《祀典·灶神》已稱引此“《漢 < 記 > 》” [68])。又《風俗通義》“按《明帝起居注》”云云[69]。后漢荀悅《申鑒·時事第二》“先帝故事有《起居注》” [70]。《隋書·經籍志二》著錄《漢獻帝起居注》五卷;并附稱“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云云[71]。總之,稱引國家史書,名之為“史《記》”的歷史和影響漸漸成為過去,它被新的各種名稱代替了。這便為司馬遷個人著作得以獲“史《記》”之名準備了前提。
其演變情況當是這樣的:
前述司馬遷其書還有《太史公記》和《太史記》之名。《太史公記》最早見于《漢書·楊惲傳》“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 [72]。按《太史公書》之名乃司馬遷自定,楊惲作為晚輩為何要擅改?我以為很可能是因為當時尚有古來國家史書稱《記》之傳統(前有“秦《記》”,漢有《著(注)記》,均見上),楊惲為突出司馬遷此書乃相當于古來國家史書的史學著作性質,故改“書(無論視為'書'或'《書》')”為“《記》”(作“書”則此義不顯)。但因畢竟乃個人著作,且為突出司馬遷,故《記》上保留“太史公”三字以別之。這是先秦兩漢書中“史《記》”之“記”本應理解為“《記》”的又一證明。也正因如此,到東漢中后期當“史《記》”之稱進一步淡化[73],而《太史公 < 記 > 》則因為在突出司馬遷此書相當于國家史書性質上其涵義優于《太史公書》、《太史公傳》及《太史公》,因而進一步流行,而后三者則漸被冷落[74]。以下一事最能反映稱《太史公 < 記 > 》的意圖所在。如東漢明帝曾批評司馬遷此書“微文刺譏,貶損當世(指西漢武帝)” [75];班固不予理睬,仍然在《漢書·司馬遷傳贊》中高度評價其書“其文直,其事核(實),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76]。盡管它違反皇帝意志,可發展到漢末,荀悅在所寫《漢紀》評價司馬遷此書時依然稱引《漢書》,照抄這十七個字,這是這一評價早已深入人心,司馬遷此書在人們心目中相當于國家史書之反映[77]。然而荀悅同時卻將《太史公書》改為《太史公 < 記 > 》(按《太史公自序》原文作“遭李陵之禍,……乃喟然嘆曰”云云,然后發憤寫作,“自黃帝始”,“為《太史公書》”。《漢書》照抄《自序》這一段話,后面也作“自黃帝始”,“為《太史公書》”。而《漢紀》在照抄“遭李陵之禍,喟然而嘆”著書之后,卻改作“始自黃帝,……為《太史公 < 記 > 》” [78]。三者對比,以“《記》”代“書”之跡顯得十分突出)。很清楚,這是借此再一次在強調司馬遷此書相當于國家史書的“實錄”性質,因而其《太史公 < 記 > 》之“記”,必當為“《記》”,而不是一般理解的記事義之“記”,因為如是后者,改“書”為“記”便無甚意義,荀悅何必要巴巴地通過前述文字排比、對比,突出這一意圖!
正是在這一背景和學術風氣下,如漢末另一著名學者應劭在所著《風俗通義》中,不但稱引《太史公 < 記 > 》,而且時而又將它簡化為《太史 < 記 > 》[79]。原因當在于稱此二名,重點均在《記》,均在肯定司馬遷所著乃相當于國家史書(“實錄”)的《記》,至于作者稱“太史公”或“太史”是都可以的,大家都知道是指司馬遷。由于此故,當古來作為國家史書的“史《記》”之名及影響進一步淡化、消失,《太史公 < 記 > 》、《太史 < 記 > 》便在不知不覺中又簡化為“史《記》”了[80]。這“史《記》”與古來列國“史《記》”的共同點是,其《記》,全不是義指記事之“記”,而是指史學著作之《記》;區別是后者之“史”是國家記事史官之“史”,而前者之“史”則非國家記事史官之“史”,而是“世主天官”的“太史公”之“史”,因而后者之《記》雖自來是指國家史書,而前者之《記》則化為指司馬遷的個人著作了。
綜上所述,結論是:從史學史角度言,錢大昕所說“古者列國之史,俱稱《史記》”,其《史記》當理解為“史《記》”,指國家史書。其“《記》”是專名,其“史”是官名。而司馬遷之《史記》,大約在漢末開始一般還同樣被理解為“史《記》”,是指個人著作。其“《記》”也是專名(盡管古列國“史《記》”之《記》與之有公私之別),其“史”乃指司馬遷。至于約自漢末起,對“史《記》”的理解逐漸發生變化,主要是將此“史”理解為文史之“史”,歷史之“史”,而非史官之“史” [81 ],又將“《記》”僅理解為記事義之“記”,司馬遷“史《記》”自然也就成了今天一般所理解的“《史記》”;后代又將它們發展成為一些新的專名[82],則屬發展變化問題。從史學史的角度,這是不能不分別清楚的。
[1]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七,商務印書館, 1958 年,上冊,第 142 頁。按此《史記》之書名號原無,據上下文補。
[2] 王利器《 < 太史公書 > 與 < 史記 > 》,收入《曉傳書齋集》,華東師大出版社, 1997 年,第 307-311 頁。
[3] 準確地說,作為專名,應標點為“《史 < 記 > 》”,可是為免層層書名號帶給各方面的麻煩,往下論及但一律簡稱“史《記》”。
[4]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收入方詩銘等《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第 247 頁。又《史 < 記 > 解》原文及注請參黃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下冊,第 1006-1009 頁。
[5] 中華書局《十三經注疏》本, 1980 年,下冊,第 2248 頁,上欄。
[6] 吳毓江《墨子校注》卷九,中華書局, 1993 年,上冊,第 425 、 432 頁。校注引孫詒讓云“皆無之,謂皆以命為無也”。
[7] 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學林出版社, 1984 年,第二冊,第 713 、 715 頁。
[8]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下冊,第 924-932 頁。
[9] 《史記》卷八八,中華書局, 1962 年,第八冊,第 2569 頁。
[10] 《史記》卷二八,第四冊,第 1360 頁。
[11] 《史記》卷十五,第二冊,第 685-686 頁。索隱“史記”二字,此標點本未加書名號,當是為了區別于司馬遷《史記》,我以為當理解為“史《記》”;又“秦記”,標點本俱加書名號為《秦記》,我以為當理解為“秦《記》”(《韓非子集釋》之“周記”,原書加書名號為《周記》,當理解為“周《記》”)。理由均見下。
[12] 《史記》卷六,第一冊,第 255 頁。
[13] 《史記》卷六,第一冊,第 293 頁。此班固語,參第 290-291 頁“孝明皇帝十七年……”句下《正義》、《索隱》,又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五,中華書局, 1981 年,第一冊,第 193 頁。又文中“秦《紀》”當為“秦《記》”。按紀、記本有別(見《王力古漢語字典》,中華書局, 2000 年,第 910 頁),但因在“記載”這個意義上二字相通,因而古書校勘上亦有相混者,只能據上下文意確定,此即一例,下同。
[14]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中華書局, 1963 年,第三冊,第 3034 頁。
[15] 《華陽國志》卷三,國學基本叢書本, 1958 年,第 39 頁。
[16] 《史記·秦始皇本紀》末附從秦襄公至秦二世之要事,索隱以為它們“皆當據《秦紀(記)》為說”,也是稱《秦紀(記)》 。金德建先生有《 < 秦記 > 考征》一文,收入其《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第 415-423 頁,請參看。
[17] 又《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注引“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注“《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以上分別見《周禮正義》,中華書局,1987 年,第八冊,第 2098 頁及 2137 頁。此二處雖非直接稱《記》,而是稱《志》,但通過二鄭權威之注,仍間接知古史書稱《記》。
[18] 《史記》卷十五,第二冊,第 686 頁。
[19] 《十三經注疏》,下冊,第 2195 頁上欄。
[20]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六冊,商務印書館, 1959 年,第 4272 頁。
[21] 《史記》卷五,第一冊,第 179 頁。所記之事當即“秦《記》”。
[22] 《史記》卷四,第一冊,第 147-148 頁。
[23] 《逸周書》乃西周初文字,參拙稿《史佚非作冊逸、尹逸考》,《文史》,中華書局,2009 年,第一輯。可見稱《記》為史《記》,時代是很早的。
[24] 王先謙《莊子集解》卷三,中華書局, 1954 年,第 64 頁。
[25]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下冊,第 614 、 650 頁,及引王先慎、太田方說。《山木》此文見王先謙《莊子集解》卷五,第 15 頁。
[26]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下冊,第 1108 、 1112 頁。
[27] 以上兩篇分別見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第二冊,第 578 、 584 頁,及第四冊,第 1629 、 1633 頁。
[28] 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上冊,第 371 頁,中華書局, 2008 年。
[29] 這種辦法,先秦已有。如《左傳》成公四年有“史佚之《志》”、襄公三十年有“仲虺之《志》”。“《志》謂《記》也”,鄭司農語,見《周禮正義》第 2089 頁引。因當時僅稱《志》或《記》的著作多,故標明作者以別之。
[30]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五冊,第 3168 頁。
[31] 《戰國策》卷十一,國學基本叢書本, 1958 年,第 91 頁。
[32] 《越絕書》卷十,四部備要本,第 27 頁。
[33] 《儀禮注疏》卷三,《十三經注疏》上冊,第 958 頁,中欄。
[34] 胡培翚《儀禮正義》二,四部備要本,上冊,第 34 頁。又《孟子·滕文公上》“且《志》曰喪祭從先祖”。趙岐注“《志》,《記》也”,并引《周禮·小史》為證。焦循以為小史所掌之《志》即《記》,“容有喪禮從先祖云云”,實“不知”出自哪部禮書。見《孟子正義》卷五,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第一冊,民國 23 年,第 193 頁。可為諸《禮》書中之《記》被單獨摘出引用之證。
[35] 以上分別見《禮記正義》卷十九、卷二十,《十三經注疏》,下冊,第 1401-1402 頁,又第 1407 頁。
[36] 以上三條均見《禮記正義》卷三六,《十三經注疏》,下冊,第 1521-1524 頁。
[37] 《孟子·離婁下》,《孟子正義》卷八,第 338 頁。
[38] 《墨子·明鬼下》,《墨子校注》卷八,上冊,第 337-339 頁。
[39] 此語《墨子》及先秦兩漢書均不載,最早見于《隋書·李德林傳》轉引,中華書局, 1973 年,第四冊,第 1197 頁。按稱列國之史為《春秋》,除魯《春秋》,其他少見,疑乃墨子個人習慣用語。《公羊傳》莊公七年何休解詁“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十三經注疏》 ,下冊,第 2228 頁)。此證一般應稱“史《記》”,司馬遷稱列國之史一般均為“史《記》”可證,見下。
[40] 《虞氏春秋》見《史記》卷七六《虞卿傳》,第七冊,第 2375 頁,又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序》,第二冊,第 510 頁(包括《呂氏春秋》)。
[41] 何休曰“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十三經注疏》,下冊,第 2228 頁),即一證(準確地說,“史《記》 ”應標點為《史 < 記 > 》,見本文第一頁注 3 )
[42] 司馬遷和當時人雖高度評價孔子《春秋》,但只把它視為私人著作。如《太史公自序》“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其非國家史書無疑。又《孔子世家》“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反映問題同,分別見《史記》第十冊,第 3299 頁,及第六冊第 1944 頁。關于西漢人視《春秋》為孔子私人著作,請參錢穆《孔子與春秋》,收入《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商務印書館, 2001 年,第 263-270 頁。
[43] 王利器先生舉有十四例,此外還舉有其他先秦兩漢著作稱引史《記》者,請參看,見王利器《 < 太史公書 > 與 < 史記 > 》五,《曉傳書齋集》第 307-310 頁。其中所引《史記·孔子世家》“乃因史《記》,作《春秋》”(原文見《史記》第六冊,第 1943 頁),更把“史《記》”與孔子所作《春秋》一公一私的性質分別得很清楚。
[44] 此文收入楊明照《學不已齋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第 29-50 頁。五個書名號均沿原書之舊。
[45] 《史記》第十冊,第 3295 頁。
[46]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六冊,第 4270 頁。
[47] 《禮記正義》卷二九,《十三經注疏》,下冊,第 1473-1474 頁。
[48] 《周禮正義》第一冊,第 193 頁。
[49] 《史記》第十冊,第 3320 頁。
[50] 汪榮寶《法言義疏》卷十八,中華書局, 1987 年,下冊,第 507 頁。
[51]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五冊,第 3114 頁。
[52] 《史記》第十冊,第 3285 、 3296 、 3299 、 3321 頁。《史記》其他自稱“太史公”處尚多,不贅引。
[53] 見《漢書·藝文志》,王先謙《漢書補注》第五冊,第 3132 、 3140 、 3140 、 3143 、3156 頁。此《志》中此例不勝枚舉。
[54] 《史記·太史公自序》,第十冊,第 3319 頁。
[55] 很可能還有包括其父司馬談為著書者之意。因司馬遷本稱其父為“太史公”,并說此《書》“悉論先人所次舊聞”,見《史記》第十冊,第 3295 頁。本文不深論。
[56] 《史記》第八冊,第 2446 頁。
[57] 晉張華曰“圣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見《博物志校證》卷六,中華書局, 1980 年,第 72 頁。清趙翼也說“古人著書,凡發明義理,記載故事,皆謂之傳”,“是漢時所謂傳,凡古書及說經皆名之”,見《陔余叢考》卷五《史記一》,商務印書館, 1957 年,第 85 頁。
[58] 《太史公自序》,《史記》第十冊,第 3319 、 3293 頁。《天官書》“太史公推古天變”云云,是掌觀察天象之證,《史記》第四冊,第 1344 頁。
[59] 《太史公自序》“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史記》第十冊,第 3319 頁。又 3287 頁注引如淳曰“《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又第 3296 頁“遷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謂綴集之也”,綴集即保管、整理。又《漢書·司馬遷傳》補注以為“”即“籀”,讀書,“言讀而尋繹之也”,亦可通。王先謙《漢書補注》第六冊,第 4247 頁。
[60] 分別見《史記》第十冊,第 3287 頁注,及浦起龍《史通通釋》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下冊,第 307 頁。
[61] 《史記》第十冊,第 3296-3300 頁。
[62] 參注 42 、 43.
[63]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五冊,第 3114 頁(請參補注引何焯等語);又第 3417 頁《劉向傳》上奏稱“孝昭帝時”有“特異”現象,“皆著于《漢紀(記)》”,《著記》之“著”,當即此義。此“《漢紀(記)》”正規名稱,應是《漢著記》。
[64]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四冊,第 2541 頁。同書第三冊,第 1809-1815 頁《律歷志(下)》引《三統歷譜》上有《著紀(記)》漢朝各帝在位年數。如“《著紀(記)》高帝即位十二年”、“惠帝《著紀》即位七年”等,可與上一史料互證(按此《著紀(記)》下至東漢光武帝,與劉歆《三統歷》時代不合,清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以為“原編至成帝止,其下皆后人所續”。收入《二十五史補編》第二冊,第 1566 頁,中華書局, 1986 年。
[65]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七冊,第 5008-5009 頁。
[66] 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帝紀》卷十上,萬有文庫本,民國二十九年,第三冊,第 402 頁(請參王先謙集解引惠棟等語)。同前書第五冊,第 908 頁《馬嚴傳》,有詔與杜撫等“雜定建武《注記》”,是其證。按“注”與“著”用在《記》前,或說二者義同,或說否,請參王先謙《漢書補注》第五冊第 3114 頁補注引何焯等語,本文不論,但國家史書名《記》則同。
[67] 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列傳》卷七十上,第十四冊,第 2870 頁。又第十一冊第 2165 頁《蔡邕傳》“撰補《后漢記》”(注引《邕別傳》則作《漢記》);又第十二冊,第 2306 頁《盧植傳》 “補續《漢記》”;又第十四冊第 2904 頁《侯瑾傳》“按《漢記》,撰《皇德傳》”,均其證。此《漢記》即后代所稱的《東觀漢記》。
[68]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第 302 頁。
[69] 《初學記》卷三十《烏第五》引,第三冊,第 732 頁,中華書局, 1962 年。此文今本《風俗通義》佚。《隋書·經籍志二》也說“后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見《隋書》卷三三,第四冊,第 966 頁,中華書局, 1973 年。
[70] 《申鑒》,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第七冊,第 15 頁。晉袁宏《后漢紀序》稱參閱過“《漢靈、獻起居注》”,收入《兩漢紀》下冊,中華書局, 2002 年。
[71] 《隋書》卷三三,第四冊,第 966 頁。
[72]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七冊,第 4427 頁。
[73] 參注 66 、 67 “劉毅上書”等,證明東漢國家史書之名流行《注記》、《著記》、《漢記》,古來“史《記》”之名始終未見再被稱引。
[74] 參楊明照《學不已齋雜著》第 47-50 頁(漢末書已不見引此三名)。
[75] 班固《典引》文引,《文選》卷四八,中華書局, 1977 年,下冊,第 682 頁。
[76]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六冊,第 4273 頁。
[77] 十七字中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王先謙曰“自唐后每帝修實錄,義取于此”,可見二字份量之重,王先謙《漢書補注》第六冊,第 4273 頁。又《三國志·王朗附王肅傳》。不同意魏明帝否定《史記》之說,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錄”(《三國志》第二冊,第 418 頁,中華書局, 1962 年),可見影響之深遠。
[78] 以上均見袁宏《兩漢紀》上冊《漢紀》第 249 、 247 頁。《太史公自序》原文見《史記》第十冊第 3300 頁、 3319 頁。《漢書》照抄《自序》語,見王先謙《漢書補注》第六冊,第4252-4253 、 4257 頁。
[79]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稱《太史公 < 記 > 》見卷一第 15 、 32 頁;稱《太史 < 記 > 》見卷二第 69 、 89 頁。
[80] 參楊明照《學不已齋雜著》,第 34-38 頁。
[81] 在這之前,先秦兩漢史料中之“史”,僅指史官。關于“史”義這一變化,將另文詳考。此處僅舉一例:東漢末(公元 192 年)王允將治蔡邕罪。因邕前曾撰補《后漢記》,未成,故此時刺史馬日磾救邕,向允提出的理由是邕乃“曠世逸才”“當續成漢史”。此“史”自是歷史之“史”,而非史官之“史”,見《資治通鑒》卷六十,靈帝初平三年,古籍出版社, 1957 年。
[82] 如《五代史記》、《宋史記》、《蒙兀兒史記》等,其作者無疑便是這樣理解先秦兩漢《史< 記 > 》,仿效定專著之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