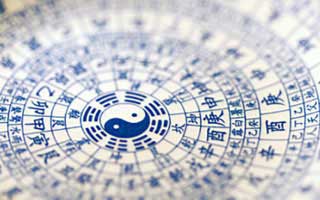北山衫
《海伯利安》, [美] 丹·西蒙斯著,潘振華、官善明、李懿譯,讀客文化·吉林出版集團2014年11月出版,560頁,59.00元
2020年11月,美國深陷疫情旋渦時,我與兩位友人到優勝美地作短途旅行。為了打發五點便天黑的漫長雪夜,我們在小旅館圍爐夜話,每個人輪流講一個故事。第一個人十分偶然地講了《十日談》中的故事。第二個人接著講了《海伯利安》。為了保持隊列,我應該講《坎特伯雷故事》。
考慮到三本書的傳承性,我們幾乎巧合地實踐了一項古老的文學傳統。薄伽丘的《十日談》是佛羅倫薩瘟疫時十位青年男女到鄉村別墅避難,歡娛游戲、互講故事的集合。《坎特伯雷故事》則是一群三教九流的朝圣者在從倫敦至坎特伯雷的行程中,為了打發旅途寂寞互講故事解乏,兼作比賽。喬叟約莫與薄伽丘同時代,游歷意大利時接觸過薄伽丘的作品(是否與薄會面則屬懸案),受其人文主義影響匪淺。《坎特伯雷故事》若干小節字句依稀與《十日談》相應。而《海伯利安》對《坎特伯雷故事》則是十分顯然地主動地套用了其形式。它講述了星球大戰前夕,人類命運存亡之際,七個看似毫無關聯的人前往遙遠的海伯利安星球朝圣。旅途中每人各講一個故事,解釋自己為什麼會被選中,由此展開一幅跨越星際的浩瀚畫卷。
由篇幅很短的個人軼聞(anecdote)來講格局很大的“太空歌劇”無疑具有風險。不亞于試圖以點狀星球來覆蓋整個星系。但雄心勃勃的丹·西蒙斯經過早期文學生涯的積累,同時對諸多類型文學都有了相當的實驗,是時候挑戰一部鴻篇巨制來一番“劍之試煉”了。
選擇《坎特伯雷故事》的既有形式是十分高明的,它看似加大了創作的難度,如同《坎》中為了英詩格律而不得不對重讀和音節有所取舍,《海伯利安》的人物設定和劇情推動被框架施加了額外的限制。反過來講,它其實發揮了西蒙斯擅寫短篇小說的長處,將老本行拔高一步,在其基礎上架梁疊櫞,從而實現質的飛躍。
我們且看以短篇講史詩是如何做到的。在各類幻想作品中,不論是文學還是影視,不乏以旁白介紹背景開場,以便在數分鐘之內將受眾吸納入一個架空的世界之內。更不乏這樣的例子,最初的一兩章(集)世界觀設定讓人眼前一亮,但亮點也就止步于此了,剩下的篇幅都不過是設定之上平庸的附著物。如果遵循這樣的快速啟動套路,海伯利安應該這樣開場:
“舊歷公元29世紀,人類擯棄了古老地球而發展出了真正意義上的星際文明。已知的八千星球中,約四百個實現了人類移民。部分星球之間能以遠距離傳送門瞬移,以超光儀進行通訊。它們構成了一個整體的世界網,由‘霸主’這一組織所控制。另一部分缺乏傳送門的星球則被稱為偏地星球。它們仍能以常規的太空飛船到達,但冷凍休眠的旅程將會產生可觀的時間債。本體人類世界的邊緣,另有稱為驅逐者的變異人。它們自大流亡后便與人類分道揚鑣,通過不斷基因改造,適應了微重力的太空環境。人并不是宇宙的絕對主宰。大流亡之前便存在的人工智能進化出了完整的自我意識,最終脫離人類社會而形成了獨立的主權:技術內核,簡稱內核。內核向霸主提供包括傳送門和超光儀在內的多種技術支持,并向霸主的參謀長聯席會議派駐顧問,參與各項戰略決策。人類對內核的依賴誠然已達岌岌可危的地步……”
單看以上,很基礎的星際設定。接下來懸疑的部分出現,旁白繼續講道:
“身處偏遠世界的海伯利安就是偏地星球中的一個。在海伯利安遠離人類定居點的荒野山谷之中,豎立著六座謎一樣的遺跡——光陰冢。它們巨大,靜默,如座座迷宮,卻空空如也。沒有人知道它們是誰所建、為何而建。只知道它周圍流淌著駭人聽聞的逆熵場,據說能使時光倒流;還有怪力亂神的神秘生物——伯勞流連。正如同名的鳥喜歡將活著的獵物扎在尖刺之上一樣,伯勞也喜歡將人扎在尖刺的痛苦之樹上慢慢折磨,故而得名。在崇拜伯勞的伯勞教徒心中,它是人類罪惡的末日審判者,被尊奉為痛苦之神。他們成群結隊前往光陰冢朝圣,然而有去無回。近來逆熵場突然爆發式擴散,加上驅逐者同時入侵,使海伯利安變成了刀山火海。霸主破格批準了最后一次前往光陰冢的朝圣。七名朝圣者到底為什麼要冒著幾乎必死的危險前往?又是什麼前緣使得他們脫穎而出被伯勞教選定?從星際飛船至遺跡的漫長旅程中,他們決定每個人都講出自己與伯勞的關聯,讓彼此了解故事的全景。現在,故事開始了。抽簽的順序決定,第一個講述的是蒼白虛弱的神父……”
這樣的簡介無疑也很抓人,為故事的切入提供了足夠的潤滑。但是,本書的讀者打開第一頁時,對上述背景其實一無所知。相反,丹西蒙斯把他龐大宇宙的設定壓下不表,先不厭其煩地描繪了朝圣者之一,一位霸主領事,在海伯利安一艘太空飛船瞭望臺上彈奏古董鋼琴時舷窗外的風景:
“艙下沼澤中,一只只綠色的巨型蜥蜴狀生物蠕動,嗥叫著。北方正醞釀著一場雷暴,青黑色的烏云下,一大片龐大裸子植物構成的森林輪廓沉郁。層積云就像九千米高塔,插入狂暴的天空。地平線上繚繞著一條條閃電。靠近飛船的地方,一些時隱時現爬蟲的身影會磕磕碰碰地誤撞入阻斷場,尖叫一聲,墜入靛青的迷霧。領事聚精會神地彈著序曲中最難的一段,毫不顧及風暴和夜幕的臨近。” (讀客文化2014版,潘振華、官善明、李懿譯,微有刪改)
全本小說起始于一個場景設定。人物所處的瞭望臺很小,但窗外的世界很大。它提供的信息包括:這顯然是一個外星球,因為裸子植物森林曾覆蓋恐龍時代,但不存在于現在的地球。巨型蜥蜴可能是外星生物。九千米高的層積云暗示與地球不同的重力等參數。人物在太空飛船上彈鋼琴品酒,高科技,很從容。
從舷窗的一瞥已使我們得到一個星球的初步印象,它陰沉,晦暗,充滿不祥的預感。人腦是一架很奇妙的儀器,非常善于填充空白。存儲記憶時對信息極度壓縮,只記梗概,提取時再往缺失處填充合理細節,得到完整的畫面。西蒙斯要做的也正是以點帶面,在關鍵點上使人信服,讀者動用想象力自會將稀疏的部分鋪滿關聯。
重點現在落到了如何選點。既要到達《十日談》與《坎特伯雷故事》那樣風俗畫卷的效果,同時要避免成為聯系不緊密的故事合集,《海伯利安》選擇讓七個人講六個故事是很平衡的折中。神父,上校,詩人,學者,偵探,領事,職業不同,經歷極度差異化,盡可能覆蓋到海伯利安宇宙更多側面。
有人說,所有的現代小說都是偵探小說。這指的是它們的信息披露方式。主人公到甲地,遇見一些人,她與讀者同時得到一些信息;接著到乙地,丙地,行程繼續。在《海伯利安》中,這條行程就是七個人朝圣。得到彼此有交集的經歷,用來破解指向光陰冢與伯勞的謎題。
為了讓故事各具風格,西蒙斯展現了他技藝純熟的一面:他要融合各種類型,無論驚悚、浪漫、偵探,還是黑色小說,都得心應手;包括科幻小說的亞型,賽博朋克、軍事科幻,俱手到擒來。第二個上校的故事,外太空戰斗一節,隨時隨地可能制服破損面臨缺氧,還有脫離飛船滑向太空的危險,如真空一般將讀者緊緊包裹。此種高強張力不難在后來《地心引力》等作品找到回響。第四個學者的故事里,時間倒退而記憶重置,《本杰明·巴頓奇事》與《初戀五十次》的要素融為一體(甚至有傳言說后者立意來自于《海伯利安》,不過幻想元素的雜糅無法確切考證了)。第五個偵探的故事中,除了AI寄身于賽博體這一概念,幾位角色侵入數據平面層,在賽博空間出生入死都是標志性的威廉·吉布森式情節。吉本森的粉絲看到人物對話小小地調侃一句“牛仔吉布森”,想必能會心一笑。甚至七人中的一名某夜離奇消失留下血跡,也是阿加莎式暴風雪山莊的經典橋段。所謂小說類型,或者亞型,在熟手面前都不過是敘事工具,依據需要隨意調用。西蒙斯的工具箱精當而完備,巧手裁剪、混搭,織出不可思議多元素融匯的奇錦。
每個短篇在三萬詞的篇幅下切到了足夠的縱深,使人物朝圣的動機得到合理解釋。西蒙斯還以可觀的篇幅引入宗教學的討論。亞伯拉罕三教與禪宗以各自代表人物為縮影繼續影響著未來人的精神世界。光陰冢朝圣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在伯勞面前許愿(七人中無一人信奉伯勞教),不如說是為了解開一個謎題與心結不惜舍生赴死,使一步一步邁向終點的旅程因死亡不斷迫近而具有殉道的壯美。伯勞以金屬之軀刺穿人體,將其高懸于痛苦之樹,本身即充滿基督受難的隱喻。而第一個故事中的耶穌會神父杜雷之歸宿的指向性則更明確了。他為了驅趕寄生的異形,“就像該死的羅馬人所做的”,將自己釘上放電的特斯拉樹,不斷遭受電擊致死而又重生,在痛苦中循環往復,日復一日,整整七年。根據西蒙斯對希臘神話的鐘愛(另一本小說Ilium——《伊利昂》——即以希臘神話為主題)不難猜測,神父化身的便是崇高的圣者與永恒的悲劇英雄普羅米修斯。
與信仰的追求同樣深刻的還有情感與倫常。極盡忘我的床笫之歡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上校在手掌翻覆之間便能讓一個星球的首領身首異處、百萬生靈涂炭,而他鐵石心腸的外殼下,卻難忘夢境一個女人肌膚的溫熱與柔軟。父母之愛呢,每天看著自己的孩子返老還童,除了為她營造一個被保護得很好的“楚門的世界”,還要面臨噩夢逼迫與孩子回到0歲可能憑空消失的兩難。所謂堅貞不屈的愛情,在丈夫保持青春而妻子日漸衰老的雙生子佯謬中如何承受歲月無情的變遷,遑論他們身后代表著互相沖突的兩個世界……如果說科幻的起點是一個個的“what if...?”(如果……會如何?),西蒙斯無疑將種種疑難推向了極致。大悲大喜,極大癲狂,迅疾的情感轉換帶來過山車般的閱讀感。
回到前面的問題,以點帶面來寫史詩,除了使選點有代表性,還要使每一個點不寫則已,一寫便刺穿肌膚,深入腠理,讓人過目難忘。西蒙斯的選點是稀疏的,這留給他更大的空間來鋪陳細節。熟悉《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的讀者不難發現,《銀翼殺手》里霓虹燈下的東京式都市街頭雨夜的經典場景并不取材于原著,而是電影的二次創作。如果將《海伯利安》影視化,供改編者的選材可能會更五光十色一些,因為西蒙斯在場景設定上從不吝惜筆墨。比如詩人前往都市核心TC2星球面見編輯。編輯的辦公室在超線尖塔大樓的最高一層,像雄鷹盤踞在星系最高最尖的頂峰,樓外空氣彌漫血色,巨大閃電布滿圓形辦公室三百六十度視野,室內地毯從房間邊緣垂下,墜入高達六千米的落差,詩人尋思:其他作者靠近邊沿時是否也想縱身而下?同樣居住在TC2星球的普通人大概享受不到出版公司的奢華。經濟稍好的得以在千篇一律的鋼鐵蜂巢小屋中蝸居,貧苦人士則遁入毒品與犯罪橫行不見天日的地下。代表都市繁華的一個星球就有數種建筑風格特異,從壯麗到冷峻切換種種視覺奇景。
地理分布上,想象一盤桌游,每個人物占據一個起點,比如上校在火星訓練營里長大,詩人出生于舊地球,偵探是一點三倍重力盧瑟斯星矮壯的本地人。接下來游戲開始,他們開始不辭辛勞地旅行,足跡不斷交錯成網。上校南征北戰,領事派往陌生國界,詩人流亡異鄉,學者舉家搬遷。在他們旅途中,我們一窺不同星球的標志物,有的以巨樹為艦,有的島嶼浮游。許多其他星球被浮光掠影掃過,形成眾星拱月的豐富場景。
鋪陳最多的毫無疑問是海伯利安本身。在星際穿越只需打開一道門的年代,海伯利安的交通方式接近原始。首先電磁場異常,大部分現代科技在此宣告失靈。危險荒野使得飛行器止步于人類聚集區。故事幾乎刻意地將神父送上了大航海時代般原始的傳教士之旅。追隨神父視角,我們從濟慈城出發向南面的鷹之大陸進發,穿過每年有數月薪火彌漫的火焰林,躲避一靠近就放電的特斯拉樹,到達高原之沿,站在地殼塌陷形成的大裂痕頂端,張開雙臂,俯瞰三千米瀑布湍流而下,完成一次風光加人類學的雙重探險(此處應有航拍)。
設定的刻意可以理解。好比孫悟空一個筋斗就能背著唐僧到西天,我們還有什麼《西游記》可看?同樣的低科技限制之下,朝圣者去往北大陸的行程也是路漫漫而修遠。不同于《坎》對行程幾乎只字不提,或者《一千零一夜》里“第一夜”“第二夜”僅作為故事名義上的序號,他們行程見聞本身也具有意義。朝圣者們從巨樹之艦降落到達海伯利安的首都濟慈城,一路向北。溯河而上的游船由許多魔鬼魚拖拽,沿途經過土著人的房屋,神秘氛圍極似《現代啟示錄》里的東南亞。下一站由數十億公頃高草組成的草之海則讓人想到儒勒·凡爾納筆下的潘帕斯大草原。這些根本不存在于地球上的風光既奇麗又有部分現實的參考因而可視可感。有趣的是,我曾在佛羅里達大沼澤國家公園的草灘上乘坐空氣船。因為任何的螺旋槳都必然被草掛絆,所以驅動船體使用的是吹動空氣的巨大風扇。書中穿越草海的風力運輸船顯然結合了這部分現實的合理性,雖然它的懸浮是虛構的。就像哈利·托特達夫《異星歧途》那樣,古老的船體與反重力的高科技奇妙并存,蒸汽朋克與賽博朋克可以共存于一本書里。
西蒙斯將大量的虛構與現實混雜在一起。書以幾百年后時代的人的語氣講述,對那時的人們來說是常識的某些東西,現在自然還沒有發生。比如在列舉偉大詩歌傳統時,在彌爾頓、拜倫、濟慈、迪蘭·托馬斯這些切實存在的詩人后面,接上了諸如吳僑之和埃德蒙·吉菲里拉這樣虛構的名字,并且有模有樣地為吳僑之安置了《最后的三月》這樣的代表作和死于大流亡前最后一次中日戰爭這樣的生平。即使這樣一個邊緣角色,也是分散于幾個地方分幾次慢慢提及,像是真的家喻戶曉的名字。這樣浸入式的信息披露顯得真實。除了借霸主CEO之口和領事自白突然交代主要勢力間拮抗的重大信息,西蒙斯對大部分設定的解釋都做到了自然地化入日常對話與情節。
故事的末尾,六位朝圣者到達沙漠的廢墟,并排向光陰冢走去。迎接他們的命運將會揭曉在下一本書里。有人說,海伯利安四部曲,百十萬言,只寫了一部序曲。那《海伯利安》第一部,在最吸引人處戛然而止,作為一部形式完美的小說留下便是序曲之序曲吧。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