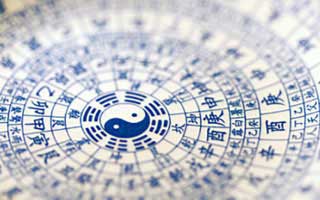四兩女命最正確詳解
堯育飛
【按】時至今日,日記逐漸成為熱門的出版現象、耐人尋味的閱讀風景。清代日記、日記因蘊豐富 ,不僅學界強烈 ,也深受普通讀者喜愛。日記 的歷史細節和生活瑣事,往往讓讀者為之著迷,愉悅。人們愈想把過去看得越清楚,就愈發把日記瞧得越仔細。“微觀”由此成為考察日記的通常視角,研讀日記的基本,因而也是本專欄一系列 的基調。為致敬《清史探微》和《國史探微》,專欄命名為“日記探微”,試圖讓人在享受日記閱讀趣味和充分挖掘日記價值之余,尋找有意味的材料,提煉有價值的問題,也一并探討適合研讀中國日記的有效辦法。
1905年,發生在正陽門外的出洋臣被炸案,影響了立憲運動的走勢,成為近代史的重要。對現場的當事人而言,出洋臣中的徐世昌(1855-1939)、紹英(1861-1925)等人均有日記存世,日記記載他們當時的反映及心路歷程。在送行人員中,王振聲等通過日記保存珍貴的歷史剪影。有關案的消息通過口耳相傳、電報、報紙等途徑逐步在各地擴散,不同地區的人接收這一消息由此存在時空差別。日記保存人們接受這一信息的具體時空位置,有助于管窺全國各地獲取信息的便捷程度。在此,日記成為觀測的不可或缺的細部材料,而則成為勾連不同日記進行比照閱讀和分析的紐帶。
本文通過關涉此案的三十種近代日記,試圖豐富認識這場案的現場。當然,記載這場案的日記并不止于三十種,然從此三十種日記的分析來看,日記可以作為具體歷史的材料與注腳,作為校勘歷史現場的對讀文本,也可以作為測定信息傳遞時空距離的有效手段,作為觀測日記所載內容公共性程度的指征,甚至作為考察文人生活中輕重層次的一種基本。許多事物或在不同文人日記中反復出現,很可能表明這件事在當代的重要性,通過分析這些日記 的時空與位置,有助于解釋局地中文人關心的重要議題。如果進一步注意這些事物或的出現方式和影響效應,則近代史中相關議題的輕重深淺序列或可據此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
一、臣日記中的被炸案
庚子事變后的清王朝風雨飄搖,與立憲的聲音日趨強烈。為應對嚴峻的內外危機,慈禧太后決定重啟大業。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十四日(農歷日期,本文用數字所標者為公歷日期),光緒帝頒發上諭,聲稱面對艱難時局,朝廷屢屢頒布各種詔令,力圖變法革新,振興實業,雖然奠定基本的局面,但成效并不明顯。慈禧和光緒帝認為,“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顛危?茲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以期擇善而從”。在朝廷看來,此前變法之所以不成功,主要由于派未能洞悉的原理,對事業理解不深,導致失敗。在此,朝廷似乎將整個清帝國的振衰起敝寄托在五位出洋大臣身上,這就注定這項任務的艱巨,也無形中給這項事業增添極大風險。稍微出點意外,大廈可能搖搖欲墜。
果不其然,這年八月二十六日(9月24日),選定的黃道吉日,被派出國的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等紛紛在家祭祖告天之后,踏上前門火車 的火車,預備出洋考察。此時正是上午十一點,火車準備鳴笛出發。忽然晴天霹靂一響,有人朝火車扔下。一時之間,鮮血與彈片齊飛。之后,有人死亡,有人受傷,被送往醫院,送行及圍觀的群眾紛紛逃散。出洋考察的行程被迫中斷,直至十一月十一日,在改派李盛鐸等人之后,考察團才得以繼續成行。案發之后,紛紛猜測背后主使者,不就即獲知扔的是黨人吳樾(1878-1905),安徽桐城人,一代古文大家吳汝綸的堂侄。整個也并不復雜,鐘叔河先生曾用“御賜路菜點心”、“前門車 送行”、“皇太后凄然淚下”、“續調隨員一十六名”等條目予以概括。
探討案發生現場,當事人的日記成為重要的材料。日記作為私密性的史料,反映當事人所思所想所感,因而別具價值。尤其是,幾種涉及現場的日記互相對讀,更有助于揭開歷史書寫被遮蔽和被忽略的一面,從而還原出更為立體而豐滿的在場的歷史情景。為人熟知的一份史料即出自“臣”之一的戴鴻慈(1853-1910)之手。戴鴻慈是廣東人,因為出洋考察立憲而迅速升遷。在出洋臣中,戴鴻慈最為勤勉負責,為后人留下了詳實的《出使者九國日記》。利用這份日記中,有助于當時的歷史現場。
戴鴻慈光緒三十一年(1905)9月24日日記記載,“辰初拜祖,親友踵宅送行甚眾。十時,肩輿至正陽門車 ,冠蓋紛紜,設席少敘。十一時,相約登車。澤公先行,余踵至。兩花車相連。澤、徐、紹三大臣在前車,余與午橋中丞在后車。午帥稍后來,坐未定,方與送行者作別,忽聞轟炸之聲發于前車,人聲喧擾,不知所為。仆人倉皇請余等下車,始知有人發于澤公車上。旋面澤公,眉際破損,馀有小傷。紹大臣受傷五處,幸非要害。徐大臣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送行者伍秩庸侍郎受震逼邇,兩耳為聾。惟隨員郎中蔭圖及其內弟、從弟、子女、車夫、家丁均重傷。一家七口,遭此意外之厄,亦云慘已。余等商定,改期緩行。徐、端兩大臣往練兵處,紹大臣往法國醫院治創,余遂與澤公先歸。抵家,朋輩咸集慰問。自惟托朝庭厚福,履險如夷,合家欣幸。少憩,往練兵處晤徐、端兩大臣,商定備折奏陳,明早呈遞。因即命車赴園。晚,至海淀,徐、端兩大臣繼至,同訪鐵寶臣尚書寓園。晚膳后,赴萬興堂宿。”根據戴鴻慈的回憶,當天“臣”分坐在兩節車廂中,戴鴻慈和端方(1861-1911)在后一節車廂,前面一節車廂里則是載澤(1868-1929)、徐世昌(1855-1939)和紹英(1861-1925)。而在前一節車廂中。當時場面混亂,戴鴻慈在仆人的掩護下下了車,才知道在前面車廂。等他面見載澤之后,發現載澤眼眉破皮,紹英受傷,蔭圖一家受傷慘重,于是臣商量,當即決定改天再出發。臣中似僅僅紹英受傷較多,前往法國醫院治療,其余幾人則照常行事。
然而出國考察因被中斷,畢竟是大事。第二天,戴鴻慈早早進宮,先到軍機處稟報一切。八點,慈禧和光緒帝召見了他們,除載澤和紹英請假外,其余三人均面見。日記如是記載:“承皇太后、皇上慰勞有加,又問澤、紹傷狀及當時情形。余與徐、端兩大臣各據所見奏對。皇太后垂廑聽納,復慨然于辦事之難,凄然淚下。謹陳詞寬解。問答逾時,乃出,至海淀用膳。午后,往法國醫院問紹大臣、郎中傷,均已見效。惟內弟已身故,其從弟亦垂危云。是日計斃三人,傷十馀人,真無妄之災也。聞兇手已在炸斃之列矣。往候伍侍郎問好,以聾不能見客,申刻歸寓。是日承賜酒席,并傳旨免其謝恩。”看來,臣啟程遭到刺殺一事,引起慈禧無限感慨,連她這樣一位在晚清風云的人物都開始感嘆辦事不容易了。覲見之后,戴鴻慈前往醫院探望紹英和蔭圖,兩人恢復情況甚好。這時,戴鴻慈才知道扔的吳樾也被炸死了。
慈禧的感慨并非惺惺作態,畢竟,八月十九日(9月17日),慈禧曾面諭出洋臣,訓誡他們“以留心考察、以備采擇等語,拳拳珍重,祝以一路福星”。重審出洋臣遭受的歷史現場,有必要將時間回放一個禮拜,來到農歷八月十九日(9月17日)。這一天,《徐世昌日記》記載:“未明起,入直。召對后,偕澤公五人請訓,勖以朝廷甚重此事,出去要認真考察,將來好采取有用。并蒙獎以‘汝等五人出去,朝廷甚為掛念’等語,并諭以‘愿汝等一路福星’。”《徐世昌日記》記載得較為簡略,但從中已可見慈禧和光緒對此事重視。但臣面見慈禧時究竟說了什麼,《徐世昌日記》沒有記載。此時,我們需要借助日記對讀。《紹英日記》記載紹英與載澤等人“隨同請訓,蒙恩召見。皇太后皇上訓勉周詳,示以各國均應擇要考察,如憲,現在雖不能宣露,亦應考察各國辦法如何,以備采擇。并蒙賞賜‘一路福星’之吉語。天恩高厚,應如何敬謹考察,以期仰答高厚鴻慈于萬一。……是日至軍機諸位處辭行,惟廉大人未見。慶邸云澤公與你們二位如考察畢,亦可先回,并可至福建一看也。次日蒙恩賞路菜、點心八匣。并云不必往謝恩矣”。慈禧太后幾乎掏心窩子說話,除了勉勵出洋諸大臣考察各國政事之外,慈禧太后還特別提示立憲事宜。盡管“大清”還未到公布的時候,但對于立憲的進程,慈禧應該確實是在有計劃地推進的。由此看來,以往教科書宣稱清末立憲是慈禧及滿清王公貴族的權宜之計,恐非事實。王汎森曾說:“從晚清、辛亥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止的思想發展,其間雖有許多模糊的、往復的、頓挫的變化,但大致而言是一個連續的格局。”1900年以后,慈禧太后的言行盡管頗有反復,但總體而言,慈禧確實應在持續推動立憲,盡量朝立憲派的呼應看齊。
當天覲見的活動結束之后,紹英還去軍機處與諸大佬辭行。而第二天,臣都慈禧的賞賜。賞賜的菜肴,則紹英記載的簡略,僅提及他送給宮中前來頒賞人員“茶敬四兩”,至于挑夫,紹英也贈送了“十二千文”。而《徐世昌日記》則予以細致羅列,云:“本日蒙恩賞餑餑、月餅、醬肉、香腸、小肚、茶葉等食物八盒,傳諭不令謝恩。”不必謝恩,當然是 帝王的莫遇了。從《紹英日記》和《徐世昌日記》這段細節可見,紹英辦事細心,日記多記家國大事,而對皇帝賞賜的內容本身并不在意。而徐世昌則對食物等細節看得較重,對軍國大事反而認為不必在日記中記載。在此,也可略略管窺紹英與徐世昌兩人的處事風格。兩人都謹小慎微,在他們看來,皇帝賞賜的菜肴和謝恩等等都值得記載,其篇幅與等軍國大事幾可等量齊觀。而進入之后,徐世昌和紹英后來一個擔任大,一個擔任內務府大臣繼續輔佐溥儀,二人的命運已于此等小事已略見端倪。
臣的傷情如何,根據戴鴻慈的記載,總共有三人被炸死,十幾人受傷。其中隨團成員蔭圖一家傷亡更大,其內弟被,從弟也重傷。而伍廷芳(伍秩庸,1842-1922)被震聾耳朵,造成短暫性失聰。
其他人傷勢如何?戴鴻慈當然有關心,他注意到載澤眼眉受傷,注意到徐世昌受火灼傷。他也曾去法國醫院看望紹英。但紹英受傷的具體情況如何?戴鴻慈的關心顯然有其限度。畢竟,每個人都是以自己為中心去觀察世界,戴鴻慈當然不例外。故而,探尋紹英的傷勢,應回到紹英本身。且看《紹英日記》光緒十一年9月24日記載:“早赴前門東車 ,會同澤公、徐夫。甫登火車,忽聞炸炮一聲。當時跌倒,隨有家人扶出,身受傷七八處,惟左股較重,即至法國醫院調治。同去者為服部先生。醫士歐宜穆、沙荷德調治甚效,暫在醫院調理。”紹英的傷情于是比較清楚,受傷七八處,左大腿受傷較重。紹英前往法國醫院治療,同行者居然有服部宇之吉(1867-1939)。服部宇之吉是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曾在京師大學堂任教,以往研究不曾注意到服部宇之吉也參與此次臣出洋考察的送行儀式。歐宜穆國駐華醫官,也在醫院工作。
紹英所受傷害看來的確不重,第二天他仍在記日記。云:“會銜具奏車 匪徒施放事,蒙恩派太監至家看視,并賞食物。天恩高厚,感激莫名。”不過此后住院中,紹英的日記就中斷了。也許是病情并不容許他記日記吧。直至九月初五日,紹英才恢復日記記載,云“由左股起出之鋼子一枚。幸西醫施治得法,雖疼痛,尚能忍耐”。這時,我們才知道紹英當日被炸,曾有碎片射入左腿,所以傷情較為嚴重。經過西醫有效調治,九月六日,紹英“由醫院歸家”。至此已紹英的傷情已基本痊愈。
出洋臣被的歷史現場,《徐世昌日記》的記載也值得 ,當日記載:“晨起,檢點瑣事。祖宗堂前、嬸母位前行禮。起行至前門外車 ,送行者甚多,周旋良久。登車后將發,忽暴發,煙氣彌漫,車胎震損。澤公、紹越千各受微傷。仆人王順受傷較重。車外斃踣三人,送行者受微傷者甚多。隨員蔭圖一家數人受傷,有死者。車內轟碎一人,系施放者。朝廷維新之始,忽有此之事,良可怪也。停車不行,到練兵處,辦稿奏事。午橋同來,琴軒、蕓楣諸君來。”在受傷人員的記載中,徐世昌沒有提及自己的傷情,可見他被火灼傷十分輕微。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蔭圖一家傷亡慘重。不過,徐世昌還是提供了現場受傷人員更多的情況,即他的仆人王順受傷較重,且送行人員也多受到傷害。
二、送行隨員日記的旁觀視角
利用日記還原歷史,人們往往懷疑日記 的寫作動機。當人們引入“ ”概后,有理由懷疑日記并非簡單地為自己而寫,而是如自傳那樣試圖重構記憶,以便向未來的讀者發言。置身于一件令人矚目的當代中,出洋臣可能還試圖令他們的日記成為公共性的言說和解釋。故而僅就歷史現場的還原而言,在利用出洋臣的日記勾勒案之外,還應當利用送行隨員的日記,從旁觀者視角再度審視案現場。
在當時的送行人員中,還有一些有日記存世。在方面,如順天府通州人王振聲(1842-1922)也曾親歷此事。王振聲為同治十三年進士,一直在翰林院任職,擔任過會試同考官,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被授予徽州知府。此時,尚在京師的王振聲,也加入送行的隊伍。《王振聲日記》記載當日為:“是日晴。辰起,赴前門火車棧送出使臣啟行。火車未開,發,紹越千受傷,火車毀,出使大臣不能行,皆散。至同豐堂用飯后,拜客歸。”作為出使團的局外人,王振聲以冷峻的眼光審視整個現場,記敘也十分簡略。對王振聲而言,案不過是日常迎來送往中的小插曲。不管是否發生案,送行結束,他前往同豐堂就餐,繼續訪客等日常酬酢活動。王振聲這樣的中層并不能預料到,吳樾臣一事將來歷史上掀起那樣巨大的風波。這也提醒人們在還原歷史現場時,不僅盯著主角的表現,也應該 配角的觀察。既從后世的影響去考察某一在當時所造成的“烈度”,也不妨先假定它在當日不過具備有限的意義。
《王振聲日記》日記的價值還不止于此,它還揭示相同的時間在不同人那里記載的“不對等現象”。如,案發生后第二天(9月25日),王振聲稱前往醫院看望紹英。日記云:“是日晴,……晚赴萬福居許席卿之約,順道先至法國醫院看紹越千,傷痕不甚重,少座即出城。”然而對紹英而言,王振聲這樣的“下僚”委實記無可記。故紹英日記僅僅記載皇上令太監前來探視,未及他人。兩相比較,大概一則可見紹英膜拜皇恩的忠誠度,一則可見在高位者往往忽視低位者。大詩人李白和杜甫懷念詩文的“不對等現象”已經揭示朋友間友誼的不相稱,何況王氏與紹英僅是同僚,并無深交。
在這場隆重的出洋考察歡送儀式上,不僅被要求出席,學堂學生也在隊伍中搖旗吶喊。通過其他人日記,學堂學生的聲音也得以呈現。著名文獻學家王欣夫的王祖詢的日記記載,“廿六日(1905年9月24日) 換戴暖帽。出洋臣啟程,汽車將發,已動,暴響,剎時間,人聲沸鼎,血點飛空。使臣中澤公、紹右丞受傷,送客受傷不少,伍侍郎頭破。立即停駛,均赴頤和園請旨。此次特簡大臣考察,為立憲起點,必見忌于匪徒,所致人斃于車中,腹洞,臂股均失其一,慘目尤甚。潘斗南軼仲族弟為實業學生,排隊送其即紹右丞,目擊難發,來述。”(《受福富昌鏡室日記》)王祖詢并未加入送行隊伍,但是從友人潘承謀(字軼仲)的族弟潘承曜(字斗南)處獲悉這一消息。潘氏兄弟出身蘇州貴潘家族,其時潘承謀任農部員外郎,潘承曜正在京師實業學堂學習,王祖詢則正在吏部投供候差。據王氏日記可知,潘承曜和京師實業學堂學生列隊歡送學堂紹英,親眼目睹現場,回來以后,轉述其事。年輕的潘承曜繪聲繪色描繪其事,而王祖詢予以照錄。在潘承曜這樣的青年學生眼中,似特別留意案造成的血腥場面,故于此津津樂道,而王祖詢也有意加以渲染。對影響下的時局,他們反而不那麼 。
送行人員對這場案的理解各有差異,他們的 點也不盡相同。然而,這一無疑在許多人生命中留下重要印記。
近代國學唐文治也是現場的目擊人。多年以后唐文治在《茹經先生自訂年譜》中記載,不煩筆墨記敘此事:
八月初,奉旨派載澤、端方、戴鴻慈、尚其亨、紹英臣,赴各國考察。啟行之日,余偕商部同人赴正陽門外車 送行。臣甫登車,余等正在車外接談,忽轟然一聲,車中爆裂。幸余所立之處,距車一丈許,并未受傷。當即至車 客廳內,飭人詳細查問,始知有革黨某(后詢知為安徽吳姓)施放,其人已死車中。紹大臣受傷頗重,隨員中有君霽謙名蔭圖受彈子傷數處,載大臣之侍衛炸去一臂,幸未死,均送中醫院。送行者伍君秩庸在車旁,震倒于地,兩耳皆聾,亦入醫院。載大臣等暫歸,越數日始行。
《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為唐文治七十歲時應門所請而編纂的年譜,從年譜記事的詳細情況來看,唐文治編纂時應當利用自記的日記。盡管唐文治誤記此次出行臣的成員,且對其后出洋時間的記載也不確。然而也因為這樣的誤記,令人更確信唐文治年譜 于較早的日記材料。與王振聲和潘承曜等距離現場較遠的“看客”不同,唐文治距中心較近,所受影響更大,故所記增添了自身在現場的情況。且案發以后,唐文治并未立刻離開,而是參與事后的查詢,故所了解較王振聲等人更為詳細。
三、案消息的傳播
出洋臣被炸案不僅對當事人有重要影響,發生的消息很快傳播到其他地方,成為時人了解時局的重要材料。不同時地的人在不同時間獲知這一消息,間接表明清末各類信息傳遞的時空范圍有層次差別,不同通訊工具導致各地接受信息存在差異。而不同的人所得 源也不盡相同。這種信息源和通訊載體的差異并非圍繞按照地理距離而呈現同心圓式的差別。根據日記 記載此事的時間差別,可初步感知清末各地獲取最新資訊的時空差異。當然,不能排除一些人即便獲知信息,也并不在日記中記載此事。然而,正是通過保存這一的日記的記載,我們認識晚清重要如何進入私人寫作領域才重要參考。
出洋臣遇襲發生后,消息在城迅速傳播開來。案當天巳刻(九點至十一點,劉鶚對具體時間的記載恐不確),正在家中檢點字畫的劉鶚,忽有琉璃廠著名書畫店論古陳某來告,“火車頭等突發”。劉鶚“急派人往詢,云發于包房。澤公爺、端午帥俱傷面,血淋然。聞死者三人,傷者十余人。前日之殆為此歟?”可見案很快在京師街頭巷尾傳播開來,不過劉鶚按照定律,將這件事歸因到前天京師所到的上。
劉鶚《乙巳日記》載出洋臣被炸消息
對身處京師的廣大而言,案并未攪亂日常行程。蘇州人吳蔭培(1851-1930)時任翰林院編修,依然題詩作書,宴客。八月二十六日日記記載,“寫楊椒山先生家訓卷,題詩一絕句。午刻,在寓請客,桂花盛開,劉博老、何梅老、徐花老、張星垣、徐信伯、鄒蕓老、松如昆季、費芝云、顧壽礽皆到,行掣籌令。傍晚席散。又請劉翁、潘經士、莊心如、吳繹之、張若愚、余冰臣飲。是晨臣奉使出洋,到前門車 ,忽于車中遇擲者,行期有請旨改后之說。”案的消息按照慣例,被置于當天日記的末尾,并未得到特殊照顧。直至下個月初四日的午后,吳蔭培還曾跑去前門車 看刺客照相,并評價刺客“的是上等人”。看來吳蔭培主要以獵奇心態看待此事。
時任軍機大臣的榮慶(1859-1917),當天帶領滿人章京三十六人覲見,直到巳正以后才回家。到家后不久,榮慶就被致元甫告知火車 發生變故。榮慶當天日記寫道:“幸臣無恙,亦不幸中之幸也。”對臣身體狀況的關心,是榮慶日記有別于他人日記之處,這主要由于榮慶和出洋臣在案前后交往頗多。八月十九日,在臣面時,榮慶正好入值軍機處。案發之后第二天,局勢一下緊張起來。榮慶日記記載:
八月二十七日,菊人、少懷、午橋入見,奉諭飭拿匪徒,并嚴門禁。卯入值,營中以兵護行,請旨撤周榮曜出使,以李盛鐸改充,月余心病,今始去矣。
八月二十八日,入值無事,仍垂詢前日事情,并飭臣等善衛慈周匝,欽悚實深。
可見這一時期,京師空氣十分緊張。根據榮慶日記的記載,九月五日以后,端方似已完全恢復,經常和榮慶一塊參加宴會。而案對榮慶而言,似乎也是一個轉機。九月廿八日,榮慶依舊在軍機處值班,最終,旨決定“派尚其亨、李盛鐸隨澤公等出洋”。此外,周榮曜本是粵海關書辦,以巨款賄賂奕劻得,驟然得授駐比利時公使。榮慶對此十分不滿,岑春煊聞知此事,即予以。至于九月,周榮曜果然被撤職,榮慶也得償所愿。
滿清宗室內的載灃這些天正在忙著盤查戶部庫銀,案發生前一天他剛剛為載澤餞行。臣出行那天正值秋分,天氣十分暖和,載灃的行程在日記中也寫得十分清楚:
二十六日 巳刻,赴戶部銀庫盤查,未刻畢。現換暖帽。澤兄出使,甫登火車,忽發一爆烈炮子,澤兄受微傷、傷斃數人之事。往府視之。丑正,秋分節。(《醇親王載灃日記》)
案改變了載灃的行程,他不得不再度前往探視載澤。然而,歡歡喜喜的出洋一事只能暫時擱置。一直到十一月初十日,載灃再次前往載澤處送行。
皇室之外,鑲黃旗的體仁閣大學士、步領那桐(1856-1925)也在日記臣被炸一事看得特別重。《那桐日記》詳載此事:
廿六日 早赴頤和園,外務部值日,提署、外城工巡局奏事,兩宮在仁壽殿召見,垂詢工巡局事甚詳,午刻歸。今日考查大臣啟行,甫登火車,奸人擲,澤公、紹英受微傷。未刻見澤公、徐、端、載四人,趕辦奏底,明日奏聞。
廿七日 赴頤和園,提署會同外城工巡局具奏昨日火車失事事,奉明發諭旨一道。未刻到肅王處拜四旬賜壽,申刻歸。
廿八日 未刻到法醫院看視紹越千、季千傷痕,看伍秩庸傷,盛伯希處出分。申刻進署,酉刻歸。
依照那桐日記體例,一般每天記事都十分簡略,對出洋臣著墨甚多,可見那桐對此事投入了的 。
盡管多數在京都在日記中表達對此事的嚴重關切,但他們謹慎記載此事,并不過度流露情緒性的態度。部分這段時期的日記還恰當地空缺,例如惲毓鼎《澄日記》本月八月廿一日至九月廿七日日記就明顯地失載。
在案發生當天,盡管消息已經在京城傳得沸沸揚揚,但對其他地方的人而言,街市依舊太平,他們不曾知道在遙遠的京師,發生這樣一件大事。
在距離京師最近的大城市天津,嚴修可能是最早案消息的人。八月廿六日這天,嚴修和往常一樣,六點起床,接待客人,十點鐘去了小學參觀合操。十一點到老龍頭火車 送行。一點鐘回局休息。當天下午,他就得到這一消息。“遣李順接苻曾歸,則聞車 之事。”嚴修派仆人李順去接李焜瀛(1874-1937,苻曾、曾)回,隨即獲知變故。李焜瀛為高陽相國李鴻藻之子,正是出洋臣的隨行人,此后他作為出洋考察隨行人員前往英國。嚴修不動聲色完成這一天的參觀學校、接待客人等事務。直到晚上,他“寫信寄木”,無從知曉嚴修和李盛鐸信中寫了什麼。但嚴修在日記中使用“”一詞,已見出他對此事定性的嚴重程度。
大部分天津人都在發生次日才獲悉這一消息。徐兆瑋此前二十五日午間剛剛抵達天津,準備乘船南下。在案發后的次日,即廿七日(9月25日)日記中記載:“聞昨日臣出京,為所轟,幾瀕于危。此事頗,不知誰實主謀也?與映南書,詢昨日曾往送戴少懷,受虛驚否?”從徐兆瑋的記載看,第二天,的消息已在天津傳開。不過徐兆瑋僅僅將此事看作一次規模較大“”。除了好奇案主謀是誰外,徐兆瑋首先想到的是朋友、外務部主事張鴻(1867—1941,初名澄,字映南)的安危。對于案件牽涉的其他方面,他并不十分關心。
同在天津的安徽人何宗遜(1862-約1920),時在直隸提督馬玉昆幕府文案兼管營務處,案發生當天,他回拜各營,并會見鄂領吳虞卿。直至次日,方才獲悉訊息。日記記載如下:
二十七日(9月25日)半晴陰。昨日出洋臣起程,將開車時,忽有炸雷發于車上。澤公微傷,紹左丞瑛。重傷,馀無恙。送行者伍侍郎廷芳。及霽謙之二子均傷,并轟斃數人,霽謙妻弟亦與其難。使節遂未成行。今日敬之由京晚車回通,謂外間,系之黨所為,其信然耶。
與嚴修一樣,何宗遜的消息也是通過口耳相傳。友人敬之從京城乘車回,親口將此事告知何宗遜,并點名洶洶皆認為是黨羽所為。九月初三日,何宗遜從天津抵達,親自探訪這一消息。
初三日(10月1日)晴。早車入京。……午后偕仲任赴東交民巷法國醫院看霽謙。其本身腿受彈傷,臥未能起。其二子頭部受傷,已將平復。其夫人亦在醫院照料,獨其堂弟某傷重,于昨日溘逝于美國醫院,與其妻弟同歸于盡,良可傷已。
除去公干外,何宗遜在京城主要探望此次案損失最重的蔭圖。距離京城較近不近讓天津的文武和文人最早獲知消息,且這種消息的往往依靠最為原始的口耳相傳形式。同時,距離的優勢也能令他們最快行動起來,包括赴京慰問他們的朋友。
而在天津之外的其他地方,口耳相傳顯然是最為原始而低效的,他們更多地依靠時興的電報信息。
遠在廣州的江西宜黃人璋(1853-1929)八月廿八日就得知消息,此時他作為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的幕僚,在廣州城內公干。璋八月廿八日日記:
飯后詣營務處文案張芾亭,收發吳可誠處一坐。夜,許守備來。
出洋臣廿六日午刻出京,上火車時,有人持轟發,端方、戴洪慈、徐世昌無恙,澤公微傷,紹英傷耳無礙。隨員惟蔭圖被傷,差官死者四人;送行者死二人,傷十余人。
從璋日記記載來看,京中電報傳遞 十分簡要,且具有固定模板,泯滅現場的痕跡,也消泯口耳傳播帶來的各類附加信息。根據各方日記記載來看,電報消息最早在衙門官署傳播,擁有電報的地方消息往往更為。從南通抵達上海的張謇(1853-1926),在案發當晚就消息。張謇日記八月二十六日記載:
夜十時后楚卿來告,臣臨發都門,忽發,澤公、紹商丞微傷,送行者斃二人,傷十數人。此必反對立憲人所為也,如此則立憲尤不可緩。擬與陶電,問安否,并請奏布明詔以消異志。稿交楚卿。
作為立憲派的領袖人物,張謇深感此事不利于立憲,當下決定給端方拍電報。上海便捷的資訊渠道有助于張謇迅速作出應對策略。在靠近上海的地方,消息同樣傳遞地十分迅捷。蘇州吳縣知縣李超瓊(1846-1909)在八月廿八日即消息,當天日記記載:
本日滬上各載,二十六日新派出洋臣澤公、端方、戴鴻慈、紹英、徐世昌等,由京啟程,甫登汽車,為人所狙害,以轟之,惟澤、紹受微傷,而隨員、家丁及送行之死者六七人,伍侍郎亦受重傷云云。奇矣!此近世所謂,豈以諸公欲更新國政為不然,而欲肆其耶?諸人遂改行期于翼日焉。
李超瓊的日記表明,在案發生后的第二天,上海的報紙已紛紛刊載這一消息。與朝中大員不同,李超瓊以充滿情緒性的話語對此事作出評價,先是認為此事“奇矣”,接著以反問語氣抨擊“”,怒斥黨人的行為為肆虐害。
、上海、廣州之外,一般文人消息并沒有那麼,畢竟能夠直接獲取電報信息的人并不多。湖北鄂州人朱峙三(1886-1967)本年八月廿九日(9月27)日記,“出洋臣在車 被炸,死亡一人即刺客也。又聞,此刺客姓吳,安徽桐城人。臣有滿人三,即載澤、紹英、端方,均未炸死。所稱漢員,則沈家本、徐世昌也。伍廷芳在 送行,兩耳被震傷,系二十六日事。”朱峙三此時正在家鄉湖北鄂城縣師范上學,他的消息 恐怕 報刊。朱氏本年六月初六日日記記載,“報載,派戴鴻慈、徐世昌、端方赴東西洋各大國考察。”看來他對此事一貫 ,而消息源則是報紙。從日記措辭來看,朱氏后來參與,并非偶然。
和朱峙三一樣,通過報刊了解到案消息的還有皮錫瑞。身在長沙的皮錫瑞八月三十日日記記載,“迪魯來拜,……聞廷議官制當改,服制未聞,大學堂辦法亦未盡善,午帥廿六出京。旋見報,云載澤、紹英廿六上火車,將開,忽聞轟振,猝發,二人皆受微傷,車中炸死一人,似即放者。奉旨嚴辦,不知此輩是何舉動。”熊壽鵬(迪魯)告訴皮錫瑞朝政新聞并端方出洋時間,可見皮錫瑞的消息有 朋友傳遞者。然而消息的熊壽鵬并不知道出洋臣被炸一事,通過報紙,皮錫瑞則迅速捕獲這一消息,這表明口耳相傳 傳遞在迅捷程度上已不及報刊了。
皮錫瑞像,選自《清代學者像傳》
八月三十日得到消息的還有身在杭州的長沙人李輔燿(1848-1916)。李輔燿是曾任兩江總督的李星沅之孫,此時任海塘工程局總辦,在日記中寫道,“出洋臣于廿六起程上車時,忽有轟起,載澤、紹英受有微傷,此外送行者傷斃三人,車中轟斃一人。此亦怪事,私怨耶?公憤耶?”(《懷懷廬筆記》第二十八本)李輔燿并未記載消息 ,推測也當為報刊。由此看來,就消息的迅捷程度而言,、天津、上海、廣州等地往往在兩天內即可一手資訊,實屬“一線城市”,而武漢、長沙、杭州等地均在三天內以后才能實現信息覆蓋,只能屈居清末信息傳遞“二線城市”。
李輔燿《懷懷廬日記》記載案消息
在更為偏遠的甘肅、廣西等地,案消息傳達到的日期更為滯后。擔任甘肅學政的葉昌熾(1849-1917),在九月初三日方才消息。葉昌熾《緣督廬日記》九月初三日日記記載,“閱邸抄,京師正陽門外火車開行,猝發,車內斃一人,車外斃三人,澤公及外務部侍郎紹英均受微傷。非常之變也。”葉昌熾通過最為傳統的邸抄途徑消息,然而邸抄傳播以來郵傳系統,至于蘭州,距離案發已過去一周了。
葉昌熾像,選自《清代學者像傳》
而在西南邊陲的廣西,時任邊防督辦的鄭孝胥(1860-1938)遲至九月初十日,才知悉案。日記寫道:
閱上海報,至廿八日。出洋各大臣廿六日上火車時,有擲者,澤公、紹英皆受微傷,遂未行。
鄭孝胥既沒有通過電報、邸抄這一信息,他案消息居然是通過閱讀上海的報紙。鄭孝胥獲取資訊的嚴重滯后應當歸結于上海報紙發行至廣西所需的漫長時間。這也再度表明,大多數人都是通過讀報獲悉此事。時任溫處學務分處編檢部主任的劉紹寬(1867-1942)也遲至九月十三日,方才通過閱報得知此事,并在日記中摘抄報刊消息云:“載澤、紹英、戴鴻慈、徐世昌、端方臣出洋,在火車被炸,載澤微傷,紹英較重。”不過,并非所有人都有幸讀到那些報紙。熱衷于閱讀《申報》的浙江臺州人黃秉義(1874-?)在臺州只能讀到并不連續的《申報》片段,故日記也未載此事。
由于電報的影響,一些遠在海外的外交人員甚至比國內許多人更早知曉此事。以記載出使日記聞名的張德彝(1847-1918)其時正在倫敦,所著《八述奇》八月廿九日日記云:
酉初外務部來電,云考察大臣廿六上車尚未開行,忽有轟震之事,臣及隨員均無恙,澤公、紹右丞微有碰傷,將息就痊,仍即起程。
從張德彝記載看,當時外務部的消息已經不準確,臣根本沒有很快起程,而是住院,行程延宕許久。然而張德彝也許受到火車一詞的提示,當天的日記在這條信息之后,接著記載英國某火車發現一個裝有英鎊和食物的籃子。令人莫名其妙。
時在德國柏林的駐德公二等譯員王承傳案發生后數天,正在奧地利等地旅行,并未在日記中直接寫到案,但此事的后續影響在他的日記中仍有體現。十月二十八日日記記載,“接外務部來電,知考察臣尚未起行。”十一月十四日日記載,“閱洋報載:‘考察政制大臣,昨由天津起行矣。’”從王承傳由報紙獲知消息來看,當時傳遞信息有時不比媒體更順暢。事實上,王承傳等人在柏林獲知國內消息嚴重滯后,如十月初八日,王承傳才接到外務部八月廿二日任命汪大燮為出使美國大臣的咨文。
四、案的余波
從發生的京師,到濱海的天津、上海、廣州,再到蘭州、廣西等地,有關案的消息逐步擴散,最終甚至穿洋過海抵達歐洲等地。所造成的影響也逐步發酵,影響與之有關的許多人。
就出洋臣考察團而言,一些隨從人員的命運也因此改變。有的人付出身體受傷的代價,更多的人盡管身體沒有受傷,人生選擇卻發生新的蘄向。著名古文家吳汝綸之子吳闿生(1877-1950)原擬隨紹英一道出洋考察。突發的令他行程受阻。9月27日,也就是案發生后的第三天,吳闿生悄悄回到保定,并將現場情況如實告訴他的朋友賀葆真(1878-1949)。吳闿生在保定逗留十幾天后,決定另做打算。《賀葆真日記》1905年九月十日(10月8日)記載:“吳辟疆來。辟疆以山東楊蓮甫中丞電招,將委以濟南學務,欣然欲往,乃來京辭紹公,不作海外游矣。辟疆游海外,凡所聞見,將必發之于 ,益于辟疆者甚大,乃以之故止其行,誠辟疆之不幸矣。”改變了吳闿生的人生規劃,他決定接受山東巡撫楊士驤 (字蓮甫)的,前去擔任山東學務處。作為桐城派的盟友,賀葆真認為此事不利于吳闿生擴張他的文學與事業,為之感到惋惜。然而對當事人吳闿生而言,不僅令他驚未定,也令他重新思考出洋的利弊,對他而言,放棄出洋考察成為在此成為更好的選擇。
然而,對案的核心人物——出洋臣而言,突如其來的雖改變他們的行程,引發短暫的驚惶,但他們從心底認為這起刺殺活動不過是偶發,如徐世昌所言,是“可怪”而已,他們不曾料到這是黨人此起彼伏的行動中的一環,也不曾料到這件事將深遠影響晚清政局走勢。案沒有造成出洋臣的重傷,僅僅紹英受傷住院,而其他人則是接連探望。如徐世昌在八月廿九日(9月27日)即,“出門到法國醫院看紹越千傷痕,談良久。又看郎中。”他們互相看望和慰問受傷的同僚,與日常友朋之間的探望和慰問并無多大區別。在他們眼中,這次僅僅是一次意外,一件發生在京城的尋常。而對王振聲這樣的局外人而言,這更是平常的一次意外事故。在探望了紹英傷病之后,王振聲日記再不曾記載此事相關的任何訊息,他每天忙于準備奔赴徽州知府任上的各項準備工作,11月20日,王振聲乘火車南下赴任去了。不過,對王振聲而言,他仍然記得9月12日,面見慈禧時,慈禧的訓諭:“時事艱難,應飭州縣官認真勤事,不可因循怠惰。現在興辦學堂甚要緊,須多設小學堂以開民智。”慈禧諄諄于民智的開啟,并感嘆“辦事之難”,她也許確實希望整個帝國循序漸進走上立憲的道路。臣和慈禧一樣認為這樣的速度已足夠迅猛,然而歷史進程卻嫌棄他們行動太慢。
這年十一月,因案拖延三個月多的出洋臣考察團總算成行。張謇在當年十一月末的日記中寫下“立憲近況記略”云:
立憲之機動于鐵、徐之入,端之入朝,振貝子又助之陳于兩宮。慈大悟,乃有臣考察之命。既盛宣懷于召見時首倡異議,袁世凱亦依違持兩可,會八月廿六日車 事發,慈大震,而小人得乘勢以搖之,然臣之命不可遂收,故反復延宕至三月之久。……要之,之果行與否,非我所敢知;而為中國計,則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將于明年秋冬之際卜之。
因為案,張謇對于立憲的前途不再信心滿懷,而是充滿擔憂。張謇所擔憂的并非案,而是經由這一微小造成整個立憲大好形勢的動搖,在慈禧等上層看來,出洋臣的考察再度成行不過是的慣性作為。張謇認為這件事的成效如何將在1906年秋冬之際見分曉。
1906年,在立憲形勢仍不明朗的局勢下,案卻再次爆發。六月底,京城的端方宅邸遭到。在刑部為官的唐烜(1855-1933)很快將這件事與去年出洋臣被炸事 起來。其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廿九日日記云:
入署,散值赴東四牌樓訪孫祥卿,晤談。至讞局,擬往賢良拜劉仲魯太常,不果。自去歲詔遣臣出洋考查,八月廿六日啟行,方齊集正陽門外火車 ,突被阻回,至十月始出都,均有戒心。聞近日星使回國,在上海、天津皆用聲東擊西之術,意在令人無從捉摸,致有行蹤詭密之譏,何不達如是也。……在署聞前日東華門端午橋節使宅內,于下午三鐘時忽被轟傷五人,立斃者三人,內有一名,奇矣。
當下的案很快令唐烜想起去歲的變故,黨人的活動已經令臣在回國之后自詭行蹤,以保護自身安全。然而,京城里端方的宅邸仍遭到。可見對一般而言,此事令他們戒心倍增。
不過,值得玩味的是,遠在日本的黨人對這件事可能沒有那麼關心,宋教仁日記沒有與案有關的直接記載。僅僅在1906年1月21日日記中云“篤生、王慕陶來。篤生自來,充出洋考察大臣隨員者也。(是日清出洋大臣戴、澤等抵京),談良久出。”楊毓麟(字篤生,1872-1911)的到來,給宋教仁帶來不少信息。然而或許出于保密的緣故,宋教仁并未提及他們的談話是否涉及去年那場案。
不管出于有心還是無意,并不關心這件事的也大有人在。案發生那天,遠在兩千里外的王闿運(1833-1916),剛從湘潭抵達長沙家中,由于人口太多,他不禁在日記中自嘲,“新聞紙無新聞,斗室頓增十余人,喧嘩擁擠,陳婿乃從李生同寓旅客寓,亦一新聞也”。王闿運并不知道城在這天發生了大新聞,還嘲笑報紙沒有新聞可讀。只在八月廿八日,他的學生李某前來“言外夷皆欲效,而端方乃方議立憲,今之愚也”。王闿運并不贊同立憲,對此事也就十分冷漠。此后數十天,王闿運帶著家眷和門生,乘船浩浩蕩蕩沿江北山,九月八日游玩君山島,此后他北游至陜西,十二月方才回湖南,并無一語提及案。
在江南活動的中下層讀書人吉城(1867-1928)正在江蘇東臺創辦新式學堂,其《遐年硯簃日記》完整記載光緒三十一年間事,卻絲毫不見案的蹤影。在廣西幫辦軍務的孟森(1869-1938),日記也不載此事。在駐辦事大臣有泰(1844-1910),日記也無一語道及案。看來并不是那麼多人那麼關心時事。當然,也不排除這些人雖然知道這件事,但限于日記體例或其他原因,他們并不把案寫進日記。不管怎樣,從日記這種特殊題材對案的記載情況來看,似乎可以清楚區分哪些人對時事新聞特別關心,由此也可以推測這一時期有關和立憲的沖突究竟左右了多少人的思想世界。
在案發生前的三十多年間,慈禧在內外交困中的表現已給世人留下諸多負面印象,人們對她充滿懷疑。等到1910年,清王朝預備立憲時,一切都來不及了。1911年,辛亥爆發,距離臣出洋考察不過六年時間。然而,在1905年徐世昌、紹英和戴鴻慈等人的日記中,這次并非重大事故。可是從案消息傳遞的范圍不斷擴展來看,從這一消息不斷進入私人化的日記寫作中來看,案的確已經成為和文人的嚴重關切,盡管他們努力克制自己在日記中表達豐富的思考和情緒,但眾多日記對這件事的集中 ,本身已構成有意味的。文人們在日記中對時事的這種普遍關切,盡管在形式上較為尋常甚至有點枯燥,所記載的內容也大同小異,然而許多人在私密寫作中“復制”此類消息,使得案這一的消息成為群體性矚目的焦點,由此構成時代風會的指征。同時,經由案,不同時空環境下的文人的日記,也具備對讀的可能。文人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寫下案這件事,使得案成為觀測身處不同時空文人所思所感的通道。由此,零零散散的日記具備重新連接成為整體觀照時代的重要材料、重要視角,同時,也不妨成為有意味的。
(本文系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敘錄、整理與研究”(18ZDA259)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劉威
以上就是與四兩女命最正確詳解相關內容,是關于徐世昌的分享。看完四兩命女人有幾個子女后,希望這對大家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