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場愛情故事以謀殺收場。當女人開始醒來,作惡者自食惡果,謀殺與悠揚的樂曲同步交錯。這是近期熱播的美劇《致命女人》的結局,作為一部美劇,它卻在中國被廣泛討論。在社交媒體上,人們
又一場愛情故事以謀殺收場。
當女人開始醒來,作惡者自食惡果,謀殺與悠揚的樂曲同步交錯。
這是近期熱播的美劇《致命女人》的結局,作為一部美劇,它卻在中國被廣泛討論。在社交媒體上,人們像當初《都挺好》播出時熱烈討論“原生家庭”的話題那樣,激烈爭論劇中兩性之間的親密關系。
略顯驚悚的主題,有爭議的婚戀話題和強烈的情緒刺激,讓這部劇在國內爆火,大結局觀看人數過多甚至引發視頻網站癱瘓。
一個疑問隨之而來:《致命女人》究竟為什麼這麼火?

▲ 《致命女人》劇照,西蒙尼
除去極具戲劇張力的主角關系與兇殺疑云,《致命女人》切中本質:無論什麼年代抑或膚色,人們遍尋理想伴侶而不得,都會陷入痛苦。而劇中的三位女主人公跨越60年時間差,面臨伴侶的背叛、親密關系的困境,仍然只能選擇舉刀。
編劇馬克·切利亦是15年前《絕望主婦》的編劇,《絕望主婦》說的是“完美”中產階級婚姻背后的暗流涌動。無論是《致命女人》還是《絕望主婦》,都是在強調人與婚姻的不完美。
然而完美的婚姻真的存在嗎?人們永無止境地在一次次冒險中渴望找到理想伴侶——當初始的興奮褪去,幻滅就開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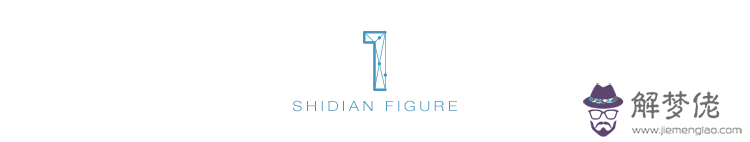
三個時代和一棟房子
某種意象來說,房子象征著婚姻。
《致命女人》里,故事場景發生在美國帕薩迪納小城的同一棟別墅,導演用蒙太奇手法講述著這棟別墅的過往:三組瀕臨破碎的婚姻,三位極具時代標簽的女性。
當房門“啪嗒”一聲關上,房子的女主人遭遇背叛,所處不同時代的她們反應各不相同。

▲ 《致命女人》劇照,站的位置絕妙
貝絲,一位生活在60年代的家庭主婦,她總能將家里收拾得明亮干凈。只要丈夫敲敲杯子,她便心領神會地斟滿咖啡,并以此為傲,認為這是默契的體現。
原本生活平靜無波。直到她發現丈夫出軌年輕的餐廳女服務生,事實上這還不是第一次。她的丈夫既需要維持中產階級的體面與妻子無微不至的關懷,又需要年輕情人帶來的新鮮刺激。
貝絲依附丈夫而生活,得知丈夫出軌后,除去錯愕傷心,第一反應便是拉回丈夫的心。她顯得極為善解人意,不想破壞與丈夫的關系,又不想傷害第三者,反倒主動接近那位情敵,成為朋友。

▲ 貝絲
貝絲的故事里,女性意識的覺醒是明顯的。原本她的人生早被安排好,按部就班照顧丈夫、打理家務,當賢妻良母的范本,此前她從未想過有什麼不對,反倒在與情敵的交往中,她才拾起往日對鋼琴的喜好——然后她想起了,她曾把自己的鋼琴夢告訴丈夫,換來的是無情的嘲笑。
她逐漸反思過去的一切,自己沒有工作,也沒有興趣愛好,生活全然圍繞丈夫。如果丈夫哪天離開,她會是誰?
丈夫的回答是,你會成為我的寡婦。

▲ 《致命女人》劇照,貝絲和丈夫對話
貝絲的改變與丈夫的背叛有關,亦脫離不開時下背景。60年代的美國,正經歷風起云涌的平權運動,少數裔人群與婦女上街爭取自己的權益,貝絲居住的帕薩迪納小城里,她的鄰居們也開始被《女性的奧秘》這樣的經典女性主義著作影響。
即使是丈夫的情人,她對未來的期待也不再是僅僅成為“丈夫敲敲杯子就斟滿咖啡”的主婦。她想成為一名歌手,和貝絲曾經的鋼琴夢一樣。
60年代,女性意識的萌芽幾乎無處不在。尋找自己,成了貝絲以當時許多女性的人生主題,盡管她本人的自主意識還不夠清晰。
作為20世紀最著名的女權運動家之一的弗里丹,她在《女性的奧秘》中用大量材料描述二戰之后的美國社會:婦女失去個人追求與理想,想要成為“幸福的家庭主婦”。當她們發現這種“幸福的家庭主婦”并不存在,會引發強烈的“無名痛苦”。
人們往往將這種痛苦的原因歸結為不夠獨立。相比60年代的貝絲,《致命女人》中房子的第二任女主人——80年代的社交名媛西蒙尼擁有充分的經濟獨立。
她的衣物飾品皆源自奢侈品牌,出入高檔餐廳,常活躍于當地社交界。之前的兩段婚姻為西蒙尼積累了豐厚的經濟資源,在第三段婚姻中,她只是需要愛情。丈夫高大俊朗且談吐不俗,好似她幸福生活的最佳證明。

“我的人生就是很完美。”這句話是西蒙尼的驕傲,也是束縛她的魔咒,她希望自己的生活是令人艷羨的。
而西蒙尼的丈夫也正是看中這一點,他喜歡的是同性,但在被妻子發現自己的性取向時并不驚慌。他只需要提醒西蒙尼,如果事情敗露,只會讓她“完美的人生”名譽掃地。
這招也的確行之有效。西蒙尼聰明強勢,唯一的軟肋即是“面子”。童年時家中并不寬裕,一家五口擠在狹窄公寓,那時母親便告誡她:“如果你想睡在昂貴的床單上,就要好好選擇睡在你身邊的人。”
早年貧苦的生活讓西蒙尼尤為享受別人的羨慕與稱贊,注重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令她不敢揭露婚姻的事實。
在這段80年代的親密關系中,束縛住西蒙尼的并非物質,而是他人的目光。
當故事進行到房子迎來第三位女主人泰勒,2019年的她已經將親密關系的探索推進到開放式婚姻。
泰勒是一位體面的律師,她是一名雙性戀,她的丈夫已經連續兩年沒有收入,她也有一個女友。于是他們決定住在一個屋檐下,探索親密關系中多邊關系的可能性。
探索的結果卻是失敗的。欲望和秩序之間,依然沒有找到平衡的答案。

▲ 泰勒與丈夫
不可否認,《致命女人》選取的三個故事并非完全貼近生活,有相當戲劇夸張。
三位女性隨著時代變遷,她們的經濟逐漸好轉,工作愈加體面,也有屬于自己的生活,愛情和婚姻不再是人生唯一的主題。但分明一切向好,她們還是沒有找到理想伴侶,面臨無解的婚姻。
無論在哪個時代,女性依然會為親密關系的困境而陷入令人窒息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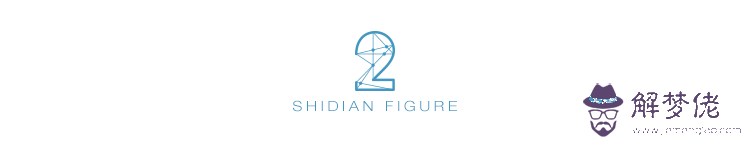
親密關系的困境
眾所周知,婚姻并不容易。
這部劇的每一集都設置了一個巧妙的片頭,第2集的片頭以一個男孩在成長中的觀察貫穿。當他年幼時,隔壁原本恩愛的夫妻家中乍然出現槍聲,他問母親發生了什麼,母親只是嘆氣:婚姻遠沒有看起來那麼簡單。

幾年后,男孩成為青年,隔壁新搬進一對夫妻,平常如膠似漆。然而過了一陣子,警察出現,他看到白布掩蓋尸體,身邊的妻子意味深長:離婚比死亡更加昂貴。

當男孩老了,隔壁年輕情侶同樣以悲劇收場,老人在警笛中感嘆:又一個浪漫愛情故事以謀殺結尾,真令人難以相信。而此時,身邊白發蒼蒼的妻子的回答卻是:我相信。
愛情會以謀殺結尾,女性相信,她們更能理解婚姻為何會走向絕境。

60年代的貝絲,80年代的西蒙尼,當代的泰勒,身上的特質分別從歸順、魅力四射到現今推崇的獨立。她們都擁有美好的品質,但60年世事變遷過后,在親密關系的狩獵場中,依然沒有一個人能成為贏家。
近年來獨身主義盛行,有人將此作為問題的解決方案。可無論如何美化孤獨,人類終究還是一群社會性動物。克里斯多福·孟在《親密關系》這本書中提出,人即使在物質豐富的條件下,仍然需要與他人互動。
親密關系的形成與破滅,會決定人的愉悅或痛苦。
相較于男性,女性會格外關注親密關系。正如西蒙尼喝醉后的那段獨白:“我總認為自己是個非凡的女人,但如果沒人想愛我,我能有多非凡呢?”

被丈夫欺騙多年,西蒙尼仍然無法恨他,因為每當脆弱時,丈夫會不吝贊美。年輕情人送給她階級與年齡都全然不符的手表,她也會戴在手上,因為她看重其中的情意。
當西蒙尼的外遇被戳破時,丈夫表現平靜。雖然早知道丈夫的性取向,但這樣的反應仍然激怒了她,她歇斯底里地朝樓上的丈夫大吼:為什麼你不像一個真正的丈夫一樣感到憤怒?



從表象來看,仿佛女性格外注重愛情,而在以往男性主導的婚姻關系中,她們很多時候無法找到滿意的伴侶。多數女性問題的觀念討論最終都會變成二元對立,淪為過多地闡釋兩性之間的差異,使之呈敵對的狀態。
但事實并非如此。《親密關系》的作者克里斯多福·孟曾說過:“幾乎每個人都希望擁有很棒的親密關系,花費大量精力在尋覓伴侶的旅程中,不斷尋找、失去或離開某個人。”
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需要親密關系。而當最初的興奮褪去,伴侶的行為無法滿足期望,人們感到沮喪。
在克里斯多福·孟眼里,這就來到了親密關系的第二階段——幻滅。
與女性在親密關系中對立的從不是男性,而是幻滅。伴侶身上曾被視為可愛的小怪癖,開始讓人覺得無聊甚至惱火,進而發展成兩人之間的斗爭。

人們渴望親密關系的深入,可隨著深入的過程中,會發現現實與預設的差異性,并不是每個人都能負擔這種深入性。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說過,全是真相的生活比全是謊言的生活更難以忍受。
當幻覺破滅,維系需要花費精力與時間成本,最簡單的方案是逃避,比如結束或背叛。有時,這會引起難以想象的后果。
于是,《致命女人》的編劇讓他的女主角們舉起了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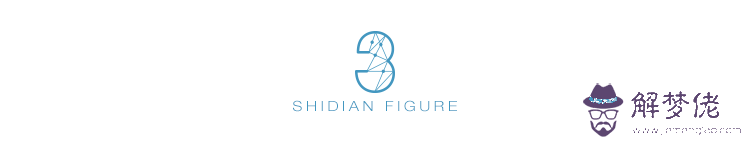
被逼舉刀的女人
有人說,《致命女人》中“殺夫”的結局太過驚悚,其實這更多的是一種象征意義。
“殺夫”的含義,在西方語境中大多代表一種背叛父權社會的扭曲反抗,對手并非某一個人,而是父權、夫權的象征。
早在古希臘悲劇《俄瑞斯忒亞》三部曲中,著名的俄瑞斯忒亞弒母橋段象征男權的復位,而克呂泰墨斯特拉殺夫則是對父權無節制權力的反抗。
這種反抗在夫妻之間更為常見,有時會做出極端的偏差行為。
同樣探討婚姻困境的電影《消失的愛人》里,丈夫尼克與妻子艾米原本恩愛纏綿,然而隨著妻子日益增強的控制欲與丈夫暴露熱戀前的不思進取與懶散,讓妻子艾米極度失望。
結婚五周年紀念日,她步步為營,刻意失蹤,制造被丈夫謀殺的假象,借助公眾輿論對丈夫的施壓完成了一場“殺夫”行為。

▲ 《消失的愛人》劇照
百老匯歌舞劇《芝加哥》則更加極端。權力、欲望與荒誕充斥著畫面,六名女囚依次登場,每個人都有自己殺了丈夫或者情人的理由,背叛、吸毒……有些冠冕堂皇,有些卻只因丈夫嚼口香糖,在曼妙的舞蹈中,游離的聲線重疊成一句:They had it coming(他們活該)。
這并非正面案例,然而呈現出的女性形象更為復雜,作為獨立個體,女人和男人相同:人性善惡面在體內共生,沒有絕對的善與惡之分。

▲《芝加哥》劇照
這種文學意象不僅存在于西方視域,也廣泛存在于東方世界。比如白先勇筆下的玉卿嫂,遭遇磨難勇敢追求愛情后,卻遭情人背叛,選擇共同滅亡;電影《殺夫》中溫柔沉靜的女人林市,受凌虐多年最終化身惡魔殺夫悲劇……
在藝術作品里,這只是創作者的極端幻想就足以令人后背發顫,而當這樣的悲劇發生在現實里,才真正可怖。
早年間,柴靜曾采訪過一名女性重刑犯安華。她被丈夫打了整整二十年,在整整忍了二十年后終于拿起了刀。可是事發之后的幾年里,安華始終想不起殺人的瞬間,臉上全是茫然:
我也一直在想,但想不起來。
與此相對,一篇法學報告顯示,各地監獄女性暴力重犯中,因殺夫而獲罪的比例很高,有的地方甚至達到百分之七十。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這類新聞的評論下,不缺為暴行叫好的人,認為這是一場“以惡懲惡、以暴制暴”的報復。《致命女人》的劇情深入后,多數評論也同樣在叫囂:背叛者與反派角色必須死。
時隔60年,女人處于絕境時仍然選擇被迫舉刀,并通常被淺顯地歸為兩性矛盾,這無疑是一種對文明的諷刺。
除了滿足公眾視野里廉價爽快的復仇感,親密關系的問題非但沒有被解決,最終導致自己也被毀滅,將悲劇無限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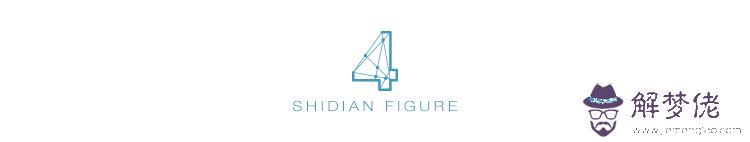
更好的方案存在嗎
女性主義學者戴錦華曾分享過一部電影《君子協定》:主人公是一位很成功的社會新聞記者,需要采訪美國社會中猶太人遭歧視的現狀。他跑去找自己的猶太戰友,對方只說:除非你生而為猶太人,否則你永遠不會明白。

▲ 《君子協定》劇照
于是主人公便將姓氏變成猶太姓氏。自此,他發現生活有了很多細微變化。門房態度微妙,女秘書的笑容少了敬畏。等再次拜訪那位猶太戰友時,他說:
現在你知道了。日復一日芒刺在背的生活,看不見的毒刺每天刺傷你,可你不能叫喊、抗議,因為你拿不到證據——一切太偶然、太瑣屑。
戴錦華分享這個故事的本義是,若將猶太人換成女性,就能巧妙地概括“不甘遵循男性規范的女人在婦女解放的社會中生活”的微妙境遇。
女性的極端反抗,男性通常難以理解。
但《致命女人》的編劇馬克·切利是個例外,這跟他本人的喜好與經歷有關。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性取向,擅長觀察女性心理:
“我是同性戀,所以我對這個問題更加熟悉。我從小到大都沒有把女性作為欲望的對象,而是作為朋友和知己。女人們的種種經歷總讓我心馳神往,我能看見她們生活中內在的戲劇性。”

▲《絕望主婦》劇照
15年前,他在《絕望主婦》中就顯露了這點,主人公住在虛構的中產社區,是他人眼中的完美主婦,永遠保持光彩照人,在丈夫回家時早已備好晚餐和笑容。隨著劇情的深入,觀眾才發現,原來友善的面孔中暗含較量,為了目的不擇手段。
從《絕望主婦》到《致命女人》,是將一種完美關系打碎給人看的延續。
將完美打碎,是重建真實的開始。時隔八年,馬克·切利開始探討是否存在更好的解決方案。
2019年泰勒這條線正是提出了新的方向——開放式關系,它雖然不夠完美,但也探討了新的可能性。只是從目前的走向看,自由的背后是無法控制的邊界,如同劇中那場探戈舞,你進我退,步伐交織,一旦加入他人,失控成了定局。

關于婚姻與親密關系,更好的方案在哪里?
《致命女人》已經完結,編劇仍是沒給出一個清晰答案,無論規訓或是拓展邊界,顯然都不是問題的答案。
無論是60年代,抑或80年代,我們曾以為有最優解出現,但時代不斷進步,愛依然令人痛苦。
這仿佛成了一個無解的循環,我們在反思婚姻制度的同時不禁思考,更好的方案真的存在嗎?
但可以預見的是,答案既不是忍耐,也不會是互相殘殺。

或許正如大結局里,尚且年輕的西蒙尼從上一任房主貝絲手中拿到鑰匙,貝絲已經脫下了討好男性的繁復的蓬蓬裙,她身著簡練褲裝即將去紐約展開新生活,笑得狡黠:
平安喜樂的日子不難有,訣竅是,別去做會讓你后悔的決定。
參考資料:
1.克里斯多福·孟《親密關系》
2.弗里丹《女性的奧秘》
3.槍稿《那些殺掉老公的女人們》
4.北青藝評《女人為什麼要殺人?從“絕望主婦”到“致命女人”》
5.黃小姐與藍小姐《看劇||是什麼讓女人起了殺戮之心?》
6.戴錦華《生為女人》
7.貴圈《致命女人:談戀愛哪有殺老公好看》
8.人物《又一個愛情故事以謀殺收場》
9.李君威《權力合謀下的殺獻與對無節制父權的反抗——古希臘悲劇<阿伽門儂>簡析》






